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改革”离不开“开放”
完全寄希望于政治家个人的担当来推进改革显然并不现实。改革,归根到底,是需要全社会投入的宏大项目,最终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这一点上,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or cowen)在新书《自满的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中所哀叹,美国的问题在于长期的富足已经让整个社会丧失掉曾经令托克维尔惊叹不已的“不安现状”的精神:迁移、冒险、适应变化,这一切驱使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活跃的经济,一个平等流动的社会,培育出从富兰克林到乔布斯等渴望改变世界的创新之才,也让美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东山再起。
仅仅从题目来看,把富足归为问题的核心有宿命之嫌。但科文强调的是托克维尔曾指出过的一个令美国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移民(也包括西部探险者),他们的冒险精神是美国创新和繁荣的源泉。托克维尔曾警告:一旦失去移民这个创新源泉,美国民主就会面临衰败的危险。
如果顺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创新精神的衰减归因于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足。这或许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论断——美国居于全球化的核心地位,是全球化的动力,美国企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美国经济怎么会开放不足?
测量一国对外开放度的一个经典指标是贸易额(进出口额相加)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的贸易额占比在80年代以来一直在20-30%,与日本持平。而其他几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高于美国。例如,英国和法国在50%以上,德国在80%以上,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是40%左右,此后一路攀升到70%以上。
即使考虑到大的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相对要低,美国的开放度也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个令人惊讶的数据其实和美国制造业和国内中小企业普遍负担重(税收、福利、监管)、效率低的现实相匹配。即使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它们的优势更多集中在金融领域而非在制造业,因此贸易额自然无法和德国、中国等相比。
贸易额占比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国的经济活力。但是过低的占比势必意味着国内企业竞争动力不足,面对市场波动的调整能力有限。一旦国际市场竞争环境趋于激烈,产业转型就会变得难以承受,国内反贸易、反移民情绪开始高涨。相比而言,在1990年代经历过阵痛的国家,包括德国、中国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今天的抗压能力相对都较强,经济下行期面临的国内危机也相对缓和。而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个阵痛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一些南欧国家,则极为窘迫。
对外开放带来的压力和持续的调整是个人和企业承受转型之痛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政府利用外来压力抵抗国内既得利益、推动改革的有效工具。政治经济学文献称此策略为“自缚手脚”(tie your own hands)。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来倒逼国内体制改革。
美国需要的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但美国显然没有认真利用这个机会。凭借着独特的优势,美国长期以来可以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身继续享受全球化的成果。而长期的富足也确实磨损了“不安现状”的美国精神。但是,如科文在书中警告的,变革就像债务,可以延期,却不能拒付。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将危机变为改革机遇,危机就会找上门来,要求用更大的代价来还债。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付出的代价。“冷战”结束后的各界美国政府,尽管都无意于利用全球化来冒改革的风险,但至少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特朗普则干脆视自由贸易和开放为敌,在“美国优先”原则的口号下让美国政府放弃一个又一个国际助力——先有tpp,后有巴黎协议,再有开放移民政策——并转而向钢铁、煤炭、石油等传统工业妥协,让美国政府进一步被国内资本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势力俘获,陷入到奥尔森(mancur olson)描述的小集团政治中去,令改革更为艰难。
这个不幸的事实并非难于理解。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前任们,显然都在选择一条轻松的路径,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改革的代价。施罗德的改革为德国在21世纪初的繁荣铺平了道路,但也令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让位于默克尔,后者得以在一个更坚实的结构上领导德国继续向前。特朗普先生对这种风险心知肚明,即使他很清楚,美国的伟大依赖的绝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1980年代以来第一位反对自由贸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建立在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之上:美国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中付出太多而失去“再次伟大”的机会。无论是在共同安全上还是在自由贸易上,美国都在被其他国家敲诈,导致美国今天面临诸多问题。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逻辑。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笔者此前在本刊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讨论中提供了大量细节来解释,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并非源于国际贸易,而是深植于国内长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解决之道,也只能是目光向内,练好内功,应对国际市场的无常变幻。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只会助推这些矛盾进一步恶化,令美国失去恢复荣光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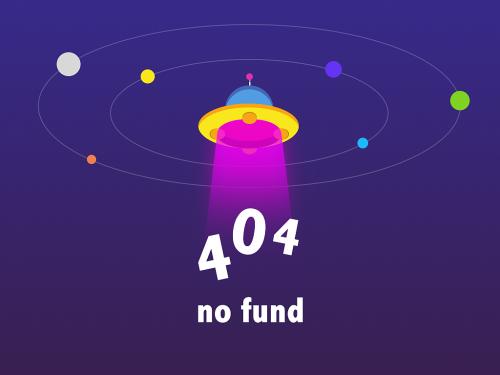
2017年11月9日,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繁荣的代价
自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为欧美发达国家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中收益最多的当属美国。回顾1990年代的反全球化浪潮,反对之声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抗议的焦点则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操纵、污染。而绝大部分西方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又来自美国。这一事实恰恰反映出美国当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整个1990年代是美国经济狂欢的季节。但危机也在同时酝酿,尤其在21世纪初逐步凸显出来。对这一时期美国公共政策失误可以简单总结为“补有余而损不足”。具体而言,“补有余”部分主要包括对金融产业放松监管,对传统制造业过度保护,为高收入人群减税。“损不足”之处则包括拒绝为中小企业减负(包括税率和工人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医疗制度,增加教育和基础建设投入等。其结果是,一方面在全球化中获利最高的金融产业和大企业以及相关的高收入人群享受最大化的政策红利,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普通民众抵御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尤其是当产业结构转型发生时。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1990年代末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各国被迫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这个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显著。但一个突出的异类是美国,几乎在各个方面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背道而驰,视这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为异端。例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导致美国人的健康状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美国在医改法案方面的党争和不作为已是尽人皆知。又如,欧洲国家在战后逐步提高最低收入标准,而美国却从1980年代以来不断减少,助推收入差距拉大。此外,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严重滞后,公立学校投入乏力,教师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美国青少年在历年的国际竞赛中处于发达国家的中下水平。而基础设施更新的严重滞后如果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让人难堪的地步,也不会受到特朗普和投资界的极度青睐。
政治家的担当
在1990年代经济极度繁荣之时,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被忽视。但当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一个“扁平的世界”时,这些“改革赤字”的代价就开始彰显。
这几乎是西方国家普遍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或许可以称为“先发展劣势”。但这并非是一个宿命,而是政策选择。反观一些在90年代没有享受到美国的特殊优势的西方国家,例如北欧诸国,尤其是德国,反而能够励精图治,及早采取措施,一方面减负,一方面增强竞争力,防患于未然。
1998年,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力推全面改革,在产业、福利、教育、技术、绿色经济等各方面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领导德国走出统一后面临的困境。而同一时期的美国则沉浸在泡沫经济的狂欢中,先是克林顿任内的互联网泡沫,后是小布什推动的房产泡沫。泡沫经济带动的是金融扩张,后者又助力游说集团和政治献金在政治中的影响,进一步阻碍改革的推行。
“改革”离不开“开放”
完全寄希望于政治家个人的担当来推进改革显然并不现实。改革,归根到底,是需要全社会投入的宏大项目,最终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这一点上,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or cowen)在新书《自满的阶层》(the complacent class)中所哀叹,美国的问题在于长期的富足已经让整个社会丧失掉曾经令托克维尔惊叹不已的“不安现状”的精神:迁移、冒险、适应变化,这一切驱使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活跃的经济,一个平等流动的社会,培育出从富兰克林到乔布斯等渴望改变世界的创新之才,也让美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东山再起。
仅仅从题目来看,把富足归为问题的核心有宿命之嫌。但科文强调的是托克维尔曾指出过的一个令美国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移民(也包括西部探险者),他们的冒险精神是美国创新和繁荣的源泉。托克维尔曾警告:一旦失去移民这个创新源泉,美国民主就会面临衰败的危险。
如果顺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创新精神的衰减归因于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足。这或许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论断——美国居于全球化的核心地位,是全球化的动力,美国企业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美国经济怎么会开放不足?
测量一国对外开放度的一个经典指标是贸易额(进出口额相加)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几个主要经济体。美国的贸易额占比在80年代以来一直在20-30%,与日本持平。而其他几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高于美国。例如,英国和法国在50%以上,德国在80%以上,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是40%左右,此后一路攀升到70%以上。
即使考虑到大的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相对要低,美国的开放度也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个令人惊讶的数据其实和美国制造业和国内中小企业普遍负担重(税收、福利、监管)、效率低的现实相匹配。即使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它们的优势更多集中在金融领域而非在制造业,因此贸易额自然无法和德国、中国等相比。
贸易额占比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一国的经济活力。但是过低的占比势必意味着国内企业竞争动力不足,面对市场波动的调整能力有限。一旦国际市场竞争环境趋于激烈,产业转型就会变得难以承受,国内反贸易、反移民情绪开始高涨。相比而言,在1990年代经历过阵痛的国家,包括德国、中国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今天的抗压能力相对都较强,经济下行期面临的国内危机也相对缓和。而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个阵痛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一些南欧国家,则极为窘迫。
对外开放带来的压力和持续的调整是个人和企业承受转型之痛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政府利用外来压力抵抗国内既得利益、推动改革的有效工具。政治经济学文献称此策略为“自缚手脚”(tie your own hands)。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来倒逼国内体制改革。
美国需要的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但美国显然没有认真利用这个机会。凭借着独特的优势,美国长期以来可以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身继续享受全球化的成果。而长期的富足也确实磨损了“不安现状”的美国精神。但是,如科文在书中警告的,变革就像债务,可以延期,却不能拒付。如果不能主动应对,将危机变为改革机遇,危机就会找上门来,要求用更大的代价来还债。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国付出的代价。“冷战”结束后的各界美国政府,尽管都无意于利用全球化来冒改革的风险,但至少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特朗普则干脆视自由贸易和开放为敌,在“美国优先”原则的口号下让美国政府放弃一个又一个国际助力——先有tpp,后有巴黎协议,再有开放移民政策——并转而向钢铁、煤炭、石油等传统工业妥协,让美国政府进一步被国内资本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势力俘获,陷入到奥尔森(mancur olson)描述的小集团政治中去,令改革更为艰难。
这个不幸的事实并非难于理解。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前任们,显然都在选择一条轻松的路径,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改革的代价。施罗德的改革为德国在21世纪初的繁荣铺平了道路,但也令他失去民众的支持,让位于默克尔,后者得以在一个更坚实的结构上领导德国继续向前。特朗普先生对这种风险心知肚明,即使他很清楚,美国的伟大依赖的绝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