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居然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守门员,这大概是把足球与橄榄球视为同源运动的英裔澳大利亚球员所不可想像的,在橄榄球里可没有这一说,甚至根本就没有守门员。足球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大概也象征了旧世界的一种等级秩序,与“人人平等”的澳大利亚梦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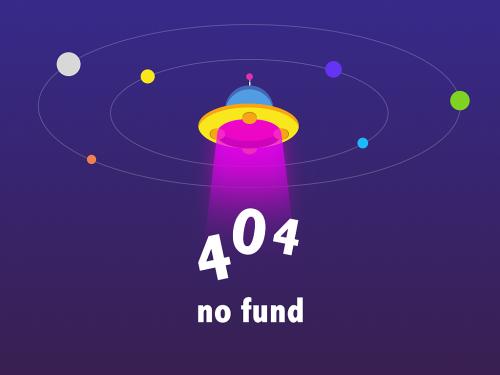
俱乐部小吃摊供图:杨春宇
澳大利亚足球中的欧洲政治
欧陆移民俱乐部与英澳俱乐部之间的争执一直存在,不过相对而言不那么激烈,影响也只限于体育界。对媒体而言,更有新闻价值的消息是欧陆移民球队之间更为火爆的对抗。这种对抗的主要原因来自移民母国的政治斗争,例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纠纷。双方支持者在足球赛场上互相谩骂,有时酿成斗殴,在广播电视传媒的大肆渲染下,这种污名的影响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于澳大利亚。
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争端由来已久,但是在二战后的移民潮到来以前,并没有在移民社区内激起太多的民族情绪。或许是因为二战的伤痕激发了民族间的矛盾,新的南斯拉夫各族移民在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彼此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异国他乡慢慢酝酿起来。1950年代,克罗地亚人在在澳洲各地组织起了足球俱乐部(阿德雷德1952,墨尔本1953,吉隆1954,布里斯本1955),悉尼的俱乐部成立于1957年,足球俱乐部开始成为克罗地亚人的一个平台,借以表达在其它渠道难以传达的政治诉求。由于二战中曾受到克罗地亚人的伤害,塞尔维亚人对这种诉求十分反感,更不用说那些拥护南斯拉夫的其他族群俱乐部了。
从1960年代开始,这些族群俱乐部开始在地方联赛中遭遇,1961年发生在悉尼“南斯拉夫人”(yugal)俱乐部与“克罗地亚”俱乐部之间的第一次比赛就引发了球迷之间的冲突,两个俱乐部都受到了主办方的警告。此后在1963和1964年又发生了几起球场骚乱,双方球迷的对抗甚至延伸到了赛场之外,鉴于事态严重,新南威尔士足球联盟禁止俱乐部在1956年的赛季中使用“克罗地亚”为名,然而即使更名为“亚得利亚地下铁”,该发生的斗殴依旧发生[9]。在墨尔本,克罗地亚队与南斯拉夫队、塞尔维亚队的遭遇也引发了类似的冲突。
同样对立的族群还包括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南斯拉夫解体后,希腊人认为自己才是马其顿的真正后裔,对邻邦编造历史窃取了这个光辉的名字十分不满,所以在双方遭遇的赛场上也时常发生冲突。1992年2月,在希腊裔刚刚抗议过马其顿独立建国之后一天,“海德堡亚历山大”与“普雷斯顿马其顿”就在联赛中遭遇了,尽管因为前者的抵制,实际上只有4000名观众到场,还是爆发了冲突,起因是一位希腊裔牧师称马其顿人为“巴尔干人”。牧师遭到暴打,警方出动了直升机和警犬才恢复了秩序,冲突中有9名观众和11名警察受伤。[10]
类似的冲突还有很多,英裔澳大利亚人十分厌恶这些斗争,认为移民不应该把母国的政治带到澳大利亚来,以至于人们提起足球来就会想起那些他们分不清区别的族群和搞不明原委的矛盾。到90年代前为止,在人们的想象中足球仿佛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少数民族运动,二战之前英国人发展足球的历史已经被晚近的记忆所模糊了。而对英裔足球爱好者来说,尽管移民对足球的贡献是个事实,但他们更喜欢强调移民带来的混乱,最常提起的就是1960年4月至1963年7月间,因为布拉格俱乐部拒付转会费,澳洲足球被fifa下令禁止参加国际比赛这一事实,尽管英国足球流氓活动在六七十年代的兴起使他们也羞于再提足球在英国人的管理下就会正常运转之类的论调,但还是觉得澳大利亚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是被族群政治搞乱了。
迈向“世界运动”
面对足球运动影响日益下降这一问题,各州足球协会想了很多办法,基本都围绕着削弱族群色彩这一点来展开。一开始的措施是消极应对,比如把两个对头分到不同的组比赛,可是这样也还是不能防止他们在决赛中遭遇。后来官方禁止双方在赛场中打出民族旗帜,可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依然会在脸上画上国旗的图案,穿上有民族标志的服装入场。还有一个办法是禁止俱乐部的名称中带有族群名称,企图从根本上消除移民对俱乐部的认同,这样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却并不能阻挡真正支持者的热情,况且俱乐部也不一定就俯首听命。
体育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在国内一般被归入“民族体育”的范畴内来研究,重点在于各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而在西方国家,相关议题多半归属于体育社会学和族群认同等研究领域,沿着皮埃尔·布迪厄、诺伯特·埃利亚斯等社会学大家的经典论述,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成熟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不但论及与体育相关的社会变迁、文化展演、族群认同和全球化等议题,而且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般理论也有所贡献,可以说,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
在中外研究关注点差异的背后是不同的国情和文化背景。首先是不同的民族构成,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世居民族,“民族”概念基本不涉及外来移民。而西方国家由于殖民和社会流动的原因,外来移民构成了各种“族群”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在美洲和澳洲各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体育运动受此背景影响,往往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还折射出各民族的政治认同。
其次是“体育”这一文化现象的现代渊源。“sport”这一术语严格来说对应的中文词汇是“竞技”而非“体育”,强调的是对抗性和制度性的一面。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sport”不但负担起了塑造公民体魄、意志和纪律性的责任,而且以其高度的对抗性和复杂的组织比赛规则成为了西方社会规训和宇宙观的缩影。因此跟中文背景下与“休闲”、“锻炼”等概念相关的“体育”研究不同,研究sport也就是研究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比较容易与一般社会理论的议题挂起钩来。[1]
澳大利亚学者对足球与族群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正是展现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体育的一个好例子。通过这一案例,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个移民社会的变迁和全球化的过程,更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义内在的张力。考虑到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移民不断增加,由此造成的新型民族问题日益凸现,这些经验对我们不无借鉴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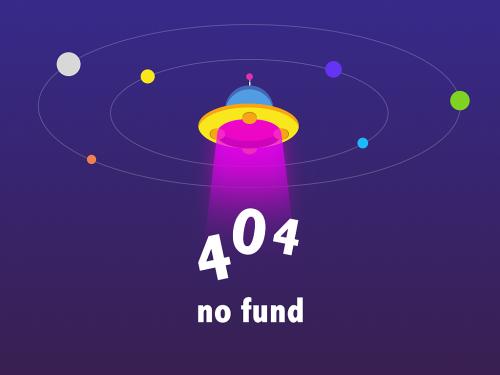
从“英国球”到“外国球”
虽然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起源于英国的现代足球运动(soccer)却并非澳大利亚足球的主流。在澳大利亚流行的足球(football)共有四种:橄榄球联合会(rugbyunion)、橄榄球联盟(rugbyleague)、澳式足球(australianfootball,80年代以前叫australianrules)和英式足球(soccer)。
在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橄榄球联合会和联盟最为流行,联合会在新南威尔士的地位最高,联盟次之[1]。这两种运动风格都比较强悍,在四种“足球”中对抗是最激烈的。澳式足球比较强调灵活性和速度,对抗性稍弱于橄榄球,但是球员防护少,风险也颇高。相比较起来,足球是最为文雅的,身体接触少,对抗相对较轻。所以现在少儿足球和女子足球发展很快。从地域分布上看,足球在每个州都是第二流行的广义足球项目,其中相对而言,在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要比在其他地方更流行些。[1]
所有这四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运动,在英语国家的人看来都是广义的足球,只是规则不同,参加的阶层不同,筹办的组织不同而已。在英语国家有句谚语:“足球是野蛮人玩的绅士运动,联合会是绅士玩的野蛮人运动,联盟是野蛮人玩的野蛮人运动。”意思是足球踢起来很绅士,可热衷此道的却是工人阶级,榄球是一项野蛮的运动,一开始却是贵族把持着的,后来才因为下层阶级的加入而分裂开来。[2]
在英联邦体育史上,有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现代足球是在英国成型的,是英国的第一运动,可是在许多重要的英联邦国家(或英联邦的旧成员国)里,如美国、加拿大、南非、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足球却都不是最受欢迎的运动。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与上述历史有关,且不说美国,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殖民都是在现代足球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他们在继承足球原始形态的基础上都发展出了有地方特色的“足球”,在美国是美式足球(或曰美式橄榄球),在澳洲则是澳式足球,第一份澳式足球规则的出版仅仅比足球规则在伦敦的正式成型晚三年。[1]有了这些本地竞争者之后,留给足球的空间就相对有限。所以现在澳大利亚体育版图上复杂的“足球”分布与排名其实是与英国殖民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足球比赛据说于1880年在悉尼举行。当时来澳的英国移民,如果出身于英国私立学校的,多半玩橄榄球,而工人阶级则更青睐足球。在当时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和煤矿的矿工群体中,足球曾经风行一时,成为工余时间受欢迎的消遣。
在1929年,新南威尔士的足球组织经历了一场分裂,一方是老一代的管理者,他们赞成基于地区的联赛方式,认为自己考虑的是这项运动的整体利益,而另一方是新来的英国移民,他们认为自己俱乐部的水平较强,于是分裂出去成立了一个新南威尔士州足球联盟(nswssl),最终这个新的实体取代了旧有的组织。[1]可以说,这个时代已经奠定了澳大利亚足球发展史上主要矛盾的基调,那就是新旧移民之间的冲突,以及基于地区的俱乐部与基于移民团体的俱乐部之间的冲突。只是这个时候的澳大利亚基本上还是英国移民的天下,所以这些矛盾还没有凸现出来而已。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日军战火波及的澳大利亚政府痛感人口不足对国力的影响,制定了资助移民以充实国力的政策。种族主义的眼光当时主导了移民的优先权,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是西欧和北欧,再次才考虑东欧与南欧那些卷发、肤色偏黑的白种人。当时的欧洲满目疮痍,众多移民为澳大利亚伸出的橄榄枝所吸引。到1963年底,总共有将近200万新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其中将近一半的移民来自英国,剩下的移民中,意大利人最多,其次是希腊人、荷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20个国家的移民。新移民多半在工厂里充当劳工[2](p.117)。
与白澳政策配合的是民族同化政策,新移民都被要求说英语,采取“澳大利亚生活方式”,这种同化的理想可以从当时颇受欢迎的一本小说《他们是一群怪人》(theyareaweirdmob)中看出来,约翰·奥格雷迪在小说中虚构了一名意大利“拉丁裔”移民尼诺·卡洛塔,他并没有遭遇到预想中的歧视:
“尽管一开始澳大利亚俚语给他带来不少困难,但是很快那些粗犷的悉尼工人就把它看作是跟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伙伴。他学会了畅饮啤酒,欣赏澳式足球,最终和一位当地姑娘幸福地结为夫妻。他的意大利同胞坚持用意大利语跟他交谈时,他直摇脑袋。”(笔者有修改译文)[2](p.118)
这样的理想虽然生动,却把民族融合过程想得太过容易,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移民政策的出发点本来是为了满足澳大利亚对劳动力的需要,所以是互利互惠的事,而同化政策显然只考虑到了主人的困难,却没有考虑到客人的困难,要求移民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彻底认同当地人主要从英国继承来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当时移民首选的英语国家目的地是美国和加拿大,其次才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在他们眼中,北美是一片繁荣富庶的地方,而澳洲则是毒虫怪兽横行的世界,[3](n76)[4](n4)不过来澳大利亚的花费要求比去美加便宜。带着战争创伤来到这里的新移民一般都得度过一段艰苦岁月,在国家亟需劳动力的地方工作一段时间,这些地方多半地处偏僻,而且工作繁重,经济地位较低。澳洲的体育史家罗伊·海曾指出,战后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在澳洲的境况很有几分类似西欧国家工业革命之后离开乡村或半城市社区进入工厂的第一代工人,都面临着重建身份和社会纽带的困境[3]。即使在入籍之后,他们也要面对文化上的压力,在同化政策下,许多移民选择了艰难的融入过程,还有许多移民选择的是继续留在移民社团里,保持自己在文化与人际关系上与母国的纽带。与当年在工业革命后进入大城市的工人一样,他们选择了足球作为自己的避风港。
移民文化的堡垒
澳洲足球在战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得说多半拜欧洲移民所赐。这些移民来到人地生疏的他乡,工作之余需要休闲,但玩不惯当地风行的澳式足球和榄球,于是把家乡流行的英式足球当作了主要消遣。因为外国球员大量加入,其中不乏好手,移民很快就成为澳洲足坛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足球在澳大利亚有了个别号,叫做“外国球”(wogball)。
足球俱乐部是当年许多移民社区的文化堡垒与社交中心,人们不但可以在这里寻求实际的帮助,还能找到感情上的藉慰,在异国他乡找到些许故乡的感觉。所以尽管许多媒体将移民组织的足球俱乐部视为抗拒同化、制造分裂的场所,今天的体育史家却认为,这些俱乐部至少缓冲了移民的疏离感,有利于他们度过最初的艰难岁月[3]。即使是散居的移民,也可以通过周末加入俱乐部的活动来寻求归属感,可以说,是足球让族群成了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的实在,而不再仅仅是移民记忆中的一个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5]而对于移民中的精英来说,体育俱乐部也是个有用的组织,一是可以向政府显示移民社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参与政治的一个台阶。
在澳大利亚,可以说直到90年代之前,足球一直是一项靠移民支持的运动。与轻易就能融入主流的英国人相比,二战后到来的东欧和南欧移民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他们感到了保存和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需要做出特别的努力,作为社区的中心,足球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这种使命。在1990年代对悉尼的克罗地亚足球俱乐部所作的民族志研究中,社会学家约翰·休森(johnhughson)生动地展现了二代与三代移民青少年球迷(或曰足球流氓)群体“蓝色坏男孩”(badblueboys,简称bbb)对父辈文化的传承。他们本着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继承了父辈从克罗地亚乡村带来的父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自认为比那些背弃了祖宗传统的同辈精英更为高贵。在赛场上,他们行纳粹礼[3],高唱克罗地亚民族歌曲,用休森的话来说,这些仪式是在以足球为载体对族群传统实现“神奇的复原”(magicrecovery)。[6]
俱乐部形成后,各国移民的队伍开始通过加入联赛或友谊赛的方式与澳洲本地球队展开了对抗,这种比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友好的,但是在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族群之间竞争的色彩。移民在工厂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往往会在赛场上发泄出来,战胜澳洲本地球队代表着移民群体的一种胜利,代表着他们一旦获得公平竟争的机会,就不但不弱于,而且还会胜过本地人,使他们得以一吐在同化政策下积累的怨气。[7][8]有人曾提及,在有些极端的情况下,移民队甚至不介意使用作弊的手段来获胜,以提高社区的民族认同[3]。在战后的一段时期,移民与本地队之间的矛盾在双方都积累了一些对立情绪。
这些对立体现在组织上,1957年,以奥地利人和犹太人俱乐部为首的一些悉尼的族群俱乐部不满原先的新南威尔士州足球联盟基于地域的组队传统和晋级规则,独立出来成立了新南威尔士足球俱乐部联盟(nswfsc)。尽管当时的全国组织澳大利亚足球协会(asfa)不赞成他们这样做,但是最终它也没能抵挡住之后各州足球组织的分裂,当昆士兰和南澳在1961年也成立了新的足球协会之后,新成立的各州协会在同年11月宣布成立新的澳大利亚足球协会(asf)。这个组织最终取代了旧的组织,成为全澳大利亚统一的足球组织机构,直至今日。这些俱乐部的独立一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水平较高,理应获得较多的门票收入,而澳洲本地球队要求比赛收入平分;一部分是出于理念的不同,据说移民俱乐部比较注重胜负,不象英国移民和澳洲本地俱乐部那样注重少儿足球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1]
在移民俱乐部与本地俱乐部的对立情绪背后,除了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文化上的因素同样重要。在二战以前,其他国家移民尚未大批来到时,澳大利亚的足球水平不高,风格主要是追随英式,以建立在充沛体力基础上的凶猛拼抢为主,注重团体配合。这跟广义足球里其他类型运动的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都注重整体的力量,强调个人服从团体需要,强调牺牲精神和强硬的作风。新来的(尤其是南欧)移民们却不是这样,他们脚法更为细腻,而且善于玩些隐蔽得很好的小花招,例如假摔、拉扯球衫、背后铲人等等,还会当面吐唾沫,让英裔澳大利亚人觉得很是气不过。反过来说,欧陆球员,尤其是那些技术很好的球员也很头疼英国式的野蛮拼抢。[1][8]而且当时裁判水平不高,外来裁判与本地裁判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本地裁判往往判罚更为宽容,对身体接触、碰撞中的犯规倾向于视而不见,而欧陆来的裁判就会很注意,这就可能引起双方对于判罚公正性的争议。其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项或许是,英裔球员认为可以在对方守门员持球站立时,用肩膀将其连人带球撞入网内,而欧陆球员则对待守门员就要文雅的多,他们强烈反对这么做。[4]诸如此类的摩擦或许都不算大事,但是日积月累,双方在对方心目中的刻板印象却在一天天形成。
或许对英裔与欧陆裔移民之间的这种矛盾总结得最好的还是莫斯利和玛瑞:
英裔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在足球风格上还有文化鸿沟,前者喜欢更注重体力、拼抢凶猛的比赛,后者青睐更文明的、讲究技巧的比赛,这种风格被前者斥之为“娘娘腔”。最明显的就是对待守门员的态度了:澳大利亚人讲究公平竞赛,欧陆人讲究神圣不可侵犯。场外在比赛管理过程中,文化差异同样明显,更保守的英裔澳大利亚人想把钱均分;而那些实际上最能挣钱的俱乐部(总是欧陆人的俱乐部)却想自己把钱留下。结果就是它们与全国协会的一系列分裂举动,形成了今日管理澳大利亚足球的那些联盟。[1]
居然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守门员,这大概是把足球与橄榄球视为同源运动的英裔澳大利亚球员所不可想像的,在橄榄球里可没有这一说,甚至根本就没有守门员。足球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大概也象征了旧世界的一种等级秩序,与“人人平等”的澳大利亚梦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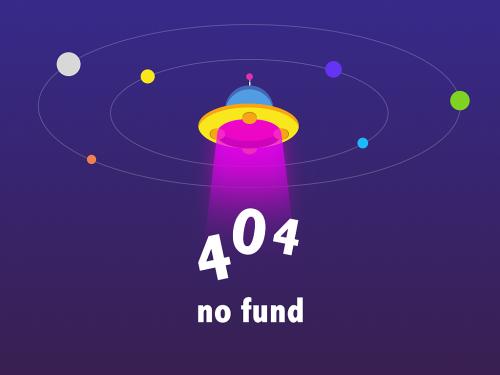
俱乐部小吃摊供图:杨春宇
澳大利亚足球中的欧洲政治
欧陆移民俱乐部与英澳俱乐部之间的争执一直存在,不过相对而言不那么激烈,影响也只限于体育界。对媒体而言,更有新闻价值的消息是欧陆移民球队之间更为火爆的对抗。这种对抗的主要原因来自移民母国的政治斗争,例如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之间的矛盾,以及马其顿与希腊之间的纠纷。双方支持者在足球赛场上互相谩骂,有时酿成斗殴,在广播电视传媒的大肆渲染下,这种污名的影响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于澳大利亚。
南斯拉夫内部的民族争端由来已久,但是在二战后的移民潮到来以前,并没有在移民社区内激起太多的民族情绪。或许是因为二战的伤痕激发了民族间的矛盾,新的南斯拉夫各族移民在到达澳大利亚之后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彼此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异国他乡慢慢酝酿起来。1950年代,克罗地亚人在在澳洲各地组织起了足球俱乐部(阿德雷德1952,墨尔本1953,吉隆1954,布里斯本1955),悉尼的俱乐部成立于1957年,足球俱乐部开始成为克罗地亚人的一个平台,借以表达在其它渠道难以传达的政治诉求。由于二战中曾受到克罗地亚人的伤害,塞尔维亚人对这种诉求十分反感,更不用说那些拥护南斯拉夫的其他族群俱乐部了。
从1960年代开始,这些族群俱乐部开始在地方联赛中遭遇,1961年发生在悉尼“南斯拉夫人”(yugal)俱乐部与“克罗地亚”俱乐部之间的第一次比赛就引发了球迷之间的冲突,两个俱乐部都受到了主办方的警告。此后在1963和1964年又发生了几起球场骚乱,双方球迷的对抗甚至延伸到了赛场之外,鉴于事态严重,新南威尔士足球联盟禁止俱乐部在1956年的赛季中使用“克罗地亚”为名,然而即使更名为“亚得利亚地下铁”,该发生的斗殴依旧发生[9]。在墨尔本,克罗地亚队与南斯拉夫队、塞尔维亚队的遭遇也引发了类似的冲突。
同样对立的族群还包括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南斯拉夫解体后,希腊人认为自己才是马其顿的真正后裔,对邻邦编造历史窃取了这个光辉的名字十分不满,所以在双方遭遇的赛场上也时常发生冲突。1992年2月,在希腊裔刚刚抗议过马其顿独立建国之后一天,“海德堡亚历山大”与“普雷斯顿马其顿”就在联赛中遭遇了,尽管因为前者的抵制,实际上只有4000名观众到场,还是爆发了冲突,起因是一位希腊裔牧师称马其顿人为“巴尔干人”。牧师遭到暴打,警方出动了直升机和警犬才恢复了秩序,冲突中有9名观众和11名警察受伤。[10]
类似的冲突还有很多,英裔澳大利亚人十分厌恶这些斗争,认为移民不应该把母国的政治带到澳大利亚来,以至于人们提起足球来就会想起那些他们分不清区别的族群和搞不明原委的矛盾。到90年代前为止,在人们的想象中足球仿佛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少数民族运动,二战之前英国人发展足球的历史已经被晚近的记忆所模糊了。而对英裔足球爱好者来说,尽管移民对足球的贡献是个事实,但他们更喜欢强调移民带来的混乱,最常提起的就是1960年4月至1963年7月间,因为布拉格俱乐部拒付转会费,澳洲足球被fifa下令禁止参加国际比赛这一事实,尽管英国足球流氓活动在六七十年代的兴起使他们也羞于再提足球在英国人的管理下就会正常运转之类的论调,但还是觉得澳大利亚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是被族群政治搞乱了。
迈向“世界运动”
面对足球运动影响日益下降这一问题,各州足球协会想了很多办法,基本都围绕着削弱族群色彩这一点来展开。一开始的措施是消极应对,比如把两个对头分到不同的组比赛,可是这样也还是不能防止他们在决赛中遭遇。后来官方禁止双方在赛场中打出民族旗帜,可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依然会在脸上画上国旗的图案,穿上有民族标志的服装入场。还有一个办法是禁止俱乐部的名称中带有族群名称,企图从根本上消除移民对俱乐部的认同,这样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却并不能阻挡真正支持者的热情,况且俱乐部也不一定就俯首听命。
最终,根本性的转变是由俱乐部自身推动的。进入90年代以后,澳洲移民的源头从欧洲转到了亚洲,以前被白澳政策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亚洲人种现在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大气氛下大量进入澳洲,尽管限制颇多,还是在90年代逐渐取代了欧陆移民,成为移民的主力。随着老一代欧陆移民渐渐老去,二代和三代移民对母国的认同逐渐淡漠,移民对足球俱乐部的社区归属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俱乐部提供了充足的财政支持,但是随着南斯拉夫内战的爆发,许多移民的捐款转而流向了欧洲,甚至有些已经入籍的人径直回国参战。少数族群足球俱乐部开始感受到危机,谋求向地方寻求支持。许多俱乐部在这一时期都采取了“地名加族名”的命名方式,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三支墨尔本市球队的命名即是如此。这种举措有一定风险,运作得好的话可以左右逢源,否则难免两面吃亏。传统的支持者认为俱乐部背叛了他们,而地方议会以及其他的捐赠者则坚决要求去掉族群的名字,以改变人们对足球的成见,维持俱乐部向所有人开放、一视同仁的形象。最终后者的影响力还是战胜了前者,在笔者到达堪培拉的时候,可以从名字上辨别出族群身份的俱乐部已经只有两个:冈伽林尤文图斯(意大利)和白鹰(塞尔维亚),如果不是有人指点,很难知道“堪培拉足球俱乐部队”其实隶属于克罗地亚俱乐部,也有族裔背景。[11]
但这只是对外人而言,对于许多欧陆移民及其后裔来说,要放弃对支持多年的俱乐部的拥护还是件很困难的事,即使是在族群名称完全从队名中消失后也是如此。自然,俱乐部也不愿放弃他们的支持。休森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即使“悉尼克罗地亚队”改成了“悉尼联队”,克罗地亚人依旧是球迷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自有办法来应对“去族裔”的后果。“蓝色坏男孩”们将“联合(united)”一词中的“u”绘在黑底的旗帜上,不过代表的是“乌斯塔西(ustashi)”,二战中帕维利奇领导下的法西斯军团(hughson1997)。他们用克罗地亚国旗上的红白蓝三色代表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在外人眼中却像是在代表新教的英国。[12]
洛林·丹佛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欧陆移民足球俱乐部里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个悖谬的现象。在政府推行同化政策的五六十年代,足球俱乐部顶住各方压力,将自身发展成了移民的文化堡垒,甚至还突破了联赛的限制,通过互相联合取代了形成了新的全国性组织,取代了原来英裔移民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欧陆移民的骄傲。在政府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90年代,俱乐部却开始淡化甚至否认自己的族群色彩,积极向以英裔澳大利亚人为主的地方社区靠拢。如果说前者证明了欧陆移民民族认同感的强大的话,后者大概就只能证明多元文化政策的不足了,丹佛斯引用了“澳大利亚人口与族裔事务委员会”对多元文化政策的声明:
在公共场合,因为与私人领域有根本的不同……只能承认一套法规,一套政治经济制度……允许每个文化群体自由发展其自己的法规、政治制度和实践将威胁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存在。[10]
他同意《错误的身份》的作者的质疑:多元文化到底要的是什么“多元”?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实际上是把“文化”的概念缩小了,等同于民俗、遗产和传统。[10]这基本上符合西方启蒙以来对于“理性”和“文化”的二分,即理性是普遍的人性,而文化只是花边和装饰,是旧时代留下的包袱,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妨碍理性的发挥。所以基于理性建立的制度应该成为公共领域的唯一平台,而文化则是一种私人的事务。所以“多元文化”所说的文化与文化人类学所说的文化并不一样,不是包括宇宙观、组织、制度和观念的一个整体,也不是一个流动的、充满了生造性的意义世界,倒是更接近80年代以来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跨文化主义,倾向于刻板和孤立的文化观,而在人类学里面,这类文化观早就已经得到了比较彻底的反思。
步入90年代以后,在族群足球俱乐部去族裔化的同时,英裔澳大利亚人对于足球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在战后到90年代之前,主流社会对“外国球”基本上抱一种贬斥的态度。理由有三,一是因为族裔政治引起的骚乱,这一点在上面已经谈过了,或许他们最终害怕的是被新移民排挤出自己的国家,休森曾提及,悉尼的一个英裔澳大利亚人在克罗地亚队的主场上感觉自己“象是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一样”;[12]二是对足球的发展威胁到其他运动传统优势地位的忧虑,在澳式足球最流行的墨尔本,1958年一个足球俱乐部想租用一片长期由澳式足球俱乐部使用的议会运动场,市议员的答复是“让他们去阴沟里玩吧。”;[1]三是足球本身较弱的对抗性让人质疑足球运动员的男子汉气概,尤其在欧陆风格进入之后就更是如此。不过这最后一项看起来更像是个借口。正如澳大利亚的足球英雄,曾经作为队长把“袋鼠队”带入1974年世界杯的约翰尼·沃伦(johnnywarren)所作自传的书名《小妞、外国佬和娘娘腔》[4]一样,足球在澳洲曾一度顶着众多的污名。[13]然而随着澳洲足球水平的提高,效力于英超的澳洲球员逐渐增多,同时随着民间对外交往加强,澳大利亚人正在发现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魅力。约翰尼·沃伦为足球大声呼吁: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人喜爱赢家。至少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们喜欢世界冠军。我不想贬低其他的运动或者体育项目,但是最好的板球国家也不过有大概四五个对手。橄榄球联合会和橄榄球联盟也是如此,澳式足球的范围就更窄了……要赢得世界杯,我们得击败203个国家,足球在很多这些国家可是国民运动、人民的宗教、大众的热情所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它?说“足球是项很好的运动,真的需要技巧,不过澳大利亚人就是不玩它”呢?[12](pxxv)
可以说,足球在澳大利亚正在摆脱多年来的污名,作为一项“世界运动”进入人们的视野,赢得越来越多的爱好者。2005年,澳大利亚新任的足协主席弗兰克·洛维聘请了曾任橄榄球联盟执行官德约翰·奥尼尔,开辟了新的澳大利亚足球超级联赛。精彩的新联赛吸引了众多体育爱好者,共有3万2千名观众到场观看了阿德莱德队与悉尼fc队的决赛,盛况空前。在2006年世界杯进入八强之后,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在笔者田野工作所在地堪培拉,如果把各个年龄段都算上的话,现在足球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热情的背后并不单纯是一个“融入世界”的朴素愿望在起作用,它与澳大利亚在世界舞台上寻找自身民族定位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媒体和商业对体育的介入有密切联系。此外,后殖民社会与消费主义也是谈论足球时必须注意的一个基本语境。丹佛斯指出,在完成了去族裔化过程后,现在墨尔本的足球俱乐部已经完全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了,至少在名称上无从辨别。可是在进入21世纪时又出现了新的动向,传统上有少数族裔支持的俱乐部又开始把自己的这段历史重新包装之后拿出来宣传,也就是说,在完成了向主流的靠拢之后,俱乐部重新发现了族性的价值,只是这一次的标榜不再是为了吸引移民的忠诚,而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作为文化商品的独特性。[10]
结语
从以英国移民及其后裔为主的建国方案,到吸纳了欧洲各国移民的“白澳政策”,再到包容亚洲移民的多元文化主义,澳大利亚社会从地方(provincial)殖民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后工业社会。一代一代的移民来到这里,贡献了自己青春和热情,逐步融入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现代足球本来是一项发源于英国的体育运动,却是在欧陆移民的带动下才真正在澳大利亚普及开来,其地位在当地的多种“足球”中逐步提升,成为堪与其他热门项目匹敌的流行运动。足球既是大英帝国的骄傲,也是欧陆移民的乡愁,既是少数族群文化的堡垒,也是全球化了的世界运动,既是发酵政治冲突的温床,也是传播平等和友情的方舟。看似象征了“世界大同”的全球第一运动——足球,在澳大利亚可谓走过了一条坎坷起伏的长路,展开其中纠结的种种议题,几乎就是一部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史。
如上文所言,在社会科学昌明的澳大利亚,学者是这一进程的最佳观察者,他们的研究综合了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进路,揭示出了足球与族群、政治、性别和经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而近些年来,也有国内学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少儿足球俱乐部。[14]文化多元主义能否解决今日西方社会的困境?全球化背景下,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该向何处去?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澳大利亚足球中的族群政治无疑为社会科学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参考文献]
[1]mosely,philipandbillmurray.1994.soccer.inwrayvamplewandbrianstoddarteds.,sportinaustralia:asocialhistory,pp213-30.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杰弗里·博尔顿著,1993年,《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李尧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3]hay,roy.1994.britishfootball,wogballortheworldgame?towardsasocialhistoryofvictoriasoccer,injohno’haraeds.ethnicityandsoccerinaustralia,pp44-79.campbelltownnsw:australiansocietyforsportshistoryincorporated.
[4]hay,roy.1999.black(yelloworgreen)bastards:soccerrefereeinginaustralia:amuchmalignedprofession,insportingtradition,vol.15,no.2,may.
[5]jones,roy,andphilipmoore.1994.‘heonlyhaseyesforpoms’:soccer,ethnicityandlocalityinperth,wa.injohno’haraed.,ethnicityandsoccerinaustralia,pp16-32.campbelltownnsw:australiansocietyforsportshistoryincorporated.
[6]hughson,john.1997.thebadblueboysandthe‘magicalrecovery’ofjohnclarke.inrichardgiulianottiandgaryarmstrongeds.,enteringthefield:newperspectivesonworldfootball,pp239-60.oxford:berg.
[7]vamplew,wray.1994.austrliansandsport.inwrayvamplewandbrianstoddarteds.,sportinaustralia:asocialhistory,pp1-18.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8]lynch,rob.1991.disorderonthesidelinesofaustraliansport,insportingtraditions,thejournaloftheaustraliansocietyforsportshistory,pp50-75,vol.8,no.1,nov.
[9]mosely,philip.1994.balkanpoliticsinaustraliansoccer.injohno’haraed.,ethnicityandsoccerinaustralia,pp33-43.campbelltownnsw:australiansocietyforsportshistoryincorporated.
[10]danforth,loringm.2001.isthe"worldgame"an"ethnicgame"oran"aussiegame"?narratingthenationinaustraliansoccer.inamericanethnologist,vol.28,no.2,may,pp363-87.
[11]杨春宇,《平等竞争——从少儿足球竞赛看澳大利亚社会平等主义的再生产》,载谢立中主编《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5月。.
[12]hughson,john.2002.‘wearered,whiteandblue,wearecatholic,whyaren’tyou?’:religionandsoccersubculturesymbolism,intaramagdalinskiandtimothyj.l.chandlereds.,withgodontheirside:sportintheserviceofreligion.london:routledge.
[13]warren,johnny.2001.sheilas,wogsandpoofters:anincompletebiographyofjohnnywarrenandsoccerinaustralia.sydney:randomhouseaustraliaptyltd.
[14]杨春宇:《平等及其边界: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民间组织的文化实践》,博士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年。
[1]为尊重约定俗成的翻译习惯,下文中还是用“体育”一词来对应“sport”。
[2]下文中的“足球”,如非特殊注明,对应的还是英式足球(soccer)。
[3]这很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反感,但休森指出他们其实并不是在向纳粹,而是在向自己的民族英雄安特·帕维利奇(antepavelic)致敬。
[4]‘sheilas,wogsandpoofters’都是澳洲俚语,沃伦用这些词汇是为了讽刺澳大利亚人对足球的偏见。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