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受害者”与“施害者”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成果,欧洲的犹太人从1791年起开始享有公民权利。这一进步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得到逐步完善。
当年拿破仑把犹太人从所谓的“隔离区”中解放出来,结果是,他们一方面的确有了融入基督教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必须直接面对基督教徒出于宗教原因对他们的排斥。隔离时,两者矛盾对立并不突出;融合时,格格不入才变得明显起来。
1879年,普鲁士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冯·特莱奇科(heinrich von treitschk)的那句“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在欧洲引发一波排犹高潮。1895年,反犹主义者吕格(karl lueger)以绝对多数当选为维也纳市长;此前一年,就职于法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其犹太人身份,被判“叛国罪”而终身流放,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虽然他数年后获平反昭雪,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国保守的教会人士和保皇派势力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反犹攻势,质疑犹太人享有普通公民权利这一共和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追求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zionism)应运而生,目的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开始时,欧洲的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相对富裕和有文化的阶层,并未真正热衷于这项事业,但后来纳粹的灭绝政策给他们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结果。他们做梦都未想到,偏偏是德国这个此前曾向遭迫害的中东欧犹太人慷慨施以援手,以及在文化上与自己紧密相连的国度,会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
有人说,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指的是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镇压、迫害和打击。了解犹太历史的人,应该理解以色列人为何如此团结,那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始终受到周围的威胁。同时,根据上一段落中描述的状况,我们也有理由担心,这种迫于外部压力和侵害的环境一旦消失,以色列国内的自身矛盾也许会迅速凸显。
诚然,以色列立国第二天即遭到阿拉伯人的围剿,所以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缺乏信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自己已经强大到无人可敌的时候(如今的以色列基本如此),应该给别人留活路。以色列的侍强霸道和美国人的一味袒护,或许正是西方社会“反犹思潮”重新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或质疑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反对以色列人违反国际法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不等于反犹。我们可以反对“反犹主义”,但不能因此而失去批评以色列政策的权利。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者经常混为一谈:谁批评以色列,谁就很容易被扣上反犹这顶帽子。
还有,犹太人历史上的不幸遭遇,并不是“天下曾负我,我亦负天下”的理由。按理说,反复遭受厄运打击的人,更应该理解别人的相同苦楚,更不该对他人施加同样的危害。
可惜,旧的不幸正在被新的不幸所取代,原先的受害者现在似乎已成为施害者。犹太人应该知道,以往本民族所受过的冤屈和付出的牺牲,不能成为自己蔑视国际法的“永久免罪符”。以色列有生存权,巴勒斯坦人同样享有生存权。以各种借口阻止巴勒斯坦人享有这一权利的言行,都是产生新暴力和不公平的温床和助推器。
三年前去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gunter grass)曾因一长一短两部作品闻名于世:长作品是小说,叫《铁皮鼓》,它给格拉斯带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短作品是一首诗,叫《不得不说的话》,引发一场关于以色列的政治激辨。
他在这首诗中写了这么一句话:“核国以色列正在危及本就脆弱的世界和平?”或许,格拉斯本人也担心这么说有些过头,所以在句子后加了个问号,以冲淡这句话的爆炸性意味。但他的这首诗一经发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性效应。
或许,他想要的正是这种效应。总之,这句针对以色列所说的话,差点让这位伟大的作家“晚节不保”。但是,现在重温他那些“不得不说的话”,再结合当下中东的局面,读者或许更能切身感受到他当年压抑许久的心境,更能体会他真正想要说的话。
格拉斯这首诗有两个重点:一、之所以沉默那么久,是因为他的身份——来自曾经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发表后又披露出他自己曾参加过俗称“黑衫军”的“武装党卫队”;二、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把以色列和伊朗一视同仁,将两国双双置于国际核能机构的监督之下。
格拉斯说错了吗?没有。但为何至今难以实现?
特朗普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前,内坦亚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被记者追问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他最后的回答是:“你可以尽情地猜测,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以色列不会威胁和毁灭任何国家。”如果伊朗也说它即便拥核,也保证不主动打击其他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会接受它生产核武器吗?
德国社民党和左派党前主席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日前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明确指出:“我驳斥美国发动的战争是服务于民主的谎言。”他这话虽然是点名特朗普,但针对的却是那个“谎言”本身。
而这些恐怕才是更该引发我们深思的问题。
从军事角度看,以色列已成功控制住巴勒斯坦人,但这种长期占领别人土地的状态,不仅对民主体制有害,还会造成另一个层面的分化: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犹太裔美国人越来越疏远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对此一方面无所作为,同时又指责犹太裔美国人的批评是自我仇视。这种做法非常短视,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国。
建国70年的以色列,军事上应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伊朗,目前都没有能力威胁它的生存。德黑兰虽然嚷着要消灭以色列,但它知道自己还不是这个犹太国家的对手。
然而,从外部撼动以色列固然暂无可能,它的内部却存在一个比伊朗更大的威胁:一个日趋分化的社会。这里,各阶层各奔自己的目标,而政府对此一筹莫展。由于外界更关注以色列承受的外部压力,因此很难窥视到以色列国内的真实情况。
以色列第一任也是任职最长的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愿景,是让以色列成为一座“大熔炉”。他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立国时,对什么才是“新犹太人”有着明确的设想:他应该是一个世俗(非宗教)的、通过体力劳动建设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先锋。但这个设想与那些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以色列这片“应许之地”的犹太人搭不上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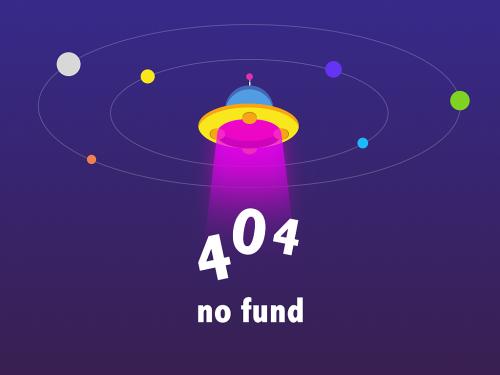
以色列民众5月13日庆祝耶路撒冷日,纪念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从外部撼动以色列固然暂无可能,它的内部却存在一个比伊朗更大的威胁:一个日趋分化的社会。
“对外团结”与“内部分化”
来自欧洲的犹太人是这个新国度的规划者和治理者,他们中的精英为这个崭新的犹太国,奠定了一种类似凯发k8国际娱乐官网入口的文化的精神。凭着这种精神,以色列如今已发展成世界上名列前茅的高科技国家。
那些来自欧洲之外地区(摩洛哥、伊拉克、也门和波斯等地)的被称为“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他们则被大卡车带到边远地区落户,譬如南部的内盖夫大沙漠。这些地区至今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人数上却占以色列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在以色列的历史和文化中,他们的贡献基本被忽略不计,既鲜有人知道,亦很少人问津。他们之中虽然也出过企业家,甚至还有人当过政府部长,但尚无人登上总理宝座。
以色列的对外“招牌”,依然是欧洲犹太人在共产主义和复国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带有某种乌托邦性质的的社区模式“基布兹”(kibbutzim)——类似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和“合作社”。政府为每个非法滞留在约旦河西岸的欧洲裔犹太人所投的钱,要多于米兹拉希犹太人三倍以上。
外界都知道,以色列除了卓有成效的国家建设,还有驱赶巴勒斯坦人的不光彩历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以色列国内那些米兹拉希犹太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生活在类似特拉维夫和海法这类经济中心的世俗犹太人,思想比较开放,与落后地区民众以及原教旨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如今,极端保守的宗教人士不仅主宰着以色列的信仰领域,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譬如,他们要求在安息日停止所有的公共生活,那些世俗化的地区也不例外。如今,每逢宗教节日,全国的公交车和铁路一律停止运营。极端宗教家庭的出生率颇高,很快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除了他们,人口快速增长的还有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政府以前虽然曾加大融合力度,但这部分以色列人仍被犹太人视为“异类族群”。政治的民族主义化和宗教化趋势,也加剧了这种社会的内部分离倾向。
根据联合执政的利库德党和“犹太家园党”今年提出的一个法案,将允许“纯犹太”社区的存在。这类政治主张在以前会被划为极端和边缘的范畴,如今却成了议会中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些政治主张只会疏远那些生活在经济中心城市,比较开明的民众与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在以色列,每个社会阵营几乎都拥有自己的政治党派,本届内坦亚胡内阁中,就由六个党派联合执政。
以色列已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但人们对何谓“新犹太人”,依然语焉不详。由于缺乏统一的认同感,以色列国内真正关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人并不多。
从军事角度看,以色列已成功控制巴勒斯坦人,但这种长期占领别人土地的状态,不仅对民主体制有害,还会造成另一个层面的分化: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犹太裔美国人越来越疏远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对此一方面无所作为,同时指责犹太裔美国人的批评是自我仇视。这种做法非常短视,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国。
有道是,外敌当前,内部团结。正是这一次次的生存危机和外部干扰(包括这次的伊核危机),才把以色列的内部分化掩盖和延缓下来。这也是内坦亚胡数年来大力渲染伊朗威胁的真正原因。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位了,留下的以色列除了是个军事强国,或许也是个分裂的社会。
“受害者”与“施害者”
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成果,欧洲的犹太人从1791年起开始享有公民权利。这一进步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得到逐步完善。
当年拿破仑把犹太人从所谓的“隔离区”中解放出来,结果是,他们一方面的确有了融入基督教社会的机会,另一方面却必须直接面对基督教徒出于宗教原因对他们的排斥。隔离时,两者矛盾对立并不突出;融合时,格格不入才变得明显起来。
1879年,普鲁士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冯·特莱奇科(heinrich von treitschk)的那句“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在欧洲引发一波排犹高潮。1895年,反犹主义者吕格(karl lueger)以绝对多数当选为维也纳市长;此前一年,就职于法军总参谋部的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其犹太人身份,被判“叛国罪”而终身流放,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虽然他数年后获平反昭雪,但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国保守的教会人士和保皇派势力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反犹攻势,质疑犹太人享有普通公民权利这一共和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追求犹太复国的锡安主义(zionism)应运而生,目的是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开始时,欧洲的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相对富裕和有文化的阶层,并未真正热衷于这项事业,但后来纳粹的灭绝政策给他们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结果。他们做梦都未想到,偏偏是德国这个此前曾向遭迫害的中东欧犹太人慷慨施以援手,以及在文化上与自己紧密相连的国度,会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
有人说,现在的以色列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指的是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镇压、迫害和打击。了解犹太历史的人,应该理解以色列人为何如此团结,那是因为他们的生存始终受到周围的威胁。同时,根据上一段落中描述的状况,我们也有理由担心,这种迫于外部压力和侵害的环境一旦消失,以色列国内的自身矛盾也许会迅速凸显。
诚然,以色列立国第二天即遭到阿拉伯人的围剿,所以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缺乏信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自己已经强大到无人可敌的时候(如今的以色列基本如此),应该给别人留活路。以色列的侍强霸道和美国人的一味袒护,或许正是西方社会“反犹思潮”重新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或质疑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反对以色列人违反国际法强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不等于反犹。我们可以反对“反犹主义”,但不能因此而失去批评以色列政策的权利。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两者经常混为一谈:谁批评以色列,谁就很容易被扣上反犹这顶帽子。
还有,犹太人历史上的不幸遭遇,并不是“天下曾负我,我亦负天下”的理由。按理说,反复遭受厄运打击的人,更应该理解别人的相同苦楚,更不该对他人施加同样的危害。
可惜,旧的不幸正在被新的不幸所取代,原先的受害者现在似乎已成为施害者。犹太人应该知道,以往本民族所受过的冤屈和付出的牺牲,不能成为自己蔑视国际法的“永久免罪符”。以色列有生存权,巴勒斯坦人同样享有生存权。以各种借口阻止巴勒斯坦人享有这一权利的言行,都是产生新暴力和不公平的温床和助推器。
三年前去世的德国作家格拉斯(gunter grass)曾因一长一短两部作品闻名于世:长作品是小说,叫《铁皮鼓》,它给格拉斯带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短作品是一首诗,叫《不得不说的话》,引发一场关于以色列的政治激辨。
他在这首诗中写了这么一句话:“核国以色列正在危及本就脆弱的世界和平?”或许,格拉斯本人也担心这么说有些过头,所以在句子后加了个问号,以冲淡这句话的爆炸性意味。但他的这首诗一经发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性效应。
或许,他想要的正是这种效应。总之,这句针对以色列所说的话,差点让这位伟大的作家“晚节不保”。但是,现在重温他那些“不得不说的话”,再结合当下中东的局面,读者或许更能切身感受到他当年压抑许久的心境,更能体会他真正想要说的话。
格拉斯这首诗有两个重点:一、之所以沉默那么久,是因为他的身份——来自曾经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发表后又披露出他自己曾参加过俗称“黑衫军”的“武装党卫队”;二、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把以色列和伊朗一视同仁,将两国双双置于国际核能机构的监督之下。
格拉斯说错了吗?没有。但为何至今难以实现?
特朗普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前,内坦亚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被记者追问以色列是否拥有核武,他最后的回答是:“你可以尽情地猜测,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以色列不会威胁和毁灭任何国家。”如果伊朗也说它即便拥核,也保证不主动打击其他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会接受它生产核武器吗?
德国社民党和左派党前主席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日前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明确指出:“我驳斥美国发动的战争是服务于民主的谎言。”他这话虽然是点名特朗普,但针对的却是那个“谎言”本身。
而这些恐怕才是更该引发我们深思的问题。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