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3近代华族
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任务本应是废除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建立新型人际关系。但是,倒幕运动是由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级武士联合发动的,他们后来成为明治政权的核心。在贵族传统久远、身份意识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对贵族的剥夺,并废弃封建身份制度。如有学者所言,“与其说要否定以前的身份等级关系,还不如说是为了回避国内的阶级对立,进行身份关系的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就是,以皇族、华族、士族、平民这样的新“四民”身份取代了旧有的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制度,其中仅次于皇族的华族就是把前近代的贵族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存在的新贵阶层。
1869年6月,明治新政府在命令各藩“奉还版籍”的同时,发布行政官布告:“出于官武一途,上下协同之考虑,自今起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据此,142家公卿、285家大名,计427家统统被称作“华族”,习惯上称公卿出身者为“公卿华族”,大名出身者为“诸侯华族”。1871年,在废藩置县前,为了彻底切断大名与各旧藩的联系,新政府命令诸侯华族全部从各地移居东京,此后,公卿华族也从京都迁居东京。“华族”这一称呼本是前近代公卿贵族中“清华家”的别称,从华族诞生之日起,公卿与大名这两大曾经形同水火的贵族终于在东京互相面对,彻底告别公卿与大名身份,变成“天皇的华族”。
在华族制度成立之初,明治政府除了建立机构对华族进行管理之外,并没有就华族在未来国家发展中居何地位有深入的考虑。面对自由民权运动中社会舆论对华族的批评以及明治十四年(1881年)后,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压力下承诺于1890年开设国会,制定宪法,为保障将来开设国会后天皇大权不落到民权派手中,明治政府深感建立以华族为主的贵族院的必要,为此专门派遣伊藤博文等人于1882年3月起专门赴欧洲,进行宪法及诸制度考察,重点了解欧洲各君主国家的贵族制度。1883年8月份回国后,伊藤博文在宫中设制度调查局,为实施立宪政治做准备,同时着手整顿华族制度。1884年7月7日,明治天皇发布《授荣爵之诏》:“华族勋胄乃国之瞻望也。宜授予荣爵,以示宠光。文武诸臣,翼赞中兴之伟业,于国有大劳者宜均升优列,以昭殊典。兹叙五爵,其此为秩。望卿等忠贞益笃,尔等子孙世济其美”。同日,宫内卿伊藤博文以“奉敕”的形式,颁布“华族令”对华族授爵,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依据“叙爵内规”予以实施。据《授荣爵之诏》及“华族令”,1884年7月7~8日,共有509家被授予爵位,其中公爵11家、侯爵24家、伯爵76家、子爵324家、男爵74家。“华族令”的颁布及1884年的授爵,标志天皇制华族制度最终确立。此后,到日本战败为止,先后对1 017家授予爵位。
(一)公卿华族
在1884年授爵中,对旧公卿贵族是按过去家格授予爵位的。家格最高的五摄家被授公爵;九家清华家被授侯爵;大臣家、羽林家、名家中的一部分(担任大纳言较多的家族)被授伯爵,其余被授子爵。明治维新后,从寺院还俗的贵族子弟(亦称奈良华族)及大神社的世袭神官等被授男爵。总体来说,对旧公卿的授爵高于大名,颇有为幕府时代受武家压制的公卿贵族恢复名誉的味道。此后又陆续有原公卿的分家被叙爵位但基本上是男爵。至战后华族制度被废除时,先后共有公卿贵族出身的华族210家,加上僧家、神官等在内共有231家,占华族总数的23%。
(二)诸侯华族
在1884年受爵的旧大名即诸侯华族中,仅有作为德川宗家的德川家达及因倒幕之功而“对国家有伟勋”的长州、萨摩旧藩主毛利元德、岛津久光、岛津忠义被授公爵;旧御三家及至戊辰战争时家领在15万石以上的旧大名被授侯爵;包括德川御三卿在内的15万石以下5万石以上者被授伯爵;5万石未满的旧大名被授子爵。至战后华族被废时,先后有旧大名出身的诸侯华族395家,占华族总数的39%,远远多于公卿华族。
(三)勋功华族
在华族中,还有391家勋功华族,即《叙爵内规》规定的“一新后列华族者,对国家有功勋者”被授男爵爵位,占华族总数的38%,基本与诸侯华族持平,这部分人是近代新贵中的新贵。华族本来是具有公卿及诸侯身份的人,1869年华族初创时,将倒幕维新的主要力量——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士族排斥在外,引起有功士族们的不满。1884年7月“华族令”颁布并授予爵位时,长州藩士出身、掌握授爵实权的宫内卿伊藤博文力主对30名士族出身者作为勋功华族授予爵位,有29名出身于上述四藩,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萨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西乡从道、寺岛宗则、松方正义等人都被授予伯爵。19世纪90年代,进入勋功华族大量叙爵时期。1895年对41人授予爵位,其中30人是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军人。1907年授爵的75人中,有69人是日俄战争中的军功人员,因日俄战争之功授男爵的文武官员前后总计96人[25]。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因在日俄战争中率联合舰队打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之功,被破格授予伯爵。在两次战争中,还有不少人因功升爵。如甲午战争后,原为伯爵的伊藤博文、大山岩(陆军)、西乡从道(陆军后海军)、山县有朋(陆军)升爵为侯爵,原为子爵的桦山资纪(海军)、野津道贯(陆军)等人升为伯爵。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又从侯爵升为公爵。这个昔日的下级武士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便与其旧主——长州藩主毛利元德平起平坐了。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本庄繁、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均因“满洲事变”之功被授予男爵。由此可见,勋功华族的叙爵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甲午战争以前的勋功华族或是军功人员或是官僚,皆是“官”,而与“民”无关,官尊民卑显而易见。1896年,日本财阀的两大巨头——三井总家长三井八郎高栋及三菱财阀总家长岩崎弥之助、岩崎久弥叔侄被授予男爵,从此开始有实业家及科技文化界人士获得男爵爵位,但数量有限,到二战结束,只有实业家18家,科技文化界人士15家。
华族是在前近代贵族制度与等级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近代新贵族。虽然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旧的贵族特权被废除,但是在近代国家政权的刻意保护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特权。如根据1889年的“贵族院令”的规定,公爵与侯爵年满25岁(1925年改为30岁)自动成为贵族院的终身议员。伯爵、子爵、男爵由同爵之间互选的方式各选出五分之一,任职期限为七年,大大超过众议院议员的四年任期;在教育方面,华族子女可以进入专设的学习院学习,如果帝国大学学生不足,还可以直接升入帝国大学,故华族可以轻易得到帝国大学的学位;在经济方面,为保证诸侯华族在秩禄处分中获得的巨额公债不流失并实现增值,专门建立了国立第十五银行(又称华族银行),颁布“华族世袭财产法”(1886年)保护华族的财产完整;发布“旧堂上华族保护资金令”(1912年)保障旧公卿华族的生活,等等。
概而言之,近代华族是将旧公卿、大名两大不同贵族统合而成,带有浓厚的身份制度色彩。出于巩固近代天皇制政权及日清、日俄战争的需要,官僚、军人等也因其“勋功”被列入华族行列,在前近代家格门第基础上,注入近代实力主义,从而产生近代新贵族。在贵族重组的过程中,近200万武士被剥夺所有特权,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近七百年的武士阶级归于解体,武家贵族只有昔日大名被保留贵族身份,公卿贵族重得荣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身份色彩强烈、徒有荣誉外表的华族日益走向衰落。据1919年的统计数字,在当时926家华族中,有569家无业或依靠财产收入及恩给为生,成为寄生阶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军事占领,并实行民主化改革。1947年5月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对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据此,华族制度连同其大本营——贵族院被废除。承载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旧贵族与78年近代史的新贵族——华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4贵族传统与日本的国民性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社会化过程中,基于长期所处的历史与风俗而形成的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性格特点在内的倾向性选择。国民性的形成,不仅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社会结构也会对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是贵族制社会结构的典型,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因此,日本的国民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笔者过去曾就日本国民性中的“实用主义”“集团主义”“等级秩序”等进行过探讨,这里仅简要分析贵族传统对国民性的影响。
(一)身份至上
日本的贵族中最有代表性、而且历史最悠久的是公家贵族。在律令制时代,贵族凭借所谓高贵的家系成为权力的核心,拥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垄断了朝廷的最高官职。从延喜元年(901年)到镰仓幕府建立(1185年)的总计395名公卿中,有265人是藤原氏出身者,占67%,居压倒优势;此外还有源氏79人(20%),平氏24人(6%),大中臣(7人)等10家贵族总计27人(7%)。在公家贵族鼎盛的时代,已经形成对高贵身份及高贵家系的尊崇。家格这种体现贵族等级的形式也引起其他社会阶层效仿。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公家贵族逐渐衰落,直到幕末,基本上没有了实际权力,而且生活贫困潦倒,但是幕府及武士在近七百年中并未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剥夺,而是在身份等级制度方面以公家贵族为学习的样板。如公家贵族在不同的场合要穿特定的服装,武士也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着装样式,武士的服装不仅区别于贵族,更与百姓完全不同,其内部还有按照不同等级的严格区别。再如,律令制度下的官位在进入幕府时代后逐渐成为有名无实的虚衔,但武士们不仅要扩张自身的军事实力,也要拥有具有权威及名誉色彩的官位,藉此表明自身跻身于贵族的行列。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期统一天下后,不仅担任关白、从一位太政大臣,而且以律令官制为基础,授予诸国大名武家官位。丰臣秀吉去世时,拥有全国最高官位者竟然是武家出身的正二位内大臣德川家康,此后又升至从一位太政大臣。德川幕府建立后,仍然把公家官位体系作为统制大名的手段。这一做法体现出武士对身份、荣誉和地位的追求。同时,身份制度被德川幕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日益巩固、完善,身份制度和身份意识渗透到近世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
明治维新以后,华族制度的建立是身份制度在近代的延伸,一方面新政府需要身份制度维护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否认身份制的存在,“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以前所属的地位,上升至更高一点的地位”。1869年华族初创之时,武家社会除大名之外的所有武士悉被列为士族,这引起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维新功臣的强烈不满。长州藩士出身的明治政府领导人伊藤博文认为,“封建武门之世,士族位于平民之上,教育有素,气节有为之人多出其间,应作为贵族之一部,拔其中之人与华族俱列元老,以收其报效”,“今士族平民之有功者立于愚笨华族之下风,只望任国会(下院)议员,此种做法现在与今后都难得有功者之人心”。于是,在以藩阀为主的明治政府主导下,1884年颁布“华族令”并对华族叙爵时,以伊藤博文为首的30名武士出身者被授予爵位。此次叙爵使士族出身者看到了跻身贵族的希望,自荐、他荐者纷至沓来,到1887年,又先后对55名士族出身者授予爵位,此举被称作“圣恩大贱卖”。
1871月10月,明治天皇召见全体华族的户主,并发布鼓励华族去海外游学的敕谕,其中指出:“华族在国民中居贵重之地位,众庶之瞩目之处,固然成其履行之标准”。这是明治政府对华族的定位,承认华族是国民中的最上层,是近代新贵族。在战后民主改革过程中,贵族制度在外力压力下走向终结。这种终结是制度与法律上的废除,而不是对贵族人身的消灭,贵族后代还在,贵族意识犹存,看重世袭的权力、崇尚权威的心理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社会往往不是以个人能力,而是以公认的家系、身份作为判别人的社会地位、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尤其是在人事制度与政治活动中,“任资唯贤”往往重于“任人唯贤”;在国会选举中,政治家的后代大多数都能稳操胜券,于是就产生了独具日本特色的表现为“族议员”的世袭政治。
(二)注重传承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对制造业“工匠精神”的讨论,作为制造业大国的日本的“工匠精神”及与此相关的长寿企业颇受推崇。日本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长寿人口国,也以“企业长寿大国”闻名于世。即使在历史上屡经战乱、经济危机和大地震的打击,仍有创业至今超过百年的企业25 321家,超过二百年的企业3 937家,是世界上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不独长寿企业,在文化艺术领域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家族,如花道池坊流家元从15世纪中期开始到如今已达45代,歌舞伎市川流宗家市川家团十郎从17世纪后期至今传了12代;茶道里千家家元从16世纪传承至今已16代。
从古到今,日本的企业及艺术流派的久远传承是通过家业的世代延续得以实现的,其根源在于日本特有的家制度。日本的“家”不单是男女结婚后生儿育女的具体生活集团和生活场所,还是“超越世代经营一定的行业乃至为换取恩给和俸禄而提供服务的集团,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一个企业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家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所谓家业,不仅指房屋土地、金银财宝,还包括人们赖以谋生的技能。这种家制度正是起源于公家贵族。在律令制时代,贵族的所有政治、经济特权都是通过家来世袭地维系着的,官职也是如此。9世纪开始大贵族藤原氏逐渐垄断朝政后,无法获得高官高位的中下级贵族不得不在一些特定的专业技术领域,通过一技之长在朝廷中立足,久而久之,贵族的家便成为从事朝廷公务的机构,如菅原氏、大江氏掌管文章道,安倍氏垄断阴阳道,和气氏、丹波氏把持医道。在这种情况下,贵族的继承就具有了延续家业的意义,经过人们的刻意维护,贵族的家系得以脉络清晰地延续下来。
贵族的传承最重要的莫过于采取独特的继承制度,在实行长子继承的同时,不排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进入家庭。有学者这样评价日本的继承制度,“除了天皇家族之外,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有与异姓混血的历史”,“即使再出色的家族,也不可能把血缘关系上溯到数代以前,因为家系和血系是很难一致的”。这里出现了“家系”和“血系”两种概念,“家系”是家业延续的系列,具有社会性;“血系”则是血缘繁衍的系列,只有家族性。在现实中,任何家族如果排斥非血缘者继承的话,都无法持续长久。一个家族家系的延续往往与数个家族血系的延续有关。由于存在养子继承的情况,不少家族即使家系延绵,而实际的血缘关系已然面目全非。
以家业为中心,实行长子单独继承,注重纵式延续,贵族的家制度对后来的武士家庭与町人家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武士的家业是为了得到赖以生存的俸禄,必须与主人结成牢固的主从关系,为主人尽忠奉公;商人的家业是指他们从事的商贾买卖及经商的经验,乃至店铺的信誉。艺能人的家业就是所从事的技艺。所以,不论对哪个阶层的人来说,家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家业繁荣昌盛、长久延续是家的终极目的和家族成员为之奋斗的目标。日本人把家视为一个生命体,认为家是从祖先那里传到自己手中的,自己的责任是将其维护周全,再完整地交给后代。每一代继承人都肩负着家业发展与延续的使命,为之付出,为之努力,期盼家业在自己手中发扬光大,至少也要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不能在自己手中衰落、断绝。这便是当今日本大量存在长寿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文化艺术领域来说,因为有人专门把某种被称为“道”的艺术作为一个家族的事业来做,珍惜它,保护它,研究它的精髓,想办法让它发展。所以,以茶道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道”才能够相传数百年而不辍,传统文化也因此得到有效保护。
(三)双重性格
早在战后初期,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就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描绘了日本人的双重人格: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这种双重性人格究竟从哪里来?在从不同角度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时候,似应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贵族的影响。
由于日本历史上不推崇以暴力实现改朝换代不仅皇室连绵延续126代,贵族也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在一定意义上说,高高在上的贵族是民众的楷模,在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都会对民众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同“废藩置县”后明治天皇对华族中的藩知事发布敕旨所言:“华族立于四民之上,为众人之标的”,标的就是榜样。有学者在阐述16世纪以后英国贵族的情况时谈到,“贵族的‘高贵’品质是由高贵的血统、优秀的品行、优越的生活方式、卓越的社会贡献等诸多因素集合而成”。日本最初的贵族——公家贵族的“贵”除了体现在“高贵”的血统——家系以外,还非常注意培养与贵族身份相应的教养。如,10世纪中期的公卿藤原师辅(909-960)在病逝前留下遗训,即“九条殿遗诫”,其中仅就每天早晨的生活起居就定下诸多规矩:
起床后先默诵七次自己所属之星宿名称;次对镜子看容姿;次看历日知吉凶;次用牙签清理牙齿,洗脸;次暗诵佛名及日常尊崇之氏神;次记昨日发生之事;次喝粥;次梳头(三天一次);次剪手足指甲(丑日剪手指甲,寅日剪脚趾甲);次择日沐浴(五天一次);次有出仕之事,即服衣冠,不可懈怠。
这11条都是早晨起床之后要做的事情,其中有5条与个人形象相关,说明此时贵族对此十分注重。其他几条有的涉及到神佛及阴阳道信仰,有的是通过每天写日记进行文化上的修炼,有的是对上朝时服饰着装的要求。“九条殿遗诫”在当时公家贵族中流行很广,表明贵族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追求也在提升。公家贵族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尽管贵族子弟年满21岁即可根据荫位制度得到相应的官位,但朝廷要求“五位已上子孙,年廿以下者,咸下大学寮”,“令习读经史,学业足用,量才授职”。因此,平安时代的贵族在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贵族文化,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达到此后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超越的顶峰。
武士依靠武力在朝廷之外建立了幕府政权,从时间上看,武家贵族掌握实权比公家贵族时间长,人数上比公家贵族多很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与平民百姓的接触和联系远远超过偏居京都的贵族,故武家贵族的核心价值对民众的影响要超过公家贵族。与注重文化和教养的公家贵族相比,长期以战争为业的武士的立身之本是精于武艺。在身份制度下,武士作为“三民之长”而存在,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尊奉的模范。不仅战争年代要精进弓马之道,即使到了天下偃武的江户时代,大部分武士成为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而历史的惯性令他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尚武精神和杀伐风气。武士出行进退,腰佩双刀,在面对平民的无礼冒犯时可以将其“斩杀后弃之不管”(斩舍),而且不需承担责任(御免)。1869年,当有欧洲留学背景的森有礼在公议所提出要“改变粗暴杀伐恶习”,建议废刀时,居然被罢免了在政府担任的职务。明治政府下达“废刀令”是迟至1876年的事情,反映出武士对尚武与杀伐的留恋。近代以后,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或变身政府官员、学校教员、军人和警察,或接受近代教育实现转型,成为新社会中的精英,大多数人陷落为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底层。在此过程中,武士伦理得以扩散到全社会。尤其是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武士的尚武精神被极力推崇,不仅自己在战争中要视死如归,也把“粗暴杀伐恶习”用于对付被侵略国家的国民,制造了无数杀人惨案,给人类和平带来巨大灾难。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及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日本被改造成民主国家,但是社会及学校、家庭一直坚持对国民自幼进行各种磨难教育,其背后仍然可以看到武士的影子及对尚武精神的坚守。
综上所述,贵族是日本身份等级制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仅次于皇室而居于社会的顶层。凭借所谓高贵的家系及优越的社会地位(公家贵族)、特有的军事功能(武家贵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掌握社会主导权,经过对贵族的重组,在近代社会依然作为上流社会而存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族的文化与教养和武士的尚武精神,造就了日本国民的双重性格:既有彬彬有礼、讲究礼仪的一面,也有冷酷无情、野蛮好战的另一面。
作者单位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谈起贵族,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欧洲的贵族。实际上在东方国家日本也曾经拥有历史悠久的贵族,直到战后民主改革时才被废除,其传承之久远,远在欧洲贵族之上。要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不能忽视贵族的存在,首先要对贵族的规模、构成和变动情况有所了解。贵族是具有特权的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其身份由血统与门第决定;二是世袭地存在;三是“在成长为贵族的过程中,还需要被赋予某种高贵性的东西,这就是官位”。在日本,贵族并不是后世史家赋予前人的历史概念,而是从古代一直延绵存在到战败的特定的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贵族居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1公家贵族
“贵族”一词初见于日本文献,是在成书于14世纪后半期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中,在该书第1卷“后醍醐天皇治世事”中有“承久以来,储王摄家之间拥有相当理事安民之器之一位贵族,下镰仓,任征夷大将军,武臣皆事拜趋之礼”,但从律令时代已经开始把居高官高位者称为“贵”了。最早具有贵族身份的是律令时代朝廷中的高官,其前身是大和时代的豪族。由于这些豪族不断挑战欠缺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天皇的权威,甚至操控天皇的废与立,645年,皇子中大兄与权臣中臣镰足联手发动“乙巳之变”,铲除专擅朝廷的苏我氏势力,并在其后实施一系列改革(大化改新)。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削弱豪族势力,加强皇权。但如同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所言,“日本制定律令的时期,虽然在绝对年代上与唐朝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就社会发展水平而言,决不能说处于相同的时代。我的结论是,将之比拟为汉朝最为恰当”。宫崎市定所表达的是,律令时代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日本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努力只是对唐朝制度的模仿,旧豪族并没有被消灭,有些新贵族本身即与旧豪族一脉相承,例如,平安时代权倾朝廷的藤原氏就是中臣镰足的后代。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贵族在律令官僚体制下成长为制度化的特权阶层,有几项标志性的制度出现。
一是《律令》对贵族有了明确的界定。先有“名例律”之“六议”条曰:“议贵,谓三位以上”,后有《令义解》之“户令”中“依律,称贵者,皆据三位以上。其五位以上者,即为通贵”的解释,据此,在当时从正一位到少初位下总计三十阶的官员中,只有五位以上才被列入贵族范围,其中三位以上是高级贵族,四五位是中下级贵族,六位以下只作为下级官员存在,没有贵族身份。
二是模仿唐朝制度,颁布“衣服令”对贵族的着装做出明确规定。诸臣在重大祭祀仪式时要按位阶穿礼服,上朝公务时要穿朝服。无位官人及平民,在朝廷公事场合要穿制服,“皆皂缦头巾、黄袍”。据此,贵族有了区别于平民百姓的外在标志。
三是朝廷任官实行“官位相当制”。所谓官位,包括官与位,“职掌所事,谓之官,朝堂所居,谓之位”。获得官位的顺序是“凡臣事君,尽忠积功,然后得爵位,得爵位然后受官”,即先通过侍奉天皇及与天皇关系的远近获得位,再根据位得到官职。“阶贵则职高,位贱则任下”。在“官位相当制”下,朝廷的重要官职完全由贵族担任。
四是荫位制度,这是对贵族的传承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制度。与下级官员25岁以上才有机会叙位相比,贵族子弟年满21岁就能根据父祖的恩荫得到官位,贵族中最低的从五位官员的嫡子可以荫位从八位上,三位以上贵族更可荫及孙辈。而没有贵族家庭背景的下级官员,从官位三十阶中最低的少初位下开始,至少需要16年至32年时间才能晋升到从八位下。“五位以上子孙,历代相袭,冠盖相望”的世袭社会因此得以形成。
那么,律令时代有多少贵族呢?据日本学者考证,在奈良时代的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二年(750年),五位以上贵族共有200名左右,此后不同时期分别有减有增,称德天皇时期(764-770)达到279名,奈良时代末的桓武天皇时期(781-806)又减少到263名。进入平安时代,由于官职家业化和世袭化的发展,五位以上贵族进一步降到150名左右。按照日本人口学家鬼头宏的推测,725年日本的人口大约有451.22万人,到平安时代中期,增至644.14万人。姑且按照200名贵族及每户五口人计算,奈良及平安时代贵族及其家属总计为1 000人左右,那么奈良时代贵族及其家属在451.22万总人口中仅占0.022%。平安时代人口增加,贵族不增反减,在644.14万人口中的比例降至0.016%。从平安时代起,律令官制中最高官职的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与令外官的大纳言、中纳言、参议等高官统称为“公卿”,后来“公卿”与“公家”及“贵族”几乎成为同义语。到镰仓幕府时期,根据贵族内部的等级确定的“家格”逐渐固定,依次分为摄关家、清华家、大臣家、羽林家、名家、半家,至安土桃山时代共有64家。
奈良、平安时代是公家贵族的黄金时代。进入武家社会,朝廷衰落,天皇在国家政治体制中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公家贵族失去往日的权利。皇室都财政困难,沦落得连即位大典也难以保证及时举行,公家贵族更是窘迫不堪。江户时代包括皇室、公家贵族、寺社等在内的公家的总收入只有12~13万石,仅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名。随着德川幕府在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持,皇室生活有所好转,上皇、法皇的院御所多有新设,服务于此的公卿贵族在原有64家基础上通过建立分家而增加到137家,即摄关家5家,亦称“五摄家”;清华家9家;大臣家3家;羽林家66家;名家29家;半家25家。确定家格的依据是血统、家系及与皇室、朝廷的亲疏关系。家格是不可改变的,且世袭地存在,由此产生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制度——“极位极官”,即某家某人能够担任的最高官位和官职。摄关家垄断公家社会的最高官职,交替担任摄政、关白;地位仅次于摄关家的清华家担任太政大臣并兼任近卫大将;大臣家任大纳言并可升官至内大臣;羽林家可担任参议、中纳言、大纳言并可兼任近卫中将、少将;名家可以经侍从、辨官、藏人头而升任大纳言;半家准照羽林家、名家而升进,可任文、武双方官职,官至大纳言。这样的家格不仅是整个封建时代任命官职的标准,也是明治时代对公卿华族的叙爵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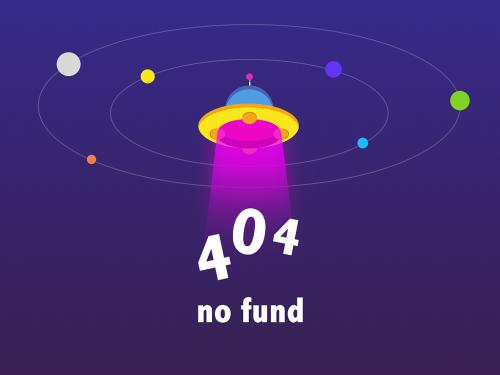
2武家贵族
随着贵族制度的发展,从平安时代开始,中央政权的核心逐渐缩小,最后大贵族藤原氏一家以外戚身份在朝廷中占据压倒优势,在长达两个多世纪中专擅朝廷。平安时代晚期,藤原氏的外戚血缘链条出现断裂,日本进入退位天皇作为“治天之君”继续掌握朝廷实权的“院政”时代。太上天皇依靠武士扩大自己的权势,与藤原氏抗衡,武士得以乘机崛起,从最初担任军事、警察等职务,到出入于朝廷、贵族之间,最终于12世纪前期在镰仓建立了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幕府,在公家贵族依然存在的同时,武家成为此后近700年中事实上的权力主宰。尽管最初的武士集团首领源氏与平氏都有贵族渊源,但是大多数武士却长期处在兵农不分的状态,直到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推行“兵农分离”政策以后,真正意义的职业军人集团才逐渐形成。从1615年“元和偃武”开始,日本进入和平时期,武士的职能悄然改变。
德川幕府建立后,武士从过去的随从主人德川氏戎马作战打天下,变成维护德川将军的统治坐天下,旗本与御家人全部住在江户,担任幕府各种公职。“番方”是具有军事与警备职能的机构,负责江户城的警备与将军护卫。“役方”是处理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的文官机构,在老中与若年寄之下,由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构成幕阁的中枢。德川家臣团在幕府建立初期以骁勇善战著称,但随着城居而逐渐都市化、贵族化,加上江户时代长时间天下太平,武士从军人转化为行政事务官员,军事素质下降,战斗意志消退,到幕府末期,其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各藩的行政体系也与幕府基本相似,藩士被安置于藩都居住,管理藩内的各项行政事务。虽然江户时代天下太平,武士的军事职能已被削弱,但幕府为提高权威,抑制大名的势力,在石高制基础上确定大名的军役负担量。所谓军役,即在发生战事时,大名要为幕府提供兵力、武器、马匹等等,但是自从1615年消灭了丰臣秀赖后,再无大规模战事。在以和平为主的环境里,幕府继续要求大名以准军役的形式奉公于幕府,如将军出行之时的随从与警卫;接收被改易大名的城池及新藩主到来之前的警备与管理;江户城的警卫、防火;承担城郭修建、治水工程等等。这些“军役”消耗了大名们的财力,也泯灭了武士们的战斗意志。
江户时代的武士究竟有多少人?这需要按照幕藩体制分别加以说明。
(1)从幕府层面来说,旗本与御家人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这两部分人被统称为“直参”。旗本的原意是本营,即战阵中大将所在之处,后具有将军旗下、守卫将军的亲卫军之意。一般将旗本定义为1万石以下、有资格谒见将军(御目见)的武士。御家人与旗本虽同是将军的直臣,但是没有谒见将军的资格。在江户时代,对于武士来说,能否谒见将军是武士身份等级的标志,御家人也被称作“御目见以下”,或直接称其为“以下”。御家人占将军直属家臣团人数的七成以上,他们在战场上是徒士(徒步作战的武士、步兵)身份,平时作为“与力”“同心”等职员从事幕府行政部门的事务及警备工作。御家人虽然号称是1万石以下的直臣,实际上不像旗本可以得到领地收入,一般只能领到不多的禄米,老资格的御家人俸禄不过200多俵,是下级武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旗本与御家人是幕府与德川将军的近卫军,在“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后由明治新政府接管的旧幕臣中,有布衣(叙六位的旗本)872人,御目见以上5 972人(旗本),御目见以下26 000人(御家人),总计32 000多人。
(2)从地方即藩的层面来说,江户时代的大名,特指持领地1万石以上者,其领地和统治机构叫做“藩”,意即幕府的屏障。要得到大名的身份,首先要获得幕府将军下发的“朱印状”,得到将军的承认。各地大名必须宣誓效忠将军,遵守幕府法规,听从调遣。在江户时代初期,对原有战国大名进行大规模改易后,为了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将各地大名按照与德川幕府将军关系的亲疏分成等级严明的三种类型:
亲藩大名是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大名的藩领,即由德川将军子孙所建的藩。其中家格最高的“御三家”是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三个儿子建立的尾张藩(位于今名古屋)、水户藩(位于今茨城县)、纪州藩(位于今和歌山县)。江户中期以后,鉴于德川宗家和御三家的血缘逐渐疏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位1716-1745年)时模仿其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创设了田安德川家及一桥德川家,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时又让其子创立了清水德川家。此三家的家主都被朝廷授予从三位、担任相当于“卿”的官职,故被称为“御三卿”。御三卿是作为德川将军家的成员而存在,故未单独立藩,因分别居住在江户城内的田安门、一桥门、清水门附近得名。在德川宗家血缘中断之时,御三卿与御三家一样负有提供继承人人选的义务。在御三卿与御三家之外,还有德川将军支系的藩领,称“御家门”。御家门可以使用德川家家徽“三叶葵”,使用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前的本姓“松平”。总之,亲藩是德川将军统治的核心,作为将军的藩屏而存在,居要位、要地。到幕末,共有23家。谱代大名是世代追随德川家的老臣的藩领。德川幕府建立后,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对原有的战国大名进行大改组。在改易旧大名的同时,德川家康对自己的拥趸进行论功行赏,将亲信配置在全国的主要地区,到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时,大名的战略配置基本完成,终德川幕府,共有谱代大名145家。
谱代大名是德川将军的亲信,在大名中人数最多,被分封全国要地,以拱卫幕府将军,是幕政运营的中坚力量。但幕府对谱代大名也加以提防,不允许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能力,大部分谱代大名的领地都在5万石以下,尤以二三万石小大名居多。
外样大名是与德川将军关系疏远的大名的藩领。他们多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时代的旧大名,以及关原之战后才臣服德川将军的大名,共有98家。这部分大名里不乏实力雄厚者,如第一外样大藩加贺藩前田家领加贺、越中、能登三国,石高102.5万石;长州藩毛利家领长门、周防两国,领地36.9万石;萨摩藩岛津家领72万石;肥后细川家领54万石,幕府对外样藩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承认他们拥有的领地,并给予他们一定礼遇,如有的外样大名在江户城中的席次甚至相对高于谱代大名。但实际上,幕府对外样大名持有深深的戒心,把有实力的外样大名都配置在偏远地区,将其严格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总之,德川幕府时期,各类大名共计266家。大名之下按一门或家老、组头、物头、平士、徒士、足轻、中间或小者这样的序列,安置于相应的岗位,管理藩内的各项行政事务,如外样大藩加贺藩仅在藩中担当会计工作的就有150人。从武士总体层面来说,由于江户时代没有详细的人口统计数字,武士的具体人数不得而知,但从明治初年的户籍统计资料可知,1872年武士及家属共有1 941 241人,考虑到在“王政复古”后有一部分人自愿“归农”的因素,可知在江户时代约3 000万人口中,武士及其家属应该在2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在近270年时间里,不足人口7%的武士作为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军事贵族成为立于三民之上的统治者。
3近代华族
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社会改革任务本应是废除封建身份等级制度,建立新型人际关系。但是,倒幕运动是由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级武士联合发动的,他们后来成为明治政权的核心。在贵族传统久远、身份意识根深蒂固的背景下,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对贵族的剥夺,并废弃封建身份制度。如有学者所言,“与其说要否定以前的身份等级关系,还不如说是为了回避国内的阶级对立,进行身份关系的重组”。这种重组的结果就是,以皇族、华族、士族、平民这样的新“四民”身份取代了旧有的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制度,其中仅次于皇族的华族就是把前近代的贵族改头换面之后继续存在的新贵阶层。
1869年6月,明治新政府在命令各藩“奉还版籍”的同时,发布行政官布告:“出于官武一途,上下协同之考虑,自今起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据此,142家公卿、285家大名,计427家统统被称作“华族”,习惯上称公卿出身者为“公卿华族”,大名出身者为“诸侯华族”。1871年,在废藩置县前,为了彻底切断大名与各旧藩的联系,新政府命令诸侯华族全部从各地移居东京,此后,公卿华族也从京都迁居东京。“华族”这一称呼本是前近代公卿贵族中“清华家”的别称,从华族诞生之日起,公卿与大名这两大曾经形同水火的贵族终于在东京互相面对,彻底告别公卿与大名身份,变成“天皇的华族”。
在华族制度成立之初,明治政府除了建立机构对华族进行管理之外,并没有就华族在未来国家发展中居何地位有深入的考虑。面对自由民权运动中社会舆论对华族的批评以及明治十四年(1881年)后,政府在自由民权运动压力下承诺于1890年开设国会,制定宪法,为保障将来开设国会后天皇大权不落到民权派手中,明治政府深感建立以华族为主的贵族院的必要,为此专门派遣伊藤博文等人于1882年3月起专门赴欧洲,进行宪法及诸制度考察,重点了解欧洲各君主国家的贵族制度。1883年8月份回国后,伊藤博文在宫中设制度调查局,为实施立宪政治做准备,同时着手整顿华族制度。1884年7月7日,明治天皇发布《授荣爵之诏》:“华族勋胄乃国之瞻望也。宜授予荣爵,以示宠光。文武诸臣,翼赞中兴之伟业,于国有大劳者宜均升优列,以昭殊典。兹叙五爵,其此为秩。望卿等忠贞益笃,尔等子孙世济其美”。同日,宫内卿伊藤博文以“奉敕”的形式,颁布“华族令”对华族授爵,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依据“叙爵内规”予以实施。据《授荣爵之诏》及“华族令”,1884年7月7~8日,共有509家被授予爵位,其中公爵11家、侯爵24家、伯爵76家、子爵324家、男爵74家。“华族令”的颁布及1884年的授爵,标志天皇制华族制度最终确立。此后,到日本战败为止,先后对1 017家授予爵位。
(一)公卿华族
在1884年授爵中,对旧公卿贵族是按过去家格授予爵位的。家格最高的五摄家被授公爵;九家清华家被授侯爵;大臣家、羽林家、名家中的一部分(担任大纳言较多的家族)被授伯爵,其余被授子爵。明治维新后,从寺院还俗的贵族子弟(亦称奈良华族)及大神社的世袭神官等被授男爵。总体来说,对旧公卿的授爵高于大名,颇有为幕府时代受武家压制的公卿贵族恢复名誉的味道。此后又陆续有原公卿的分家被叙爵位但基本上是男爵。至战后华族制度被废除时,先后共有公卿贵族出身的华族210家,加上僧家、神官等在内共有231家,占华族总数的23%。
(二)诸侯华族
在1884年受爵的旧大名即诸侯华族中,仅有作为德川宗家的德川家达及因倒幕之功而“对国家有伟勋”的长州、萨摩旧藩主毛利元德、岛津久光、岛津忠义被授公爵;旧御三家及至戊辰战争时家领在15万石以上的旧大名被授侯爵;包括德川御三卿在内的15万石以下5万石以上者被授伯爵;5万石未满的旧大名被授子爵。至战后华族被废时,先后有旧大名出身的诸侯华族395家,占华族总数的39%,远远多于公卿华族。
(三)勋功华族
在华族中,还有391家勋功华族,即《叙爵内规》规定的“一新后列华族者,对国家有功勋者”被授男爵爵位,占华族总数的38%,基本与诸侯华族持平,这部分人是近代新贵中的新贵。华族本来是具有公卿及诸侯身份的人,1869年华族初创时,将倒幕维新的主要力量——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士族排斥在外,引起有功士族们的不满。1884年7月“华族令”颁布并授予爵位时,长州藩士出身、掌握授爵实权的宫内卿伊藤博文力主对30名士族出身者作为勋功华族授予爵位,有29名出身于上述四藩,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萨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西乡从道、寺岛宗则、松方正义等人都被授予伯爵。19世纪90年代,进入勋功华族大量叙爵时期。1895年对41人授予爵位,其中30人是与甲午战争有关的军人。1907年授爵的75人中,有69人是日俄战争中的军功人员,因日俄战争之功授男爵的文武官员前后总计96人[25]。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因在日俄战争中率联合舰队打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之功,被破格授予伯爵。在两次战争中,还有不少人因功升爵。如甲午战争后,原为伯爵的伊藤博文、大山岩(陆军)、西乡从道(陆军后海军)、山县有朋(陆军)升爵为侯爵,原为子爵的桦山资纪(海军)、野津道贯(陆军)等人升为伯爵。日俄战争后,伊藤博文又从侯爵升为公爵。这个昔日的下级武士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便与其旧主——长州藩主毛利元德平起平坐了。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本庄繁、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均因“满洲事变”之功被授予男爵。由此可见,勋功华族的叙爵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甲午战争以前的勋功华族或是军功人员或是官僚,皆是“官”,而与“民”无关,官尊民卑显而易见。1896年,日本财阀的两大巨头——三井总家长三井八郎高栋及三菱财阀总家长岩崎弥之助、岩崎久弥叔侄被授予男爵,从此开始有实业家及科技文化界人士获得男爵爵位,但数量有限,到二战结束,只有实业家18家,科技文化界人士15家。
华族是在前近代贵族制度与等级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近代新贵族。虽然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旧的贵族特权被废除,但是在近代国家政权的刻意保护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特权。如根据1889年的“贵族院令”的规定,公爵与侯爵年满25岁(1925年改为30岁)自动成为贵族院的终身议员。伯爵、子爵、男爵由同爵之间互选的方式各选出五分之一,任职期限为七年,大大超过众议院议员的四年任期;在教育方面,华族子女可以进入专设的学习院学习,如果帝国大学学生不足,还可以直接升入帝国大学,故华族可以轻易得到帝国大学的学位;在经济方面,为保证诸侯华族在秩禄处分中获得的巨额公债不流失并实现增值,专门建立了国立第十五银行(又称华族银行),颁布“华族世袭财产法”(1886年)保护华族的财产完整;发布“旧堂上华族保护资金令”(1912年)保障旧公卿华族的生活,等等。
概而言之,近代华族是将旧公卿、大名两大不同贵族统合而成,带有浓厚的身份制度色彩。出于巩固近代天皇制政权及日清、日俄战争的需要,官僚、军人等也因其“勋功”被列入华族行列,在前近代家格门第基础上,注入近代实力主义,从而产生近代新贵族。在贵族重组的过程中,近200万武士被剥夺所有特权,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近七百年的武士阶级归于解体,武家贵族只有昔日大名被保留贵族身份,公卿贵族重得荣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身份色彩强烈、徒有荣誉外表的华族日益走向衰落。据1919年的统计数字,在当时926家华族中,有569家无业或依靠财产收入及恩给为生,成为寄生阶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军事占领,并实行民主化改革。1947年5月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都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以及门第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对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据此,华族制度连同其大本营——贵族院被废除。承载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旧贵族与78年近代史的新贵族——华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4贵族传统与日本的国民性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社会化过程中,基于长期所处的历史与风俗而形成的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性格特点在内的倾向性选择。国民性的形成,不仅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社会结构也会对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日本是贵族制社会结构的典型,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因此,日本的国民性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笔者过去曾就日本国民性中的“实用主义”“集团主义”“等级秩序”等进行过探讨,这里仅简要分析贵族传统对国民性的影响。
(一)身份至上
日本的贵族中最有代表性、而且历史最悠久的是公家贵族。在律令制时代,贵族凭借所谓高贵的家系成为权力的核心,拥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垄断了朝廷的最高官职。从延喜元年(901年)到镰仓幕府建立(1185年)的总计395名公卿中,有265人是藤原氏出身者,占67%,居压倒优势;此外还有源氏79人(20%),平氏24人(6%),大中臣(7人)等10家贵族总计27人(7%)。在公家贵族鼎盛的时代,已经形成对高贵身份及高贵家系的尊崇。家格这种体现贵族等级的形式也引起其他社会阶层效仿。进入幕府时代以后,公家贵族逐渐衰落,直到幕末,基本上没有了实际权力,而且生活贫困潦倒,但是幕府及武士在近七百年中并未对他们进行彻底的剥夺,而是在身份等级制度方面以公家贵族为学习的样板。如公家贵族在不同的场合要穿特定的服装,武士也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着装样式,武士的服装不仅区别于贵族,更与百姓完全不同,其内部还有按照不同等级的严格区别。再如,律令制度下的官位在进入幕府时代后逐渐成为有名无实的虚衔,但武士们不仅要扩张自身的军事实力,也要拥有具有权威及名誉色彩的官位,藉此表明自身跻身于贵族的行列。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期统一天下后,不仅担任关白、从一位太政大臣,而且以律令官制为基础,授予诸国大名武家官位。丰臣秀吉去世时,拥有全国最高官位者竟然是武家出身的正二位内大臣德川家康,此后又升至从一位太政大臣。德川幕府建立后,仍然把公家官位体系作为统制大名的手段。这一做法体现出武士对身份、荣誉和地位的追求。同时,身份制度被德川幕府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日益巩固、完善,身份制度和身份意识渗透到近世日本社会的每个角落。
明治维新以后,华族制度的建立是身份制度在近代的延伸,一方面新政府需要身份制度维护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人并不否认身份制的存在,“只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以前所属的地位,上升至更高一点的地位”。1869年华族初创之时,武家社会除大名之外的所有武士悉被列为士族,这引起许多下级武士出身的维新功臣的强烈不满。长州藩士出身的明治政府领导人伊藤博文认为,“封建武门之世,士族位于平民之上,教育有素,气节有为之人多出其间,应作为贵族之一部,拔其中之人与华族俱列元老,以收其报效”,“今士族平民之有功者立于愚笨华族之下风,只望任国会(下院)议员,此种做法现在与今后都难得有功者之人心”。于是,在以藩阀为主的明治政府主导下,1884年颁布“华族令”并对华族叙爵时,以伊藤博文为首的30名武士出身者被授予爵位。此次叙爵使士族出身者看到了跻身贵族的希望,自荐、他荐者纷至沓来,到1887年,又先后对55名士族出身者授予爵位,此举被称作“圣恩大贱卖”。
1871月10月,明治天皇召见全体华族的户主,并发布鼓励华族去海外游学的敕谕,其中指出:“华族在国民中居贵重之地位,众庶之瞩目之处,固然成其履行之标准”。这是明治政府对华族的定位,承认华族是国民中的最上层,是近代新贵族。在战后民主改革过程中,贵族制度在外力压力下走向终结。这种终结是制度与法律上的废除,而不是对贵族人身的消灭,贵族后代还在,贵族意识犹存,看重世袭的权力、崇尚权威的心理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社会往往不是以个人能力,而是以公认的家系、身份作为判别人的社会地位、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标准,尤其是在人事制度与政治活动中,“任资唯贤”往往重于“任人唯贤”;在国会选举中,政治家的后代大多数都能稳操胜券,于是就产生了独具日本特色的表现为“族议员”的世袭政治。
(二)注重传承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内对制造业“工匠精神”的讨论,作为制造业大国的日本的“工匠精神”及与此相关的长寿企业颇受推崇。日本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长寿人口国,也以“企业长寿大国”闻名于世。即使在历史上屡经战乱、经济危机和大地震的打击,仍有创业至今超过百年的企业25 321家,超过二百年的企业3 937家,是世界上长寿企业最多的国家。不独长寿企业,在文化艺术领域也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家族,如花道池坊流家元从15世纪中期开始到如今已达45代,歌舞伎市川流宗家市川家团十郎从17世纪后期至今传了12代;茶道里千家家元从16世纪传承至今已16代。
从古到今,日本的企业及艺术流派的久远传承是通过家业的世代延续得以实现的,其根源在于日本特有的家制度。日本的“家”不单是男女结婚后生儿育女的具体生活集团和生活场所,还是“超越世代经营一定的行业乃至为换取恩给和俸禄而提供服务的集团,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一个企业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家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所谓家业,不仅指房屋土地、金银财宝,还包括人们赖以谋生的技能。这种家制度正是起源于公家贵族。在律令制时代,贵族的所有政治、经济特权都是通过家来世袭地维系着的,官职也是如此。9世纪开始大贵族藤原氏逐渐垄断朝政后,无法获得高官高位的中下级贵族不得不在一些特定的专业技术领域,通过一技之长在朝廷中立足,久而久之,贵族的家便成为从事朝廷公务的机构,如菅原氏、大江氏掌管文章道,安倍氏垄断阴阳道,和气氏、丹波氏把持医道。在这种情况下,贵族的继承就具有了延续家业的意义,经过人们的刻意维护,贵族的家系得以脉络清晰地延续下来。
贵族的传承最重要的莫过于采取独特的继承制度,在实行长子继承的同时,不排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进入家庭。有学者这样评价日本的继承制度,“除了天皇家族之外,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有与异姓混血的历史”,“即使再出色的家族,也不可能把血缘关系上溯到数代以前,因为家系和血系是很难一致的”。这里出现了“家系”和“血系”两种概念,“家系”是家业延续的系列,具有社会性;“血系”则是血缘繁衍的系列,只有家族性。在现实中,任何家族如果排斥非血缘者继承的话,都无法持续长久。一个家族家系的延续往往与数个家族血系的延续有关。由于存在养子继承的情况,不少家族即使家系延绵,而实际的血缘关系已然面目全非。
以家业为中心,实行长子单独继承,注重纵式延续,贵族的家制度对后来的武士家庭与町人家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武士的家业是为了得到赖以生存的俸禄,必须与主人结成牢固的主从关系,为主人尽忠奉公;商人的家业是指他们从事的商贾买卖及经商的经验,乃至店铺的信誉。艺能人的家业就是所从事的技艺。所以,不论对哪个阶层的人来说,家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家业繁荣昌盛、长久延续是家的终极目的和家族成员为之奋斗的目标。日本人把家视为一个生命体,认为家是从祖先那里传到自己手中的,自己的责任是将其维护周全,再完整地交给后代。每一代继承人都肩负着家业发展与延续的使命,为之付出,为之努力,期盼家业在自己手中发扬光大,至少也要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不能在自己手中衰落、断绝。这便是当今日本大量存在长寿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文化艺术领域来说,因为有人专门把某种被称为“道”的艺术作为一个家族的事业来做,珍惜它,保护它,研究它的精髓,想办法让它发展。所以,以茶道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道”才能够相传数百年而不辍,传统文化也因此得到有效保护。
(三)双重性格
早在战后初期,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就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描绘了日本人的双重人格: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这种双重性人格究竟从哪里来?在从不同角度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时候,似应注意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贵族的影响。
由于日本历史上不推崇以暴力实现改朝换代不仅皇室连绵延续126代,贵族也一直存在到20世纪中期日本战败。在一定意义上说,高高在上的贵族是民众的楷模,在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都会对民众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同“废藩置县”后明治天皇对华族中的藩知事发布敕旨所言:“华族立于四民之上,为众人之标的”,标的就是榜样。有学者在阐述16世纪以后英国贵族的情况时谈到,“贵族的‘高贵’品质是由高贵的血统、优秀的品行、优越的生活方式、卓越的社会贡献等诸多因素集合而成”。日本最初的贵族——公家贵族的“贵”除了体现在“高贵”的血统——家系以外,还非常注意培养与贵族身份相应的教养。如,10世纪中期的公卿藤原师辅(909-960)在病逝前留下遗训,即“九条殿遗诫”,其中仅就每天早晨的生活起居就定下诸多规矩:
起床后先默诵七次自己所属之星宿名称;次对镜子看容姿;次看历日知吉凶;次用牙签清理牙齿,洗脸;次暗诵佛名及日常尊崇之氏神;次记昨日发生之事;次喝粥;次梳头(三天一次);次剪手足指甲(丑日剪手指甲,寅日剪脚趾甲);次择日沐浴(五天一次);次有出仕之事,即服衣冠,不可懈怠。
这11条都是早晨起床之后要做的事情,其中有5条与个人形象相关,说明此时贵族对此十分注重。其他几条有的涉及到神佛及阴阳道信仰,有的是通过每天写日记进行文化上的修炼,有的是对上朝时服饰着装的要求。“九条殿遗诫”在当时公家贵族中流行很广,表明贵族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追求也在提升。公家贵族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尽管贵族子弟年满21岁即可根据荫位制度得到相应的官位,但朝廷要求“五位已上子孙,年廿以下者,咸下大学寮”,“令习读经史,学业足用,量才授职”。因此,平安时代的贵族在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贵族文化,在文学、艺术等方面达到此后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超越的顶峰。
武士依靠武力在朝廷之外建立了幕府政权,从时间上看,武家贵族掌握实权比公家贵族时间长,人数上比公家贵族多很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与平民百姓的接触和联系远远超过偏居京都的贵族,故武家贵族的核心价值对民众的影响要超过公家贵族。与注重文化和教养的公家贵族相比,长期以战争为业的武士的立身之本是精于武艺。在身份制度下,武士作为“三民之长”而存在,一直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尊奉的模范。不仅战争年代要精进弓马之道,即使到了天下偃武的江户时代,大部分武士成为从事行政管理的“公务员”,而历史的惯性令他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尚武精神和杀伐风气。武士出行进退,腰佩双刀,在面对平民的无礼冒犯时可以将其“斩杀后弃之不管”(斩舍),而且不需承担责任(御免)。1869年,当有欧洲留学背景的森有礼在公议所提出要“改变粗暴杀伐恶习”,建议废刀时,居然被罢免了在政府担任的职务。明治政府下达“废刀令”是迟至1876年的事情,反映出武士对尚武与杀伐的留恋。近代以后,武士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或变身政府官员、学校教员、军人和警察,或接受近代教育实现转型,成为新社会中的精英,大多数人陷落为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底层。在此过程中,武士伦理得以扩散到全社会。尤其是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武士的尚武精神被极力推崇,不仅自己在战争中要视死如归,也把“粗暴杀伐恶习”用于对付被侵略国家的国民,制造了无数杀人惨案,给人类和平带来巨大灾难。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及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日本被改造成民主国家,但是社会及学校、家庭一直坚持对国民自幼进行各种磨难教育,其背后仍然可以看到武士的影子及对尚武精神的坚守。
综上所述,贵族是日本身份等级制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仅次于皇室而居于社会的顶层。凭借所谓高贵的家系及优越的社会地位(公家贵族)、特有的军事功能(武家贵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掌握社会主导权,经过对贵族的重组,在近代社会依然作为上流社会而存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族的文化与教养和武士的尚武精神,造就了日本国民的双重性格:既有彬彬有礼、讲究礼仪的一面,也有冷酷无情、野蛮好战的另一面。
作者单位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