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首先,随着1973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提升,中东地区作为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的价值也出现了增长。地区大国在同盟中的价值量也应该出现相应的提高。但问题在于,为什么1979年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在美苏之间“以转换同盟为要挟”的报价出现了走低趋势呢?为什么1979年后苏联在中东地区只剩下叙利亚和南也门两个盟友?本文认为,1979年苏联对主权国家阿富汗的军事入侵直接导致了中东地区大国安全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安全威胁从周边邻国变成了超级大国苏联本身,进而导致了中东地区国家与美国的同盟性质从“安全互补型”演变为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威胁一致型”。
1979年12月末,苏联放弃了“代理人”模式,从地缘政治较量的“幕后”径直走上了“前台”。这场战争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它不仅导致了美苏自1972年缓和局面的结束——美国总统卡特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 [47]——更重要的引发了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自身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最重要与最紧迫的利益不再是通过制衡周边国家而获得区域优势战略,而是防止自身被苏联军事侵略。
随着同盟类型的转变,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的自主性和约束能力明显提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生在1982年6月9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部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苏联盟友)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战争期间出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而在整个“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现的出奇冷静。而这在1970年代是非常可能引发联合军事行动或“石油危机”的。1979年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牢牢紧跟美国,直到苏联解体后安全威胁消除。
第二,为何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威胁一致型”同盟没有出现中国服从苏联的状况,反而出现了中苏对抗呢?本文认为,中苏同盟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双方名义上构建的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但实际上仅是意识形态一致性基础上的“安全互补型”同盟。从名义上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角度讲,中苏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区域战略需要服从苏联全球战略安排;但事实上,经历朝鲜战争后,中国眼中最大的威胁以不再是美国。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解放台湾、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赫鲁晓夫的战略目标则是推动美苏两极格局下的缓和。苏联凭借“威胁一致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中国服从,而中国则从“安全互补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苏联支持其台海战略。因此,这种表面装点并混杂着全球共运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同盟”注定因其逻辑的非相合性而走向分裂。
相反,中美的战略接近正源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入侵以及对中国核打击威胁,促使其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共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苏联对华“核恐吓”导致了中美之间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而迅速建立起“威胁一致型”准同盟。美国不再强调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也不再强调美国对越南盟友的侵略与帝国主义性质。双方在苏联共同威胁下,迅速建立起准盟关系。这一关系确立后,中国积极调整自身战略姿态,并表现出对美苏全球争霸与亚太战略的积极配合。一方面,在台海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动降低了区域竞争烈度。另一方面,在支援越南战争方面也表现出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利益的理性。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对中美双方的安全威胁日益降低。伴随着东欧剧变,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矛盾则走上了前台。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威胁一致型”准盟关系的解体。
第三,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越之间出现了“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态势?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陆上安全就不再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了。但由于中国坚持对自身的国际身份定位在天平托盘而非重要砝码,因此,在美苏两极结构已经趋于稳固的情势下,中国面临着美苏双方的巨大压力。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率领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苏在黑龙江、新疆地区增加的边境冲突促使中国放弃了充当世界第三极的主张,转而接受了自身成为美苏之间重要战略平衡砝的新角色。这就出现了中国在美国与“北越 苏联”之间两面结盟的现象。
一方面,中国与“北越 苏联”政权在越南战争中名义上仍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年才废止——但事实上随着中美和解而更加明显地降格为“意识形态型”同盟。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基于苏联共同的威胁则出现了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必要条件。当共同利益较低的“意识形态型”同盟遭遇到共同利益最高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时,即便上世纪初70年代初“北越 苏联”默认保留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同盟并默许了通过中国同美国的战略接近,也难免中国在逐渐强化中美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疏远意识形态盟友越南,甚至到了1979年双方走到爆发战争的地步。
上面关于中国的两面结盟策略构成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摆脱孤立并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囿于中国在安全上加速倒向西方世界——“一条线”与“一大片”——苏联逐步降低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压力并在进攻态势上更加审慎。即便中国对其盟友越南发动军事进攻,苏联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情绪。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世界为了更好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与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援助。70年代始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选择为中国降低苏联安全威胁和获得美国经济援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科林斯难题”的政治启示
在同盟内部,并非所有小国都是任由大国摆布的可怜虫,在特定条件下它们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局部利益加诸于战略缔造、获得同盟主导权并对战略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科林斯难题”便反映出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内主导国可能面临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即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战争能力,而许多战争本身却是为了维持同盟的存续。它反映了“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内在困境,即当偏执的区域盟友所关注的区域战略与同盟主导国关注的整体战略出现非相合性时,如何避免因错误的认知与同样冒进的行为,而导致整体战略被区域战略绑架并拖入到事与愿违的高度危险境地呢?
在两极格局的全球博弈中,历史给了我们一些获取经验的线索和提示。“采取正确结盟战略”的国家获得了来自同盟的巨大力量,而 “采取错误结盟战略”的国家不论其多么努力发展,积累起来的能量都会被对方不断增加的反作用力或己方盟友不断增加的诉求所抵消,甚至有时还会强化对方同盟行动的一致性。本文认为,“采取错误战略”是指犯了三项重大失误:第一,试图通过不断追加投入弥合同盟内部的安全利益认知差异,幻想使“安全互补型”产生与“威胁一致型”同盟一样高的战略效果;第二,在洲级大国时代,即便某个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的国家出现了同盟转换,也无法影响到两极格局的力量对比。从近代欧洲多极均势中结晶的话语逻辑可能诱导盟主国家夸大区域盟友的战略价值,从而陷入到“三大战略迷思”;第三,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展现出过度膨胀的野心、对强权政治的迷恋,将间接帮助战略竞争者在特定区域形成投入成本更低、行动效力更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这一点特别反映在为什么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比北约的西欧盟友更愿意配合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区域行动。这样会经历双重挫折,即自身盟友的离心力增强,对方盟友的凝聚力大增。因此,“采取正确的结盟战略”意味着对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友价值的理性认知、有限期待和互惠性支持,以及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众叛亲离与体系性制衡力量的生成。
一战后,国际政治已经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扩展到“全球体系”的宽广舞台。洲级大国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权力博弈已经成为只在主导国之间进行的两极游戏,中等强国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与日递减。尤其是同一个任性妄动、不负责任的地区国家结盟并不意味着增加一笔资产,而是增加一项负担。就如同长期对某一问题的慈善行为非但不能治愈,反而还会增加贫困一样——因为它不仅是对短视与懒惰行为的奖励,而且会鼓励短视与懒惰的人成倍地增加——对“安全互补型”区域盟友无底线的支持,不仅不能换来预期中的战略协作,反而会因自身的沉没成本而增大对方的胃口。因此,同盟主导国必须根据情势的变化而建立起更有效的评估方式,以界定在不同争议地区采取行动的方式、支持限度和承诺底线。其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找到一个主导国能支持的盟友,而是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盟友愿意支持主导国的大战略。缺乏排查“安全互补型”同盟的这套标准,主导大国可能被那些以“安全利益一致”为名并与之结盟的卫星、附庸、傀儡、客户组成的杂牌军拖入不必要的区域冲突,而不得不在姑息、挫败、纵容以及不可估算的代价之间使全球战略降格、转移直至从属于盟友的区域战略。
尤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权力“生产核心区”从欧洲分离出来并加速向东亚地区转移。今天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主要呈现为欧美控制“技术核心区”、印太居于“生产核心区”,而中东依然是“资源核心区”。[48]冷战至今的历史表明,美国对欧亚大陆潜在对手的遏制是依据三大地缘政治核心区而展开的。正如1988年1月里根宣言所阐释:“美国战略的首要特性在于坚信倘若一个敌对国家将统治亚欧大陆——地球上那个被称之为心脏地带的国家,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就将受到威胁。我们为阻止这种情况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自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力求防止苏联利用其战略优势而支配西欧、东亚和中东地区,从而根本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其对美国不利。” [49]
美国在三大区域内的遏制对象也清晰地表现为俄罗斯(欧洲地区)、伊朗(中东地区)和中国(印太地区)。其中,尤以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冲击最为明显。当前,中国迅速崛起是引发体系新一轮转型的核心变量。一方面表现为中美权力位差迅速收窄,另一方面表现为中美两国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权力位差均在拉大。这就意味着国际体系向两极格局转型可能性明显增加。[50]在体系权力格局从单极向两极演变的进程中,中美之间在印太地区的矛盾可能性与日俱增。这就客观上要求战略理论界提前加强对“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51]
在我们成为另一极之前,中国需要长期延续在各种形式下的不结盟战略,它可以帮助我国避免自身方面陷入盟友制造的“科林斯难题”。同时,如果中国想有所作为,那么可以试图在三大核心区的外线区域展开结盟行动,而不要在内线区域过早地摇落霸权国花园中的果实。同时,美国是否会面临亚太盟友提出的“科林斯难题”,从而面临是否支持其与中国的领土矛盾,也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中国如果想弱化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就需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类型进行有效区分。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进行部分同盟分化。一方面促使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转变为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另一方面,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安全互补型”同盟升格为“威胁一致型”同盟。为此,中国需要注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四个同盟。
首先,从美日同盟角度看,随着日本从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军事与政治大国的转型,[52]中日之间争夺领土与亚太主导权的进程与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高度一致,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属于“威胁一致型”同盟,因此不仅不具备弱化的可能性,反而随着中国崛起或东海问题而更具行动能力。
其次,从澳大利亚角度看,澳大利亚视中国为未来追求南太平洋区域主导权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这与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呈现出较高一致性,因此美澳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也属于“威胁一致型”同盟。随着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增加,美澳同盟在对华问题上将更具一致性。但由于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比日本更为遥远,中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有条件的绥靖、更加温和的外交战略促成美澳同盟安全威胁的降低。
第三,从美韩同盟角度看,韩国的安全关切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安全,它对中美全球战略竞争中涉及朝鲜半岛之外的问题并不关心,1992年中韩建交后更是极力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53]。而虽然美国坚持名义上对朝鲜的恐惧——看似美韩同盟是“威胁一致型”——但其实冷战至今以来美国陈兵半岛的根本战略是为了防范中俄。随着中韩建交以来敌对关系的持续降低,今天的美韩同盟以演化为典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因此,只要中国对韩国展现出足够的善意并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共同合作可能性的暗示,就能够降低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安全压力。
最后,从菲律宾和新加坡角度看,作为地区小国,它们的安全关切事实上仅局限于南海地区安全,因此美菲同盟与美新同盟既可能属于“安全互补型”,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威胁一致型”同盟。这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是以战略军事为主导,还是以战略经济为主导。只要中国在南海地区持续展现温和与善意——而非咄咄逼人、无视裁决、锱铢必较、处处争抢的权力政治——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并不愿意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过分迁怒于中国,而更愿意通过两头下注的“对冲战略”获得中国经济上的好处与美国安全上的援助。反之,则可能诱发两国积极同美国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
“科林斯难题”属于大国崛起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微观理论,它在精细化同盟类型的基础上发现了差异性的结果。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阐释一种同盟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更在于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与启示。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崛起大国,中国利用和规避“科林斯难题”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对周边小国滥用威慑、奉行单边主义或严重损害本国道义根基的方式,迫使周边国家因感到恐惧或羞辱而与美国形成“威胁一致型”对华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能提高中国成功崛起的机会。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类有趣的现象,当体系中存在两个主导大国且它们之间处于势均力敌的战略僵持背景下,构建同盟则成为“两极”各方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与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护持霸权最有效的路径。但问题在于,主导大国借以增强战略主动性的同盟,可能因其惧怕被抛弃与背叛而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在于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性;另一方面,为了彰显同盟内部利益一致性而逐渐丧失对内战略主导权。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如果说同盟间爆发的体系战争多由任性妄动的弱小盟友所引发,那么何种类型的同盟主导国更容易受其摆布而逐步丧失掌控能力?为什么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降的同盟政治中经常会出现主导大国逐步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被弱小盟友的“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和削弱,并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甘愿沦为其实现“区域战略目标”的工具,即便这种“区域战略目标”与“整体战略目标”走向出现了明显背离?探寻“砝码国家自抬身价”这种现象发生的政治条件是本项研究的根本目标。
当前同盟理论认为,同盟内部主导大国与追随小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位差,使其成员之间呈现出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相比于主导大国的战略韧性与承伤能力,小国往往更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同盟主导国具有充分的自主性来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进行战略规划。战略设计可以更多地着眼于主要对手,而非为了满足盟友的漫天要价。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从欧洲“中等强国”为中心的狭小舞台向全球“超级大国”为中心的宽广舞台演变趋势加速推进。超级大国与其盟友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使得后者任何退出或重新站队的威胁都变得无足轻重。“寡头垄断”市场模型更能够解释并防止大国被弱小盟友拖入不必要的同盟战争。[1]
这种以权力“结构性”为关注重点的同盟理论倾向认为,在等级性同盟内部,当某项区域子战略与整体战略出现矛盾时,主导大国将运用权力优势迫使盟友对自身区域战略进行调整,以实现次要战略利益服从与整体战略利益的理想要求。这将有效降低地区性冲突越轨升级为体系战争的风险。[2]这种观点得到了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证实。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国际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斡旋中,与争端双方具有同等亲密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只有31%,而与争端一方有同盟关系,而与另一方没有同盟关系的强国成功斡旋率则高达81%。该理论认为,同盟主导国成功斡旋冲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同盟内部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使得主导大国可以迫使己方小国接受其方案;另一方面在于同盟关系对未结盟方起到了威慑作用。[3]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既然大国谋求外交斡旋,就意味着战争方案不符合主导国的利益。那么为什么仍然存在19%的大国不仅没能约束弱小盟友,反而被弱小盟友拖入到力图避免的大国冲突之中的反常问题。通过对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991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四种同盟类型(参见表1)占比统计发现,外交斡旋失败的案例构成了这一阶段“安全互补型”同盟的一个真子集,即在主导大国外交斡旋失败的19%案例中,其同盟关系类型均属于占比24%的“安全互补型”同盟。[4]这一高度正相关为本项研究分析同盟类型与同盟效力的二元关系提供了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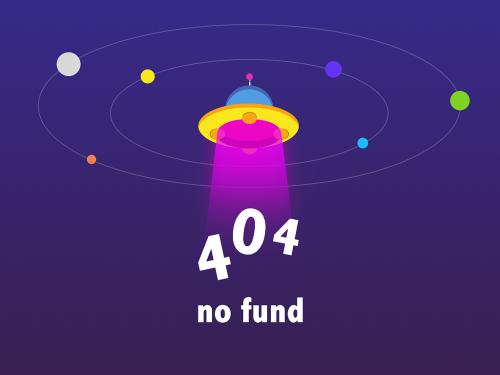
表1:同盟类型与效果特征
此外,传统的同盟关系理论将重点放在权力“结构性”问题上。但结构性权力位差普遍存在于所有同盟之中。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结构性”同盟内部大国无法约束小国的特定现象。本文认为,这种“骑士与马”的同盟关系更适用于“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两类同盟,却并不适用于同样存在权力位差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威胁一致型”同盟假定区域盟友与主导大国对共有威胁的认知高度一致。“权威强制型”同盟则假定主导国能够将权力相对优势充分转化为对盟友的控制和影响,并依靠强制权力迫使区域盟友参与并服从其全球战略。上述两类同盟确实能够保证主导国对盟友享有充分灵活的自主权。
但是问题在于,当今同盟政治实践中并非仅存在着“威胁一致型”和“权威强制型”——随着1989年东欧剧变,“权威强制型”同盟关系随着权力政治逻辑的式微正在变成同盟理论中的“濒危物种”——两种同盟。还明显存在着并无共同威胁、各取所需、相互借重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这种安全互补的同盟类型中,主导大国吸纳地区盟友构建同盟的目标常常是服务于“全球战略”,但地区盟友参与同盟的动机却并非担心或制衡另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希望获得本方主导大国的支持,进而谋求本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优势。
与前两种“等级制”同盟关系不同,“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关系更具“平面化”与“灵活性”特征。由于缺乏共同的安全威胁,享有结盟自主权的地区大国往往有机会借两大同盟竞相拉拢之机待价而沽。“砝码”国家自由站队给同盟主导大国带来的难题就是,不仅难以通过强制性权力迫使盟友甘愿压抑自身的局部利益诉求而服从同盟整体战略安排,甚至为了防止其退出或转换到对方阵营,而不得不对其与整体战略目标相悖的区域战略目标加以支持。
“科林斯难题”是“安全互补型”同盟中长期反复出现的地缘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本项研究构建理论的兴趣起点。具体来讲,“科林斯难题”是指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国家间,处于弱势的地区盟友(天平“砝码”角色)以向对手同盟转换或退出同盟为要挟,借以提升自身在同盟主导国(天平“托盘”角色)眼中的地缘政治价值。迫使同盟主导国在绥靖、贿赂、安抚、争夺、讨好与无条件承诺盟友的竞赛中竞相哄抬报价,以至于逐渐放弃建立同盟之初的全球战略目标,转而服务于地区盟友的次要战略目标。其最大特征就是主导国最初迟疑的、战术性的权宜之计最终却在不知不觉而又半推半就中演变为坚定的、战略性的命运抉择。
经验与常识告诉我们,两极格局下体系大国积极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对外战略主动权。但“科林斯难题”的出现却导致体系大国陷入到为了维系同盟而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权的悖论之中。它是“安全互补型”同盟政治中主导大国面临的现实难题。战略手段通过何种方式逐步凌驾于目标之上并导致大国放弃了既定战略是本项研究试图解答的同盟政治迷思。本文从地缘战略心理学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揭示同盟内部的政治博弈过程来构建“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微观理论。
二、“科林斯难题”的理论阐释
“科林斯难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通过对一种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同盟政治现象进行规律性探讨,借以构建逻辑自洽的微观理论。它意在探寻小国在何种条件下、采用何种方式自抬身价并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转化为整个同盟的共同难题。以下将遵循从现象到概念,从概念到理论的一般性认知规律对其进行理论阐释。
(一)从现象到概念:历史中的“科林斯难题”
科林斯(corinth)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地峡。古时候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希腊人之间几乎所有的交往都是通过陆路进行的,科林斯领土是他们交往的必经之地。同时,它又是穿过萨罗尼科斯和科林西亚湾通向伊奥尼亚海的航海要道。古代船只要经过科林斯地峡,就需要从地峡的一边被拽到另一边。因此,科林斯自古以来不仅成为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也是一个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连接的战略要地。[5]
科基拉(corcyra)位于古希腊西部伊奥尼亚海,是由科林斯移民组建的殖民地。但与科林斯其他殖民地不同,在举行公共节日聚会[6]——例如,在举行祭神牺牲仪式——时都没有按照希腊城邦的习俗而在母邦科林斯人面前表现出应有的恭顺。科林斯人认为,科基拉自恃财富可以与母邦相比而表现傲慢。更让科林斯人愤怒的是他们还将自己的海军荣誉归因于原住民腓亚基亚人。[7]
爱皮丹弩斯(epidamnus)位于伊奥尼亚湾入口的右手边,是由科基拉移民建立的一个殖民地。追根溯源则是由科林斯人爱拉托克雷德斯的儿子法里乌斯建立的。在公元前435/前434年,爱皮丹弩斯与毗邻的异族人交战遭受重挫后,邦内平民驱逐了贵族。被驱逐者投靠了异族人并联合异族在海陆进攻爱皮丹弩斯。爱皮丹弩斯人在情急之下请求母邦科基拉的援助以便结束这一困境。但这一援助请求遭到了母邦科基拉人的拒绝。
当进退维谷的爱皮丹弩斯人知道他们无法从科基拉得到援助时,“德尔菲”神谕他们把城市交给更高的母邦科林斯人,请求并接受其保护。爱皮丹弩斯人按照神谶的指示,派人前往科林斯。他们指出,城市的建立者是科林斯人,并说出神谶的内容;请求科林斯人援助他们,使他们不至遭到异族的毁灭。科林斯人马上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并迅速派出了自己的军队和移民。爱皮丹弩斯人认为,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一样,有权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殖民地,实施母邦保护的责任。另外,作为科林斯人的后裔,爱皮丹弩斯人怨恨科基拉人对母邦的轻蔑。[8]
科林斯人对爱皮丹弩斯的援助导致了科基拉人的怨恨。双方于公元前435年春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却出乎意料,科基拉人对自己的母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科林斯人为了复仇,于公元前433年再次准备向科基拉发动新的战争。但这一年向来以不结盟为特征的科基拉以“希腊有三大海上强国——雅典、科林斯和科基拉。如果你们让其中两个合二为一,让科林斯控制了我们,那么你们就不得不防止与科基拉和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作战”[9]为理由,迫使雅典与科基拉结成有条件的防御性同盟。[10]这就导致了科林斯为了实现重新夺回对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这两个殖民地,就必须寻求来自伯罗奔尼撒盟主斯巴达人的帮助。
公元前432/431年,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科林斯人以“不要让我们其他盟邦不得不在失望中加入其他同盟(这里指雅典人主导的提洛同盟)……诸神不会谴责那些在危难之中被迫去寻求新援助的人们,而会谴责那些冷眼旁观并拒绝给与盟友援助的城邦”[11]作为威胁,迫使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做出了为帮助盟友科林斯恢复对殖民地科基拉与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力[12]而向雅典宣战的决定。至此,地缘政治的博弈战场正式从科林斯与科基拉区域性“狭小舞台”跃升为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体系性“宽广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两极格局与美苏两极格局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所处的国际体系是开放的。在古希腊两极格局背后,隐含着波斯帝国、马其顿、叙拉古等庞大的侧翼强权。因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均非常珍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13]后双方达成的“三十年和约”。这一和约就像今天美苏之间约定欧洲现状不可破坏的《赫尔辛基协定》一样,构成了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例如,公元前433年,当科林斯对科基拉的进攻因雅典人援助而受挫时,雅典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选择对科林斯海军网开一面。为了避免激怒背后的斯巴达,严格奉行防御义务的雅典人在面对科林斯使者质问时不仅制止了科基拉人要求杀掉科林斯使者的鼓动,同时也表明了其防御目的:“伯罗奔尼撒人啊,我们既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破坏和约。如果你们往其他方向航行,我们绝不会阻拦你们。但是如何你们航行去进攻科基拉,我们将尽全力采取防御。”[14]残存的科林斯舰队在得到雅典维护和约的防御性答复后平安地使出了包围圈。
虽然斯巴达人对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惧,但尚未做好准备的斯巴达人也不愿过早结束这一对护持自身霸权有利的和约。在讨论是否对雅典开战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国王阿奇达姆斯综合分析了雅典的海军、双方的公共资金、域外大国波斯的虎视眈眈、国内黑劳士暴动等因素后认为,为了科林斯而过早地结束与雅典的“三十年和约”是一件不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当整个同盟为了局部成员利益而宣战,而战争的进展又是无法预测的,想求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非常不易。[15]但在阿奇达姆斯国王发言后,对国王不法行为具有监察和审判权的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则从“温泉关记忆”中认为,如果我们是贤明的,就不应该对于别人侵害我们的盟友坐视不管,不应将今天援助受害盟友的责任推延到明天。我们不应让别人批评我们在盟友受到侵害时还在讨论法律诉讼的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同盟者迅速而强有力的援助,以免导致更多盟友的恐惧……不要使我们的同盟者陷于毁灭![16]至此,经过拉栖代梦公民大会的表决,“三十年和约”在缔结后的第14年宣告失效。
科林斯人与雅典人无冤无仇,他们只想夺回对殖民地科基拉和爱皮丹弩斯的控制权;雅典人与科林斯人无冤无仇,他们被迫吸纳科基拉进入同盟,只是想确保科基拉的海上力量不被伯罗奔尼撒人所兼并。同时,三十年和约也有助于雅典人应对波斯帝国的威胁。前446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进攻让雅典人明白,以雅典帝国的实力无力同时在两条战线与波斯和斯巴达争雄。[17]卡根认为:“从雅典签订三十年和约后的表现可以看出,它不再野心勃勃,其行为也不再威胁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任何城邦”[18]。在波斯帝国等强权环伺的大背景下,斯巴达人享有与雅典人维护和平条约的利益,却陷入到要么支持科林斯人从雅典口中夺回科基拉,从而引发“世界大战”;要么接受科林斯因愤怒或战败而加入提洛同盟[19],从而彻底丧失与雅典的“权力均衡”。科林斯人将自身的地缘政治难题推给了盟主斯巴达,而斯巴达为了防止盟友因失望而背叛,不得不放弃与雅典和平的总体战略。转而带领伯罗奔尼撒同盟投向了导致整个大希腊全面衰落的体系战争。以上就是国际关系史中的“科林斯难题”。它是弱小盟友科林斯的区域难题,却最终上升成为了整体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体系难题。
(二)“科林斯难题”的前提假定
本文构建理论的前提假定主要有三点,故只有在满足以下三点假定的前提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才具备生成条件与环境。
第一,“科林斯难题”产生的政治条件是体系存在两个势均力敌、均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的安全同盟。[20]本文认为,两极均势是权宜性的,大国构建安全同盟的目的不是维持权力均势,而是为了最终获得单极优势。为了获得霸权地位,争取控制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21]——往往成为两大同盟主导国赢取战略优势的核心锁钥。 “三大核心区”的共有地缘观念很容易衍生出三种战略迷思,即“心脏地带推论”、“多米诺推论”和“黄金之国推论”。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给同盟主导国带来“科林斯难题”的地区盟友应是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的国家。
第二,“科林斯难题”的适用对象是“安全互补型”同盟,即试图通过构建相互借重的互助同盟获得各自的战略需求。同盟主导国与区域大国并不存在高度一致的安全威胁。尽管全球均势变化对体系超级大国十分重要,但地区国家结盟的目的主要针对区域内部周边国家的权力竞争。由于实力限制了利益诉求,同盟中区域大国首要地缘战略目标往往是如何借助盟主的力量获得“地区优势”,而非主导国更加关注的“全球优势”。因此,对于区域盟友来讲,加入同盟的问题永远不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强大”而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更愿意帮忙”。这就将区域与全球地缘战略目标高度相合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在“威胁一致型”同盟中,小国由于缺乏选择而更怕被大国抛弃,并最终形成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骑士与马”的主从关系。
第三,因空间、地貌与水体阻隔等“地理磨损”要素的存在,世界政治的重要赌注、占据重要战略位置或是具有改变本地区权力平衡的区域大国——战略平衡砝国家——享有较高的行动自由与结盟自主性。这就将“权威支配型”同盟——苏联控制下的华沙条约组织、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纳粹德国控制的欧陆同盟,以及拿破仑控制的欧陆同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三)“科林斯难题”生成的政治逻辑
从同盟主导国角度来讲,当两大对立同盟都试图获得权力相对优势时,关键性区域盟友的去留就变得十分重要,至少在主导大国的认知中看上去非常重要。在传统地缘战略话语逻辑影响下,主导大国对盟友价值认知可能会出现偏差并导致其陷入到“多米诺推论”、“黄金之国推论”与“心脏地带推论”。布热津斯基认为,美苏霸权国争夺的重点是除它们之外的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即技术核心区——欧洲(欧洲桥头堡)、生产核心区——亚太(远东之锚)、资源核心区——中东(欧亚大陆之巴尔干)。[22]其中,“多米诺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两大阵营在亚太地区的争夺;“黄金之国推论”主要表现在美苏同盟在资源核心区——中东地区的结盟竞价;“心脏地带推论”主要表现在西方与苏联在欧洲地区的争夺。
首先,在生产核心区的“多米诺推论”源于第二次波希战争的历史经验。[23]当时的斯巴达国王里奥尼达认为,如果温泉关失守,波斯大军将像决堤的洪水涌入希腊各邦。今天,“多米诺推论”往往指某一具有地缘政治“前沿阵地”作用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冷战时期,美国在越战中不断追加筹码也源于这一错误战略迷思,即如果丢失了越南,整个东南亚地区就会向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向共产主义,进而威胁到澳大利亚安全。同理,美国积极介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如果任由整个朝鲜半岛并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海峡对岸日本将很可能也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其次,在资源核心区的“黄金之国推论”主要指蕴藏大量资源,却很容易被征服的地区。[24]因此,必须通过在这一地区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同盟,才能确保将此地据为己有,至少防止它落入敌手。“黄金之国”的逻辑认为,对“资源核心区”的排他性掌控可以使己方在物质实力对比中获得优势。为了获得在“黄金之国”地区的排他性优势地位,美苏在冷战期间在中东地区进行了最激烈的、不计成本的争夺盟友竞赛。历次中东战争背后都能找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而这些超级大国“代理人”则可以利用美苏两国害怕失去该地区盟友的心理,不断地以转换同盟为要挟迫使同盟主导国支持其区域地缘战略目标。
第三,在技术核心区的“心脏地带推论”主要指现代国际体系发源地的欧洲部分。[25]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式迈入“洲级大国时代”。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体系主导权从欧洲“中等强国”向美苏“超级大国”转移。如果说英法霸权时代将中东欧视作影响海陆权力格局演化的“心脏地带”,那么美苏两极格局——后来变为美国单极格局——时代争夺的技术核心区就扩大为延伸至北大西洋沿岸、包含英法德所有“中等强国”的整个欧洲。纵观整个冷战时代,从地区生产总值、安全开支、知识创新到金融信贷四种结构性权力,欧洲地区都是最能影响美苏两大同盟体系权力分配的力量要素。[26]
“技术核心区”居于三大核心区之首。它是两大同盟集团最敏感、也最具进攻性的地区。两次世界大战均源于欧洲。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在于技术对产业升级、生产效率提高、能源结构优化、资源机动性增大等起着决定性作用。控制技术核心区的意义在于,即便苏联可以凭借蛮力并依靠“烟囱工业”再现19世纪80年代那种蛮力经济增长,即便其钢铁比美国多80%,生铁产量是美国的200%,发动机产量是美国的5倍,如果它不能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去适应一个日益建立在以硅晶和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新时代,就算传统重工业烘托下的gdp增长再多,也会因日益拉大的技术代差而愈发脆弱。[27]309-310
整个冷战期间,美苏均对“技术核心区”——欧洲地区——的权力波动均异常敏感。除了发生在美国后院的古巴导弹危机外,两次柏林危机是最有可能导致美苏不用“代理人”——朝鲜、越南、非洲、美洲和中东地区美苏为了避免直接对抗都采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而亲自走向超级大国对抗前台。鉴于欧洲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美苏两国在压力允许的范畴内均对地区盟友的诉求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满足。美国方面对北约盟友的经济援助与安全承诺自不待言。即便是依靠权力构建的“权威型同盟”,苏联对华约盟友的经济扶持也是不遗余力。上世纪60年代苏联出口产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制品为主。而为了帮助经互会的华约盟友发展经济以换取它们的政治效忠,苏联宛如专业从事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东欧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经济提供廉价原料和近乎不受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广大市场。以至于1985年,苏联出口逐渐沦为以能源为主(石油及天然气占出口总额53%)。反之,其进口产品几乎60%为东欧盟国生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消费品。[13]579当然,如果盟友想抛开苏联搞“布拉格之春”则会马上感受到“权威支配型同盟”的压力。
(四)“科林斯难题”的基本假说
基本假说1 :如果说区域盟友对同盟主导国战略杠杆取决于结盟自由度、安全利益一致性和战略区位价值三种要素,那么“安全互补型”同盟中的区域盟友——尤其是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往往比其他三种类型的盟友更可能激活主导大国的战略迷思与介入意愿,进而导致区域战略目标绑架同盟的整体战略规划的问题。
基本假说2: 砝码国家能够自抬身价的主观因素在于传统地缘政治话语对观念的建构效用以及在此效用下双方认知图式的自我保持。由“技术核心区”衍生出的“心脏地带推论”、“生产核心区”衍生出的“多米诺骨牌推论”、“资源核心区”衍生出的“黄金之国推论”建构了区域盟友的地缘战略价值。尤其是当同盟主导国与地区盟友共同内化了上述认知后,这种共识将强化双方对砝码国家战略价值的认知。从话语建构主义角度讲,正是这些过时的地缘政治话语和观念构成了同盟主导国陷入承诺困境,以及在这些区域内砝码国家自抬身价的主观因素。
基本假说3:砝码国家谋求自抬身价的行为多发于“安全互补型”同盟之中。“安全互补型”同盟既不存在“威胁一致型”同盟中的共有外在威胁,也不存在“权威支配型”同盟中的强制力约束。与前者相比,它缺乏一致性利益;与后者相比,它缺少惩治性约束。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在外压错位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区域盟友往往有更高的意愿和能力与同盟主导国不断地展开合作议价。另一方面,即便同盟成员在和平时期频繁举行首脑会晤、联合演习、联席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等展现的姿态多么团结,一旦需要将整个同盟迅速集结起来并让它马上投入战斗则往往会令人大失所望。
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主导国经常会面临启动缓慢、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坐地加价、临阵倒戈或责任推诿等各种问题。毕竟,所有国家都是利己行为体,都具有以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而参与互惠同盟的强烈动机。对于主导大国来讲,地区同盟真正的地缘战略价值在于其不被使用时因数量、声势所产生的威慑效果(对0.5贡献的加法),而非其真正被启动时的实际效果(对0.5贡献的乘法)。
基本假说4:“安全互补型”同盟与“威胁一致型”同盟之间会随着安全压力的变化而出现转化。一方面,如果地区大国预感到超级大国中的一方具有入侵或灭国倾向,那么它就会放弃原有在两者之间的待价而沽,转而积极主动谋求与另一个超级大国之间建立“威胁一致型”同盟。反之,如果超级大国中的一方降低了对地区大国的威胁,则会使对手原有的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降格为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
基本假说5:与人们通常认知的相反,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现象大多出现在“意识形态型”同盟关系中——例如,中国上世纪70年代既同北越是盟友,又与美国建立了准盟关系——少部分出现在“安全互补型”同盟中,没有出现在“威胁一致型”的同盟关系中。在“意识形态型”和“安全互补型”同盟内部,当某个国家无法为其盟友提供不可或缺的安全利益时,它更可能默许其盟友两面结盟的选择。
基本假说6:米迦勒·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认为,超级大国对区域大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将导致依赖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确立主从关系。[28]但本文认为,只有在“威胁一致型”或“权威强制型”同盟中这种援助才能确立主从关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不援助小国也愿意确立这种关系。在此,援助是结盟的结果而非原因。而在缺乏共同威胁的“安全互补型”同盟中,主导国对区域盟友的军事或经济援助对确立主从关系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反而可能导致区域子战略绑架全球整体战略的被动局面。单纯对盟友区域战略的支持不仅难以培植可靠的“代理人”,反而可能因给盟友和敌对同盟发出错误的支持信号而导致同盟关系的紧张与失控。一方面,地区盟友和敌对同盟可能根据援助力度判断主导大国对其区域政策的支持,从而得出与同盟主导国本意相悖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援助增强了盟友在地区的实力,进而可能导致其执行更加冒险的战略计划。军事援助本应该成为同盟强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在“互补型同盟”关系中,则变成了盟友从主导国方面榨取支持能力的象征。
基本假说7:在洲级大国时代的两极结构中,一个盟国的背叛或另一个盟友的加入不再能够改变权力均衡,也无法实质性的影响超级大国的权力对比。因此,主导大国不应过度关注盟友的背叛——事实上一个质量较大的砝码也许能够使天平一端有所升高,另一端有所降低,但在超级大国压倒性权势背景下,这些干涉量变不可能使超级大国间的平衡关系发生颠覆性逆转[29]——而应警惕承诺逐渐扩大、野心过度膨胀、不区分进攻防御情势、过分关注威望,进而避免因自身无条件支持盟友区域进攻行为而导致出现更大的结构性制衡。
洲级大国时代的开启已经改变了除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外的一切事物。它对同盟政治理论提出了全新的前提假定。我们在使用“结盟”与“权力”这类话语的常规用法来描述“核恐怖平衡”下的地缘政治时,也表现出某种思维落后于时代的不适当性。在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友的转换对两大阵营权力增减的边际效应不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可否认,从前这种游离进退的自由曾使中等国家——或小国中的较大国家——在近代欧洲体系的权力天平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角色。从欧洲传统地缘政治角度讲,担心一旦主导国不能满足盟友的需求就可能导致其背叛行为,这既符合多极化背景下结盟均势理论的一般传统,也构成了主导大国区域战略产生众多事与愿违结果的重要原因。[30]砝码国家愿意沿用传统地缘政治的话语,以便从主导大国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但事实上,它们转换同盟的威胁不应被过分夸大和关注,对于任性妄动、不负责任、坐地起价的信誉不良者,对方同盟要么选择将其看做负担而加以拒绝,要么就不得不吞下增加负担的苦酒。
三、“科林斯难题”的案例验证
在两大集团争夺地区盟友的零和博弈中,砝码国家往往可以做出“两面下注”的姿态,以求得自抬身价的有利结果。这种“友谊拍卖”的结果就是迫使它中意的同盟一方开出远远高于其战略价值本身的报价。“科林斯难题”既是小国将自身区域问题转嫁为整个同盟难题的博弈过程,也是主导大国因过分关注局部战略手段而迷失整体战略目标的政治现象。
本文将分别选择在世界权力“技术核心区”、“生产核心区”和“资源核心区”出现的三种“安全互补型”同盟案例进行无差别验证。考察样本主要包含欧洲地区的意大利、奥匈帝国、冷战时期中东地区的埃及、约旦等国,以及中苏同盟和中美70-80年代“准同盟”。[31]这其中既包含陷入“科林斯难题”的证实案例,也包含成功规避“科林斯难题”的证伪案例。为了确保验证的科学性,本文将不仅关注能够支持基本假说的证实案例,更关注那些证伪案例。只有看似并不符合本文假说的证伪案例仍与这一微观理论的内在逻辑并行不悖,才能够证明该理论的有效性。
(一)对证实案例的考察
案例验证1:19世纪70年代以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意大利地区一直是影响兼具“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的欧洲权力天平的重要砝码。在当时的欧洲大国看来,鉴于意大利地处影响世界权力的“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重合的区位优势,同时鉴于它既没有力量单独成为霸权,又拥有力量使大国间的平衡发生倾覆,欧洲主要强国都谋求通过对意大利让步来换取其合作或效忠。布莱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将意大利这类国家称为“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 [32]。
早在意大利实现统一前,它就习惯了在欧洲各国君主之间充当着待价而沽的大质量砝码角色。例如,皮德蒙特——这个在法国与意大利的奥地利领地之间的缓冲国——在意大利统一战争时期曾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鼓励。当1860年家富尔占领教皇国时,皮德蒙特走的远超拿破仑三世的预料。[33]自1871年实现统一后,意大利更一度获得与“英、法、俄、普、奥”并称的列强身份。因此,从波旁王朝对哈布斯堡王朝,到拿破仑法国对反法同盟,再到同盟国对协约国,对意大利的控制或拉拢往往成为改变“欧洲两极体系时期”权势的关键锁钥。
一战前,意大利与德奥结成了典型的“利益互补型”同盟。在一战爆发后,意大利以“尚未准备充分”为理由——同时以放弃“中立”并加入协约国一方姿态为要挟——对三国同盟进行了趁火打劫式的“二次要价”。它并不关心未来欧洲体系由法国主导还是德国主导,它唯一关心的是意大利作为未来东南欧与亚得里亚海地区支配性大国地位。为此,它对“三国同盟”开出的最新参战报价是:取得蒂罗尔和伊斯特利亚以完成“民族统一”(这两个地区居民中意大利人均不占多数);获得亚得里亚海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近东及殖民事务中的强国地位得到承认。为了最大限度地从同盟内部榨取的让步,迪圣茱莉亚诺7月26日向萨兰德提议:“没有立即决定参战的必要……我们必须使国内外每个人都猜疑我们的态度和决定,以此方式力图得到最多的好处。” [34]
这一自抬身价的战略对盟主德国立刻奏效了。为了让意大利盟友早日投入英德争夺霸权的战争,德国试图劝说奥匈拿出一部分在巴尔干地区所得的利益进行“补偿”。为此,德国前任首相冯·比洛亲自到罗马告诉意大利人:“只要快点参战,他们在弗朗西斯·约瑟夫——奥匈帝国皇帝——口袋里能找到什么,德国就给他什么。” [35]544
德国想让奥匈帝国吐出部分利益来拉拢意大利,以此求得“三国同盟”赢得欧洲体系霸权的良苦用心被只关心巴尔干区域利益的奥地利人当场泼了一盆冷水。关注在东南欧地区建立霸权的奥地利人对德国的“世界政策”与“欧陆霸权”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蒂罗尔——那里居住着30万日耳曼人——是奥匈这个多民族君主国里最坚强的支持者;而在亚得里亚海做出让步则等于把克罗地亚人推进了塞尔维亚的怀抱。正如奥匈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以尖刻的得意态度所言:“要么放弃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德国在近东的地位,要么福祸与共同奥地利并肩前进。” [20]514从为了满足奥匈在巴尔干谋求支配性地位而一再开罪俄国后,德国的“世界政策”不断降格成为协助其弱小盟友追求地区霸权的工具。这注定了当德国踌躇满志地在争夺欧洲与世界霸权的战争中走向战场时,它的两个盟友一个为了局部利益而漫天要价,另一个则不肯为了自己局部的、可能得而复失的利益而服从于整体战略。而此时“三国同盟”的主导国既没有筹码引诱意大利参战,也不敢强迫奥匈对意大利妥协。它只能在两头讨好中坐视意大利的转换同盟。
当意大利人认识到在这种零和博弈中只有奥匈战败才能获得它期待的报酬时,便于1915年3月4日转向了协约国。把敌对同盟奥匈帝国的南欧利益信手转让给意大利,这种“慷他人之慨”的做法除了在俄国会产生些许微词以外,对英法来讲完全欢迎。虽然俄国方面抱怨说,让胃口如此之大的意大利参战只会增加议和时的困难——在战胜国之间可分的胜利成果实在是太少了。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则坚决认为意大利人的参战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将成为打破两大同盟在欧洲战场僵局的转折点——“我们不能只为了给塞尔维亚弄一条长海岸线而拖延这么重大的事情。” [20]544-546鉴于当时的俄军主战场已转向德国,所以俄罗斯需要意大利人在东线帮忙分散奥匈的压力。因此,除了南达尔马提亚归塞尔维亚之外,意大利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协约国的满足。作为回报,意大利答应协约国在一个月内“对它们所有敌国开战。”[3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开始加速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向世界体系的“宽广舞台”转变。美苏两个“侧翼大国”的出现宣告了过去以英、法、德等“中等强国”主导世界秩序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意大利这类欧洲天平的砝码很难再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验证国家实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战争。而意大利给其它体系大国发出的最具身份欺骗性的信号就在于,只要战争看上去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意大利人在外交话语上就永远充满着战斗热情。这使墨索里尼在走向真正战场前仍然保留了“欧洲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平衡砝”角色,虽然在一战时表现平平,但二战前它仍凭借自己造作的表演而成为英法与德国争相拉拢与绥靖的结盟对象。
在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直到1940年意大利进攻法国以前——意大利长期被视为“欧洲四强”的一员。从《洛迦诺公约》英意两国承担德法保证人——这种典型的“威胁一致型”同盟使弱势一方的法国人无奈地称其为“简直是处在英意两个卫兵间的囚徒” [37]86——到1934年“陶尔斐斯被刺杀”后墨索里尼紧急派出四个师陈兵勃伦纳山口,并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急电,承诺意大利支持奥地利独立,从而迫使希特勒赶忙否认对奥地利的任何图谋,到“慕尼黑事件”中的四强决策,再到1938年德国入侵奥地利时的关键性表态,地处影响体系“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高度重合的意大利确实被视为一个比苏联还重要的结盟对象。
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既不是与英法结成对抗德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它本身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也不是帮助德国建立起世界霸权或者对抗更加遥远的苏联。意大利的战略目标是取得法国在环地中海地区——南欧与北非——的区域主导地位。不可否认,墨索里尼凭借自身的政治能力在战前把意大利对南欧、北非诉求的报价抬到了最高。为了赢得意大利的友谊,希特勒在意大利反复宣称,使他深感愤愤不平的是南提罗尔,而不是但泽或波兰走廊。[25]88-89当1936年墨索里尼介入南欧的西班牙内战后,德国也随即卷入了一道支持弗朗哥的内战中。
鉴于意大利的“重要结盟价值”,英法也对意大利追求区域霸权的行为给与了默许和绥靖。1935年3月,英法意在斯特雷扎举行的反德扩军会议上,墨索里尼公开表示:“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组织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达此目的,采取密切而真诚的联合行动。” [38]墨索里尼在演说中着重强调“欧洲和平”几个字,他在说完“欧洲”一词后,又用引人注目的姿势停顿了一下。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英国外交部人员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防止德国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又要为他对非洲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埋下伏笔。通过讨论,英国认为这个时候对意大利提出不得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警告是不合时宜的,这等于把墨索里尼这么重要的合作者推向德国一侧。为了拉拢意大利以壮声势,法国对这一问题也是三缄其口。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自然也就认为国联已默许了他的结盟报价,他可以随时入侵阿比西尼亚了。1935年10月,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则对意大利发动对北非阿比西尼亚的侵略问题推行了绥靖政策,这直接导致国联在道义与威望上的急剧衰落,进而加速了英法主导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
大国争相拉拢意大利对其实现全球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帮助呢?事实证明,在德意这类“安全互补型”同盟协调行动问题上,“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启动异常缓慢。只有当战争形势已经日益明显,或者当主导大国为了小国区域利益而共同作战时,这类同盟才可能显出某些行动力。
作为德国最重要的盟友,意大利并不愿为了德国争夺欧洲霸权而与英法同盟开战,但德国却不得不为支持意大利在南欧、北非冒失的追求环地中海区域霸权而抽调宝贵的军事资源。但意大利对德国追求的欧洲霸权却并不感兴趣,抑或是因为它明白其在德国对英法的战争中也无足轻重。但就在德国即将发动对英法的战争而最需要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却拒绝为德国提供军事协助。当1939年8月25日希特勒焦急等待意大利战争反应时,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带来了墨索里尼的电报:意大利虽然无条件站在德国一边,但它不可能进行“军事介入”。长期干涉西班牙内战已经使意大利筋疲力尽。它的黄金储备和原料消耗殆尽,现代化武器重整军备几乎难以起步。它只有到1942年——甚至这也是一个想象的日期,仅仅意味着相当遥远的将来——才能准备好战争。除非德国立即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战争资源;而当这些战争物资清单发来时,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的话说,“足以使可以预言的任何大话相形见绌”。
只有当形势已经明显表明德国将赢得完全胜利时,意大利才愿意作为德国的同盟投入对英法同盟“坐地分赃”的战争并证明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价值。1940年6月10日——当天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六天前33.8万名英国和盟国士兵已经完成了“敦刻尔克大大撤退”,这基本宣告了英法同盟在欧陆战场的彻底失败——意大利外交部长正式通知英国大使,意大利从当天午夜起与联合王国处于交战状态,对法国也送达了相同的照会。随后,意大利以趁火打劫的姿态,向败局已定的法国阿尔卑斯阵地发动了毫不迟疑的攻击。
法国战败后,墨索里尼加速追求环地中海——南欧与北非——区域霸权的步伐。这一区域战略不仅无法配合德国接下来的对俄战略,更导致了德国在希腊、北非等地不断抽调军队去援助意大利而一再延误“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日期。倘若德国能够心无旁骛地集结侵苏部队,进而提前一个月发动对苏战争,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避免因寒冬而兵败莫斯科的结局。为了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巩固意大利在南欧的支配性地位,1940年10月28日意军贸然入侵希腊,但一个月后便在沃武萨丢失了战场主动权。为了挽救意大利在巴尔干的败局,希特勒临时调集军队于1941年4月——这支部队两个月后就要投入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才将意大利从巴尔干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这一营救行动的短期后果是从希腊战场抽回的德军因来不及休整便投入更大的南俄战场,严重影响了德军“巴巴罗萨”整体的战争计划。长期后果则是希特勒不得不在本想暂时避开的巴尔干地区留下61.2万人的统治兵力。[39]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也遭遇到同样的崩溃窘境。为了挽救意大利盟友,希特勒又不得不从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中抽调出像隆美尔这样的优秀将领和军队分散到北非地区。可见,如果任由“安全互补型”同盟中弱小盟国做出决策,主导大国可能被迫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案例验证2: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进行了激烈的盟友争夺并组建起各自主导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40](参见表2)

表2: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互补型”同盟
表2:关于同盟关系的内容参见:stephen m. walt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154 , p.159; 关于美国培植中东盟友动机的内容参见:peter g. boyle , john l. gaddis , “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 vol.16 , no.3 , 1982 , 223-225 ; john s. badeau , “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the arab world ” ,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 vol. 22, no. 4 , 1969 , pp.10-13 , 17-19 , 137 ; steven l. spiegel , the other arab-israeli conflict ,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 pp.97-98 ; 关于苏联发展中东盟友的动机参见:karen dawisha , “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 , foreign affairs, vol. 58, no. 1 , 1979 , p. 202 ; karen dawisha , " soviet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 permanent interests and changing influence " , arab studies quarterly , vol.2 , no.1 , 1980 , pp. 19-37.
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利用双方试图在“资源核心区”获得排他性优势地位,或阻止对手单方面获得优势地位,将自身谋求阿拉伯国家内部领导地位、制衡以色列的区域战略同是否支持同盟主导国全球战略进行了捆绑销售并取得了明显的榨取效果。虽然美苏两大同盟存在着战略竞争关系,但1955-1979年间伊拉克、叙利亚、北也门、埃及、约旦、黎巴嫩均有从美苏双方获得经济与军事援助的记录。(参见表3)其中,埃及和伊拉克两国在美苏之间出现了实际上的“联盟转换”。

表3:1955-1979年美苏对“安全互补型”区域大国的援助(单位:百万美元)
表3:数据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 ,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 communist stat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 aid and trade in 1974 , washington ,d . c. ,1975 ; cia , communist aid to non-communist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 1979 and 195--1979 ,washington ,d.c. , various years ; stephen m. walt ,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p.219-220.
美国的大中东战略是促使其阿拉伯盟友同以色列和解,进而共同对付苏联的渗透。但埃及的战略则是通过对以色列战争提升其在阿拉伯世界统一进程中的合法性。因此,当1954年美国试图通过拒绝向纳赛尔提供武器援助以此迫使他同以色列和解时,埃及于1955年正式同苏联结盟。1970年,埃及希望同盟主导国苏联派遣防空部队进行消耗战援助时,遭到了柯西金的反对。当他以“老大哥”的姿态告诫埃及人要配合苏联“缓和国际局势”避免“任何可能被以色列好战者利用的事情发生”时,[42]纳赛尔威胁辞职并支持一位亲美总统上台,这一举动迫使苏联被迫冒着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而向其提供援助。[43]
1972年美苏峰会达成在欧洲相互承认、维持现状的初步协定——此时美苏在莫斯科公报中提到了中东地区“和平协议”并就军事缓和达成共识——但这种缓和并不符合中东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只有美苏双方在这一地区存在竞争——而不是和解——才能使它们获得更高的结盟收益。美苏声明使萨达特感到苏联可能为了促成中东和平——此时由于中美接近,苏联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处于被动态势,希望降低中东地区的安全竞争压力——而延缓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为了刺激苏联加快进行援助,萨达特突然通知苏联大使,埃及不再需要苏联军事顾问。到8月底,苏联在埃及的军事顾问从15000名骤减为1000名。[44]在大量驱逐苏联顾问、拒绝苏联利用军事设施后,苏联不得不将美苏缓和的大局放在一边,转而开始增加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虽然降低援助有助于实现美苏在中东地区缓和,进而缓解因中美战略接近而导致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压力。但美苏均害怕因拒绝对地区盟友提供援助而被对方阵营“挖墙脚”。这种战略互疑使得两个超级大国都难以降低对区域盟友的援助规模。到了1973年4月,萨达特宣布他对苏联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完全满意。[45]
美国的盟友约旦也经常通过“威胁与苏联结盟”的方式迫使美国增加援助,以便支持其针对埃及和以色列的区域战略。这与美国通过拉拢埃及、保护以色列的大中东战略本身背道而驰。但为了避免约旦转向苏联一方,美国也不得不被迫向其区域战略表示支持。例如,1963年,当美国发现约旦为了获得武器装备有可能转向苏联阵营,这促使美国向约旦出售m-48坦克和先进的飞机;1968年,侯赛因国王访问莫斯科并同苏联正式建交,这一举动迫使美国恢复向约旦出售武器。1975年,当约旦希望从美国购买霍克-1型防空导弹时,遭到了国会亲以势力的阻挠。为了迫使美国就范,同年一个苏联的高级军事代表团受邀访问了约旦。次年侯赛因国王再度出访莫斯科,正式就防空系统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46]这一外交举动迫使国会迅速转变态度并同意对约旦出口霍克-1型导弹。
案例验证3:上述“安全互补型”同盟案例,对于思考今天土耳其不断宣称向中俄采购武器以胁迫北约盟友提供它所需的武器援助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中国的红旗-9防空导弹在2012年参与土耳其军购竞标并在2013年获得成功。这一消息曾让国人高兴地看到中国向北约国家出口大型防御武器的希望。但事实上讲,土耳其从来就没打算真正购买红旗-9导弹,它不过是想通过对北约打“中国牌”作为要挟北约向其出口法国紫苑中远程防空导弹。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希望通过打“中国牌”以达到对法国继续压价的目的。这一自抬身价的行为马上取得了对北约主导国家施压的成效。在宣称放弃红旗-9防空导弹之后,土方立即与法国展开了购买行动。
自苏联解体后,土耳其与北约的同盟关系就逐渐从“威胁一致型”转变为“安全互补型”。对于土耳其来讲,它对美俄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不关心,它更关心的是其在伊斯兰世界地位的复兴。因此,美俄双方谁更愿意帮助其提升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谁就将成为土耳其的合作对象。土耳近年来反复在美俄之间两面下注便是北约内部同盟关系变化的反映。
一方面,为了迫使美国对其出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f-35隐形战机等尖端武器,土耳其在红旗-9事件后又故伎重演,以签约购进俄国s-400防空导弹系统,作为威胁北约盟主美国向其低价出口尖端武器的筹码。对此,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在2018年11月22日表示:“土耳其从来不依赖唯一选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评判问题。如果美国愿意与土耳其就爱国者防空系统达成协议,并就联合生产达成一致,我们就应该接受。”
另一方面,俄罗斯以s-400为对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其目的明显在于分化和拉拢北约的黑海前哨土耳其。毕竟,土耳其仅需为s-400系统支付45%的货款成本,更多的款项是由俄方主动借贷。这既可以达到弱化甚至瓦解土耳其与北约的“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固有认知,间接增加北约维系与土耳其同盟的成本,又可以通过对部署在土耳其的俄制防空系统的后期维护与后台运行,达到前沿侦测北约各类航空器参数的目的。因此,土耳其正是利用了北约对俄制防空系统的恐惧,逐步实现其要挟盟友在装备与政策上让步的可能性。
对于美国来讲,苏联解体意味着欧洲地区不再是严格意义的“两极竞争”状态。鉴于俄罗斯强大的核武能力,欧洲地区仅仅是一种微弱的“两极”竞争状态。从战略紧迫性角度讲,美国对土耳其的要挟没有必要像冷战时期一样迅速做出妥协性调整。因此,即便土耳其有心自抬身价,也可能面临被盟主美国拒绝的碰壁风险。毕竟,在美国巨大军事优势仍然存在、以及美国对国家利益划分日益清晰的局面下,土耳其的同盟转换并不构成美国生死攸关或极其重要的利益。因此,虽然美土之间的同盟关系是“利益互补型”同盟,但土耳其自抬身价的背后是“两极格局”的虚化以及美国对土耳其在全球战略中价值的重新评估。这种条件的变化造成了土耳其自抬身价的遇阻。
(二)对证伪案例的考察
首先,随着1973年国际原油价格的提升,中东地区作为世界权力“资源核心区”的价值也出现了增长。地区大国在同盟中的价值量也应该出现相应的提高。但问题在于,为什么1979年后,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在美苏之间“以转换同盟为要挟”的报价出现了走低趋势呢?为什么1979年后苏联在中东地区只剩下叙利亚和南也门两个盟友?本文认为,1979年苏联对主权国家阿富汗的军事入侵直接导致了中东地区大国安全威胁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即安全威胁从周边邻国变成了超级大国苏联本身,进而导致了中东地区国家与美国的同盟性质从“安全互补型”演变为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威胁一致型”。
1979年12月末,苏联放弃了“代理人”模式,从地缘政治较量的“幕后”径直走上了“前台”。这场战争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它不仅导致了美苏自1972年缓和局面的结束——美国总统卡特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 [47]——更重要的引发了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自身主权独立与国家安全的担忧。他们最重要与最紧迫的利益不再是通过制衡周边国家而获得区域优势战略,而是防止自身被苏联军事侵略。
随着同盟类型的转变,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的自主性和约束能力明显提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发生在1982年6月9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部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苏联盟友)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战争期间出现了由以色列支持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组织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贝鲁特大屠杀。而在整个“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们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表现的出奇冷静。而这在1970年代是非常可能引发联合军事行动或“石油危机”的。1979年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牢牢紧跟美国,直到苏联解体后安全威胁消除。
第二,为何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威胁一致型”同盟没有出现中国服从苏联的状况,反而出现了中苏对抗呢?本文认为,中苏同盟走向分裂的重要原因就是双方名义上构建的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但实际上仅是意识形态一致性基础上的“安全互补型”同盟。从名义上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角度讲,中苏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区域战略需要服从苏联全球战略安排;但事实上,经历朝鲜战争后,中国眼中最大的威胁以不再是美国。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解放台湾、推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甚至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赫鲁晓夫的战略目标则是推动美苏两极格局下的缓和。苏联凭借“威胁一致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中国服从,而中国则从“安全互补型”同盟的逻辑试图迫使苏联支持其台海战略。因此,这种表面装点并混杂着全球共运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同盟”注定因其逻辑的非相合性而走向分裂。
相反,中美的战略接近正源于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公开入侵以及对中国核打击威胁,促使其与美国迅速达成了“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共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铁列克提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苏联对华“核恐吓”导致了中美之间抛开意识形态分歧而迅速建立起“威胁一致型”准同盟。美国不再强调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也不再强调美国对越南盟友的侵略与帝国主义性质。双方在苏联共同威胁下,迅速建立起准盟关系。这一关系确立后,中国积极调整自身战略姿态,并表现出对美苏全球争霸与亚太战略的积极配合。一方面,在台海问题上中国方面主动降低了区域竞争烈度。另一方面,在支援越南战争方面也表现出基于国家总体战略利益的理性。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对中美双方的安全威胁日益降低。伴随着东欧剧变,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矛盾则走上了前台。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威胁一致型”准盟关系的解体。
第三,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中美越之间出现了“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的态势?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陆上安全就不再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了。但由于中国坚持对自身的国际身份定位在天平托盘而非重要砝码,因此,在美苏两极结构已经趋于稳固的情势下,中国面临着美苏双方的巨大压力。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率领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苏在黑龙江、新疆地区增加的边境冲突促使中国放弃了充当世界第三极的主张,转而接受了自身成为美苏之间重要战略平衡砝的新角色。这就出现了中国在美国与“北越 苏联”之间两面结盟的现象。
一方面,中国与“北越 苏联”政权在越南战争中名义上仍是“威胁一致型”同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年才废止——但事实上随着中美和解而更加明显地降格为“意识形态型”同盟。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基于苏联共同的威胁则出现了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的必要条件。当共同利益较低的“意识形态型”同盟遭遇到共同利益最高的“威胁一致型”同盟时,即便上世纪初70年代初“北越 苏联”默认保留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同盟并默许了通过中国同美国的战略接近,也难免中国在逐渐强化中美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开始疏远意识形态盟友越南,甚至到了1979年双方走到爆发战争的地步。
上面关于中国的两面结盟策略构成了其在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摆脱孤立并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囿于中国在安全上加速倒向西方世界——“一条线”与“一大片”——苏联逐步降低了对中国边境的安全压力并在进攻态势上更加审慎。即便中国对其盟友越南发动军事进攻,苏联也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情绪。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世界为了更好地获得中国的支持,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资金、技术、管理与装备等方面的大力援助。70年代始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选择为中国降低苏联安全威胁和获得美国经济援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科林斯难题”的政治启示
在同盟内部,并非所有小国都是任由大国摆布的可怜虫,在特定条件下它们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局部利益加诸于战略缔造、获得同盟主导权并对战略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科林斯难题”便反映出在“安全互补型”同盟内主导国可能面临的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即构建同盟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的战争能力,而许多战争本身却是为了维持同盟的存续。它反映了“安全互补型”同盟的内在困境,即当偏执的区域盟友所关注的区域战略与同盟主导国关注的整体战略出现非相合性时,如何避免因错误的认知与同样冒进的行为,而导致整体战略被区域战略绑架并拖入到事与愿违的高度危险境地呢?
在两极格局的全球博弈中,历史给了我们一些获取经验的线索和提示。“采取正确结盟战略”的国家获得了来自同盟的巨大力量,而 “采取错误结盟战略”的国家不论其多么努力发展,积累起来的能量都会被对方不断增加的反作用力或己方盟友不断增加的诉求所抵消,甚至有时还会强化对方同盟行动的一致性。本文认为,“采取错误战略”是指犯了三项重大失误:第一,试图通过不断追加投入弥合同盟内部的安全利益认知差异,幻想使“安全互补型”产生与“威胁一致型”同盟一样高的战略效果;第二,在洲级大国时代,即便某个处于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的国家出现了同盟转换,也无法影响到两极格局的力量对比。从近代欧洲多极均势中结晶的话语逻辑可能诱导盟主国家夸大区域盟友的战略价值,从而陷入到“三大战略迷思”;第三,在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展现出过度膨胀的野心、对强权政治的迷恋,将间接帮助战略竞争者在特定区域形成投入成本更低、行动效力更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这一点特别反映在为什么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或波兰等东欧国家比北约的西欧盟友更愿意配合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区域行动。这样会经历双重挫折,即自身盟友的离心力增强,对方盟友的凝聚力大增。因此,“采取正确的结盟战略”意味着对洲级大国时代区域盟友价值的理性认知、有限期待和互惠性支持,以及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众叛亲离与体系性制衡力量的生成。
一战后,国际政治已经从“欧洲体系”的狭小舞台扩展到“全球体系”的宽广舞台。洲级大国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权力博弈已经成为只在主导国之间进行的两极游戏,中等强国对于改变超级大国之间权力对比的边际效用与日递减。尤其是同一个任性妄动、不负责任的地区国家结盟并不意味着增加一笔资产,而是增加一项负担。就如同长期对某一问题的慈善行为非但不能治愈,反而还会增加贫困一样——因为它不仅是对短视与懒惰行为的奖励,而且会鼓励短视与懒惰的人成倍地增加——对“安全互补型”区域盟友无底线的支持,不仅不能换来预期中的战略协作,反而会因自身的沉没成本而增大对方的胃口。因此,同盟主导国必须根据情势的变化而建立起更有效的评估方式,以界定在不同争议地区采取行动的方式、支持限度和承诺底线。其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找到一个主导国能支持的盟友,而是如何能够找到一个盟友愿意支持主导国的大战略。缺乏排查“安全互补型”同盟的这套标准,主导大国可能被那些以“安全利益一致”为名并与之结盟的卫星、附庸、傀儡、客户组成的杂牌军拖入不必要的区域冲突,而不得不在姑息、挫败、纵容以及不可估算的代价之间使全球战略降格、转移直至从属于盟友的区域战略。
尤其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权力“生产核心区”从欧洲分离出来并加速向东亚地区转移。今天世界权力三大核心区主要呈现为欧美控制“技术核心区”、印太居于“生产核心区”,而中东依然是“资源核心区”。[48]冷战至今的历史表明,美国对欧亚大陆潜在对手的遏制是依据三大地缘政治核心区而展开的。正如1988年1月里根宣言所阐释:“美国战略的首要特性在于坚信倘若一个敌对国家将统治亚欧大陆——地球上那个被称之为心脏地带的国家,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就将受到威胁。我们为阻止这种情况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自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力求防止苏联利用其战略优势而支配西欧、东亚和中东地区,从而根本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其对美国不利。” [49]
美国在三大区域内的遏制对象也清晰地表现为俄罗斯(欧洲地区)、伊朗(中东地区)和中国(印太地区)。其中,尤以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冲击最为明显。当前,中国迅速崛起是引发体系新一轮转型的核心变量。一方面表现为中美权力位差迅速收窄,另一方面表现为中美两国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权力位差均在拉大。这就意味着国际体系向两极格局转型可能性明显增加。[50]在体系权力格局从单极向两极演变的进程中,中美之间在印太地区的矛盾可能性与日俱增。这就客观上要求战略理论界提前加强对“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51]
在我们成为另一极之前,中国需要长期延续在各种形式下的不结盟战略,它可以帮助我国避免自身方面陷入盟友制造的“科林斯难题”。同时,如果中国想有所作为,那么可以试图在三大核心区的外线区域展开结盟行动,而不要在内线区域过早地摇落霸权国花园中的果实。同时,美国是否会面临亚太盟友提出的“科林斯难题”,从而面临是否支持其与中国的领土矛盾,也关系到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中国如果想弱化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就需要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类型进行有效区分。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进行部分同盟分化。一方面促使行动力较强的“威胁一致型”同盟转变为行动力较弱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另一方面,避免因自身的战略冒进而导致“安全互补型”同盟升格为“威胁一致型”同盟。为此,中国需要注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四个同盟。
首先,从美日同盟角度看,随着日本从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军事与政治大国的转型,[52]中日之间争夺领土与亚太主导权的进程与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高度一致,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属于“威胁一致型”同盟,因此不仅不具备弱化的可能性,反而随着中国崛起或东海问题而更具行动能力。
其次,从澳大利亚角度看,澳大利亚视中国为未来追求南太平洋区域主导权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这与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呈现出较高一致性,因此美澳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问题上也属于“威胁一致型”同盟。随着中国在南海地区影响力的增加,美澳同盟在对华问题上将更具一致性。但由于澳大利亚距离中国比日本更为遥远,中国可以通过推卸责任、有条件的绥靖、更加温和的外交战略促成美澳同盟安全威胁的降低。
第三,从美韩同盟角度看,韩国的安全关切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安全,它对中美全球战略竞争中涉及朝鲜半岛之外的问题并不关心,1992年中韩建交后更是极力避免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53]。而虽然美国坚持名义上对朝鲜的恐惧——看似美韩同盟是“威胁一致型”——但其实冷战至今以来美国陈兵半岛的根本战略是为了防范中俄。随着中韩建交以来敌对关系的持续降低,今天的美韩同盟以演化为典型的“安全互补型”同盟。因此,只要中国对韩国展现出足够的善意并在朝鲜问题上做出更多共同合作可能性的暗示,就能够降低美国利用美韩同盟共同遏制中国的安全压力。
最后,从菲律宾和新加坡角度看,作为地区小国,它们的安全关切事实上仅局限于南海地区安全,因此美菲同盟与美新同盟既可能属于“安全互补型”,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换为“威胁一致型”同盟。这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是以战略军事为主导,还是以战略经济为主导。只要中国在南海地区持续展现温和与善意——而非咄咄逼人、无视裁决、锱铢必较、处处争抢的权力政治——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的菲律宾和新加坡并不愿意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过分迁怒于中国,而更愿意通过两头下注的“对冲战略”获得中国经济上的好处与美国安全上的援助。反之,则可能诱发两国积极同美国构建“威胁一致型”同盟。
“科林斯难题”属于大国崛起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微观理论,它在精细化同盟类型的基础上发现了差异性的结果。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阐释一种同盟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更在于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与启示。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崛起大国,中国利用和规避“科林斯难题”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对周边小国滥用威慑、奉行单边主义或严重损害本国道义根基的方式,迫使周边国家因感到恐惧或羞辱而与美国形成“威胁一致型”对华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能提高中国成功崛起的机会。
注释
[1] glenn h. snyder. alliances, balance, and stability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5,no.1, 1991,pp.121-14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j]. foreign affairs , vol. 80, no.6, 2001,p.173; john r. deni. allianc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restructuring nato for the 21st century [m]. burlington :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7,pp.9-18; joan m. roberts. alliances, coalitions and partnerships: building collaborative organization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ences, vol.71, no.4,2005,pp.660-662; jack s. levy .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the great powers, 1495-1975[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5,no.4,1981,pp.581-613.
[2]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2009,pp.158-196;robert. o. keohane, celeste a. wallander , eds. , imperfect unions :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07-139 ;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p.182;温斯顿·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下)[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378-379;382;425;刘海军.试论美国的联盟霸权——兼与19世纪的英国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2).pp.32-37.
[3] christopher gelpi . alliances as instruments of intra-allied control [a]. haftendorn , keohan eds. ,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132;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m]. ithaca ,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7,chaps.6 and 9.
[4]本文在考察克里斯托弗•格尔皮(christopher gelpi)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研究样本的基础上,又综合借鉴了同盟条约义务与条款”数据库(the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project,atop),该收录了1815-2003年所有国家签订的军事同盟协定;“战争相关指数”的“正式同盟”数据库(cow formal alliance data)收录了1816-2000至少两个国家签订的所有防御协定、中立或者谅解协议(ententeagreement),提供了同盟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的时间,而且也包括该同盟的生命周期;“毗邻数据”库中的“直接毗邻数据”(direct contiguity data),测量了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之间的毗邻程度和冲突的关系,毗邻领土效应的分解,对可观察和不可观察效应对冲突的影响。
[5]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第44页。
[6] 公共节日聚会系指希腊四大竞技聚会:奥林匹亚竞技会、皮西亚竞技会、地峡竞技会、提洛岛竞技会。本文指在科林斯举行的地峡竞技会,母邦的特权是指荣耀地位,殖民城邦向母邦呈现牺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的典礼等。
[7]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页。
[8]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4页。
[9]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10] 该同盟具有明显的防御性。它不能违背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和约:科基拉人不能要求雅典人和他们联合起来进攻科林斯。只有在本国领土或某个同盟国遭到入侵时,订立盟约的各方才有义务实施援助。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11]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
[12] 科林斯与科基拉海战后,科林斯人卖掉了科基拉俘虏中的800名奴隶,但是对其余250名科基拉公民俘虏却予以特别关照。修昔底德认为:“科林斯人希望他们将来回去后,使科基拉再回到科林斯这边来。后来科林斯实施了这个计划,引发了科基拉的党争和流血冲突。”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13] 学界倾向于将公元前461-前446年间,以雅典人为首的和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两大城邦之间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称公元前431-前404年二者之间的战争为“第二次或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典学论著中,如果不特别注明是哪一次,通常是指修昔底德所著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14]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5]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16]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88页。
[17] 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7页。
[18] 唐纳德·卡根,曾德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206页。
[19] 修昔底德,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79页。
[20]杨原和曹玮认为,这样的两极结构背景下小国更具备“对冲战略”与“两面结盟”的可能性。参见: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j].当代亚太,2015(5): 49-87.
[21] robert j. art .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n[m].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3 , p.45.
[22]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esboard :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m]. philadelphia : basic books , 2016, chapter 3, 5, and 6 . 转引自王鹏.“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j].当代亚太,2018(3):23.
[23] peter green.the greco-persian wars : the greco-persian wars [m].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ian macgregor morris . to make a new thermopylae : hellenism, greek liberation , and 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 [j]. greece & rome , vol.47, no.2 , 2000. pp. 211-230.
[24] robert jervis , jack snyder , eds . ,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c]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 . 23 ;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m].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1 , pp.3-4 ; woodruff d. smith ,the german colonial empire [m]. chapelhill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978 , p.243-270.
[25] “心脏地带”概念最早由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在其1915年的著作《地理和世界强权》中所提出。麦金德将自己“枢纽地区”概念与“心脏地带”理论进行结合,提出了“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3页。此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范围,将东中欧地区视为“心脏地带”的核心部分,并预言“谁控制了东(中)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统治了世界。”参见: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心脏地带”这一概念的外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体系霸主英国依据其控制世界技术核心区需要——从遏制俄国到遏制德国,再到遏制苏联——而在欧洲地区出现了不同范围的调整。二战后,国际体系进入“洲级大国”时代。曾经英法德这样的地缘战略旗手国家沦为体系“中等强国”。本文选取卡赞斯坦对“心脏地带”的界定,将“心脏地带”定义将延伸至北大西洋沿岸的西欧部分也算作霸权技术核心区之内。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26] susan strange . 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london : pinter publishers , 1988,pp.27-28;paul kennedy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m].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 1989 , p. 384 , 436.
[27] eric hobsbawm .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m].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6,pp.309-310, 579 .
[28] michael j. sullivan. measuring global values : the ranking of 162 countries [j]. greenwood press ,vol.51 , no.2 ,1991 , p.72.
[29] hans j. morgenthau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m]. new york : mcgraw-hill , 2005 , pp.348-349.
[30] joseph s. nye. the making of america's soviet policy [m].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 p.242.
[31]国际体系最初的“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高度重合在欧洲。上世纪70年代全球产业结构从欧洲向东亚地区转移,冷战后期至今,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生产核心区”。但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中国于1979年4月30日宣布不再延长该条约。依据条约规定,条约于一年后期满时废止。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至1989年期间,中美“蜜月期”长期保持准盟关系,这种关系就像美国和以色列一样,存在着实际合作,但没有法律条约上的义务。而中苏同盟则经历了多年的实际破裂后走向了自然解体。为了配合“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崛起战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奉行低调的“不结盟政策”。东亚地区的美日同盟则由建立初期的“权威支配型”向“安全一致型”转变,因此也被排除在“安全互补型”同盟类型之外。本文关于“同盟”的定义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参见:张景全.同盟视野探析[j].东北亚论坛,2009(1):29.
[32] brian r. sullivan. the strategy of the decisive weight : italy , 1882-1922 [a].
williamson murray and macgregor knox , eds. , the making of strategy : rulers , states , and war[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p.307-351.
[33] martin wight . power politics [m].london :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978 ,p.167.
[34] 〔美〕布赖恩·沙利文.充当决定性的砝码:意大利的战略(1882-1929[a].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 347-348.
[35]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948-1918[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7, p.544 , 514 , 544-546 .
[36]事实上,意大利又食言了。1915年5月,它只对奥匈宣战了;直到1916年8月28日才对德国宣战。
[37] 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m].new york : fawcett premier , 1978 , p.86 , 88-89 .
[38]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上)[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61.
[3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9,p.373.
[40] stephen larrabee .gorbachev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j]. foreign affairs , vol.66 , no. 5 , 1988 , pp.1002-1026 ; celeste a. wallander . third-world conflict in soviet military thought : does the “new thinking”grow prematurely grey?[j].world politics , vol.42 , no.1 , 1989 , pp.31-63.
[41] 1962年12月,肯尼迪总统明确美国和以色列具有特殊关系——美国对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成为美国对以政策的核心与基点。
[42]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 . 243.
[43] mohammad heikal . the road to ramadan[j]. middle east journal , vol. 30, no. 4 , 1976 , pp. 83-90.
[44] george w. breslauer. soviet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j]. foreign affairs , vol. 69 , no. 4 , 1990 , pp.995-96 ; alvin z. rubinstein . red star on the nile[j]. soviet studies , vol. 30 , no. 3 , 1978 , pp.188-191,202-211 .
[45] jon d. glassman . arms for the arabs: the soviet union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 vol. 426 , no.2 , 1976 , p.96 ; robert o. freedman . moscow and the middle east: soviet policy since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67, no. 4 , 1991 , p.102 ; alvin z. rubinstein. red star on the nile [j]. soviet studies , vol. 30 , no. 3 , 1978 , pp. 215-216 , 228-229 .
[46] galia gol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lo since the war in lebanon [j]. middle east journal , vol. 40 , no. 2 , 1986 , p. 241 .
[47] 董秀丽.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361.
[48] 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摘要中建议,要在印太、欧洲、中东以及西方世界地区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特别是对于前面三个地区,美国必须凭借“以实力求和平”的手段吓阻挑战。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eb/ol].january 2018. http://www.defence 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 –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49] 〔美〕科林·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a].〔美〕威廉森·默里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629.
[50]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4-73.
[51] 阎学通.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再思考——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分论坛综述[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8月14日,http://www.cssn.cn/gj/gj_hqxx/201808/t20180814_4541236_1.shtml
[52] 巴殿君,沈和.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内在逻辑[j].东北亚论坛,2017(6):24.
[53] 张慧智.中美竞争格局下的中韩、美韩关系走向与韩国的选择[j].东北亚论坛,2019(2):21.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原题《砝码国家何以自抬身价?——两极格局下同盟政治中的“科林斯难题”研究》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