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近年来,社会抗议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潮流,从美国、欧洲到亚洲,没有几个国家能够避开社会抗议运动。尽管社会抗议运动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但对任何社会来说,无论是对抗议者本身还是对社会整体,任何形式的社会抗议都是有成本的。对抗议者本身来说,除了极少数组织者可以获利之外,大多数参与者(包括旁观者)并没有获利,却要花费精力和时间。
社会抗议的组织者一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例如被逮捕和起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社会声望,获得日后从政的机会。多数人除了增加一些生活经验之外,则没有任何机会。对社会整体来说,社会抗议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正常运作(包括政府)产生负面影响。
对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如果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理解和化解当代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活动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抗议或许不可或缺,但一个社会也不能总是处于抗议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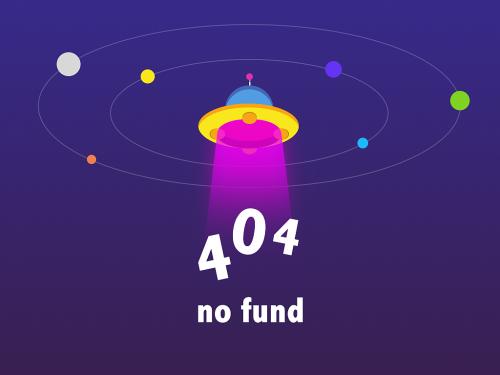
俄罗斯民众抗议普京
从理解的角度来看,人们或许可以把社会抗议运动及其可能的结果,理解为自然界频繁发生的“堰塞湖现象”。堰塞湖是由火山熔岩流或地震活动等因素,引起山崩滑坡体等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一般来说,堰塞湖的形成有四个过程:一是原有水系的存在;二是原有水系被堵塞物堵住;三是河谷、河床被堵塞后,流水聚集并且往四周漫溢;四是储水到一定程度便形成堰塞湖。
堰塞湖的堵塞物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也会受冲刷、侵蚀、溶解、崩塌等等。一旦堵塞物被破坏,湖水便漫溢而出,倾泻而下,形成洪灾。伴随次生灾害的不断出现,堰塞湖的水位可能会迅速上升,可能导致重大洪灾。灾区形成的堰塞湖一旦决口,后果严重,对下游形成洪峰,破坏性不亚于灾害的破坏力。
如果把社会抗议群体比喻成“堰塞湖”,就不难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尽管不想看到“堰塞湖”的出现,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堰塞湖”不可避免;同样,尽管很多人不想看到社会抗议,但社会抗议一直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对人类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堰塞湖”是否会出现,而在于如何消解其所能产生的后果和灾难;同样,对统治者来说,问题并不在于社会抗议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如何利用社会抗议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来管控社会抗议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社会抗议运动本身也是可以有所启示的。抗议运动如同“堰塞湖”,内部充满变化动力。“堰塞湖”的形成只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本身没有任何目的;但“堰塞湖”本身的活动则有可能最终导致“堰塞湖”的“决堤”,最终导致其解体和消失;另一方面,社会抗议运动是有目的的,但因为其内部变化动力所致,社会抗议可能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自身的消失。
“发声”和“退出”的相互关系
对“堰塞湖”的处理,不管是用“外部手术”还是内部变化动力,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对理解社会抗议运动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一,“堰塞湖”内部的面积和水位深度,与其所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面积越广、水位越深(高),内部的变化动力越强,对堵塞物所能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导致“决堤”。社会抗议也是如此。所有社会抗议都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引起的。很多抗议开始时可能只是抱怨,要求并不高;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社会抗议就可能消退了。
这是一种“一次一个要求”的抗议。不过,也有可能在一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或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说,抗议者的要求可能越来越高,直到不能满足为止。但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抗议者的积怨就会越来越深,对社会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
在不同政体下,社会抗议的“积怨”程度也会不同。在民主社会,因为社会抗议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而且风险不高,甚至没有风险,所以社会抗议经常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的忍受度一般极低,一旦对社会产生不满,就随意表达出来。不过,从经验来说,这种被人们广为称颂的社会抗议环境(例如组织自由、集会自由、民主等)并不见得有效,或者说,容易发生的社会抗议,其效果也相对无效。在很多社会,社会抗议已经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可以借用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出的“发声”和“退出”的概念来理解。赫希曼认为,当人们发现一个公司、组织或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的质量下降时,人们便开始“发声”(voice)或者“退出”(exit),以表示不满。“退出”很简单,就是离开,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质量产品(服务)的公司、组织和国家。“发声”就是抱怨公司和组织,意在改进公司和组织所提供产品(服务)的质量;“退出”则不同,无论是间接的“退出”还是无意的“退出”,都会阻碍公司或组织去改善业绩。
因此,尽管“退出”和“发声”都是人们的选择,但结果很不相同。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矛盾,互相破坏,“退出”尤其能够破坏“发声”。如果“退出”很方便,很容易,“发声”就不容易发生,因为“发声”往往需要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例如,如果离婚足够简单,夫妻双方就很可能不会通过“发声”(沟通或和解)来挽救婚姻。在美国历史上,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因为西部开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所以与欧洲比较,美国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很多情况下,“退出”的选择倾向于破坏“发声”。赫希曼认为,这可以用“水利模型”来表示,公司、组织和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的降低产生了社会抗议的压力,抗议的压力则会导致“发声”或“退出”;但如果通过“退出”选择所消解的压力越多,形成有效“发声”的机会就越小。
“退出”选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民主社会抗议的无效。民主社会往往拥有多党制,权力在不同政党之间轮换。很多社会抗议往往具有“党派”性质,要么为党派所发动,要么为党派所利用。即使不具有党派色彩的社会抗议,其参与者的选择也相对简单。例如对党派a不满,就简单地选择“退出”,转而支持党派b或c。
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得社会抗议的强度不会那么大,但政治效用也相对减少。人们总是预期换一个政党执政情况会变好,他们的要求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但问题是,由社会抗议者支持的政党一上台,也会面临同样的环境,反对党也会和原来的执政党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因此,政治权力在不同党派之间的转移尽管表达了民主性,或者说反映了社会抗议者的“声音”,但执政的实际效果不会得到改善。这导致人们所说的“几个都是烂苹果,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的情况。
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
与民主社会相比较,权力集中或学界所说的威权主义社会,到了社会抗议阶段往往已经是“深仇大恨”。在威权主义社会,“发声”往往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即使发出了“声音”,发声者面临的风险也很高,所以理性的人往往选择不“发声”,直到“不得不”发声为止,即到了不可忍受、非发声不可的时候。考虑到威权主义社会的民众也是最有忍耐力的,一旦到了“发声”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声音”往往是最激烈、最有破坏性。
不过,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不见得无效,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民主社会更有效。这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先,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群体面临“退出”问题。这些国家要么是一党制国家,要么是一党独大国家。在前者,根本就不存在“退出”的选择,因为没有反对党的存在。唯一的“退出”就是向国外“移民”,但这个选择反而降低了对原来社会的压力,这种“退出”对原来的社会毫无益处。
在后者,因为一党独大,人们对合法存在的小党的效用存有怀疑,往往也不做“退出”的选择。这种局面决定了威权主义国家“发声”的“艺术”和“质量”。因为具有风险,人们就要讲究“发声”的艺术,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用的方式“发声”;而“发声”的艺术也往往提高“声音”的质量。
其次,执政者的忧虑和主动解决。威权也意味着责任。如果执政者足够理性,就必须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一党独大国家,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或者说,执政党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执政者深知“一旦发声便是深仇大恨”的道理,也深知“决堤”所能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所能造成的破坏,因此,为了避免大面积“决堤”现象的产生,执政党就必须主动“倾听”社会所发出的“声音”,主动解决问题,满足社会的需要。
唯一不同的是,“发声者”或“声音组织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执政党不希望现存“声音”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潜在的反对党),所以往往对这些角色实行高压管控政策。西方一般认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声音”无效,但这个论断并不符合经验证据,因为从经验来看,威权主义国家的诸多“声音”在一定条件下,也促成诸多有意义的实际政策变化,有些变化甚至较之民主国家更能反映社会的变化。
第二,“堰塞湖”内部和外部的水位落差关系。很简单,“堰塞湖”内部水位与外面水位落差越大,“决堤”时刻所产生的冲击力就越大;反之,两者的落差越小,“决堤”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决堤”,所造成的冲击力也不会太强烈。
社会运动的强度其实也是如此。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差异过大,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例如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初期(也就是从没有民主到有民主的转型时期),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甚至很暴力;反之,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差异不大,社会运动往往趋于平和,例如一个已经民主化的社会,社会运动(即要求更多的民主)不会像初期那样激烈和具有暴力性。
理解这种“落差关系”对执政者防止社会剧变、维持秩序也具有意义,即“落差”问题不仅可以解决,也可以预防;但如果被忽视、不去解决,日子久了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落差变得越来越大)。
其一,执政者可以对社会抗议进行“疏导”工作,正如可以人工炸掉“堰塞湖”的堵塞物。炸掉堵塞物就是让“堰塞湖”内部的水和外部的水融合在一起。如上所说,这里的“成本”就是如何处理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其二,提高外部的水量,让外部的水位和“堰塞湖”内部的水位差不多一样高,使得内部水量对外部没有冲击力,甚至有可能高过内部水位,这样彻底消除“堰塞湖”。这种情形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不过,这种现象并不难观察到。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因为内地经济落后,生活困难,人们大规模(非法)逃亡到香港,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准急剧提高,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形也可以应用到两岸关系。如果随着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各方面权利逐渐实现,香港、台湾和内地(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和台湾社会运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近年来,社会抗议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潮流,从美国、欧洲到亚洲,没有几个国家能够避开社会抗议运动。尽管社会抗议运动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但对任何社会来说,无论是对抗议者本身还是对社会整体,任何形式的社会抗议都是有成本的。对抗议者本身来说,除了极少数组织者可以获利之外,大多数参与者(包括旁观者)并没有获利,却要花费精力和时间。
社会抗议的组织者一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例如被逮捕和起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社会声望,获得日后从政的机会。多数人除了增加一些生活经验之外,则没有任何机会。对社会整体来说,社会抗议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正常运作(包括政府)产生负面影响。
对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如果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理解和化解当代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活动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抗议或许不可或缺,但一个社会也不能总是处于抗议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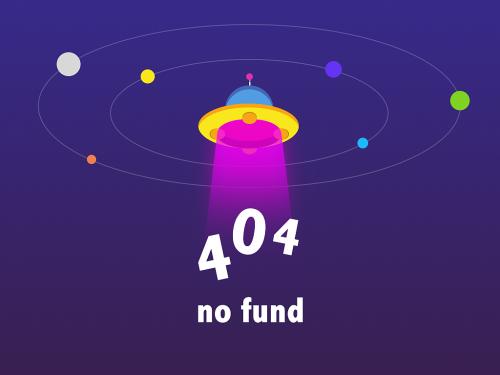
俄罗斯民众抗议普京
从理解的角度来看,人们或许可以把社会抗议运动及其可能的结果,理解为自然界频繁发生的“堰塞湖现象”。堰塞湖是由火山熔岩流或地震活动等因素,引起山崩滑坡体等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一般来说,堰塞湖的形成有四个过程:一是原有水系的存在;二是原有水系被堵塞物堵住;三是河谷、河床被堵塞后,流水聚集并且往四周漫溢;四是储水到一定程度便形成堰塞湖。
堰塞湖的堵塞物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也会受冲刷、侵蚀、溶解、崩塌等等。一旦堵塞物被破坏,湖水便漫溢而出,倾泻而下,形成洪灾。伴随次生灾害的不断出现,堰塞湖的水位可能会迅速上升,可能导致重大洪灾。灾区形成的堰塞湖一旦决口,后果严重,对下游形成洪峰,破坏性不亚于灾害的破坏力。
如果把社会抗议群体比喻成“堰塞湖”,就不难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尽管不想看到“堰塞湖”的出现,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堰塞湖”不可避免;同样,尽管很多人不想看到社会抗议,但社会抗议一直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对人类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堰塞湖”是否会出现,而在于如何消解其所能产生的后果和灾难;同样,对统治者来说,问题并不在于社会抗议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如何利用社会抗议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来管控社会抗议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社会抗议运动本身也是可以有所启示的。抗议运动如同“堰塞湖”,内部充满变化动力。“堰塞湖”的形成只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本身没有任何目的;但“堰塞湖”本身的活动则有可能最终导致“堰塞湖”的“决堤”,最终导致其解体和消失;另一方面,社会抗议运动是有目的的,但因为其内部变化动力所致,社会抗议可能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自身的消失。
“发声”和“退出”的相互关系
对“堰塞湖”的处理,不管是用“外部手术”还是内部变化动力,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对理解社会抗议运动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一,“堰塞湖”内部的面积和水位深度,与其所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面积越广、水位越深(高),内部的变化动力越强,对堵塞物所能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导致“决堤”。社会抗议也是如此。所有社会抗议都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引起的。很多抗议开始时可能只是抱怨,要求并不高;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社会抗议就可能消退了。
这是一种“一次一个要求”的抗议。不过,也有可能在一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或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说,抗议者的要求可能越来越高,直到不能满足为止。但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抗议者的积怨就会越来越深,对社会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
在不同政体下,社会抗议的“积怨”程度也会不同。在民主社会,因为社会抗议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而且风险不高,甚至没有风险,所以社会抗议经常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的忍受度一般极低,一旦对社会产生不满,就随意表达出来。不过,从经验来说,这种被人们广为称颂的社会抗议环境(例如组织自由、集会自由、民主等)并不见得有效,或者说,容易发生的社会抗议,其效果也相对无效。在很多社会,社会抗议已经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可以借用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出的“发声”和“退出”的概念来理解。赫希曼认为,当人们发现一个公司、组织或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的质量下降时,人们便开始“发声”(voice)或者“退出”(exit),以表示不满。“退出”很简单,就是离开,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质量产品(服务)的公司、组织和国家。“发声”就是抱怨公司和组织,意在改进公司和组织所提供产品(服务)的质量;“退出”则不同,无论是间接的“退出”还是无意的“退出”,都会阻碍公司或组织去改善业绩。
因此,尽管“退出”和“发声”都是人们的选择,但结果很不相同。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矛盾,互相破坏,“退出”尤其能够破坏“发声”。如果“退出”很方便,很容易,“发声”就不容易发生,因为“发声”往往需要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例如,如果离婚足够简单,夫妻双方就很可能不会通过“发声”(沟通或和解)来挽救婚姻。在美国历史上,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因为西部开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所以与欧洲比较,美国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很多情况下,“退出”的选择倾向于破坏“发声”。赫希曼认为,这可以用“水利模型”来表示,公司、组织和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的降低产生了社会抗议的压力,抗议的压力则会导致“发声”或“退出”;但如果通过“退出”选择所消解的压力越多,形成有效“发声”的机会就越小。
“退出”选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民主社会抗议的无效。民主社会往往拥有多党制,权力在不同政党之间轮换。很多社会抗议往往具有“党派”性质,要么为党派所发动,要么为党派所利用。即使不具有党派色彩的社会抗议,其参与者的选择也相对简单。例如对党派a不满,就简单地选择“退出”,转而支持党派b或c。
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得社会抗议的强度不会那么大,但政治效用也相对减少。人们总是预期换一个政党执政情况会变好,他们的要求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但问题是,由社会抗议者支持的政党一上台,也会面临同样的环境,反对党也会和原来的执政党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因此,政治权力在不同党派之间的转移尽管表达了民主性,或者说反映了社会抗议者的“声音”,但执政的实际效果不会得到改善。这导致人们所说的“几个都是烂苹果,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的情况。
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
与民主社会相比较,权力集中或学界所说的威权主义社会,到了社会抗议阶段往往已经是“深仇大恨”。在威权主义社会,“发声”往往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即使发出了“声音”,发声者面临的风险也很高,所以理性的人往往选择不“发声”,直到“不得不”发声为止,即到了不可忍受、非发声不可的时候。考虑到威权主义社会的民众也是最有忍耐力的,一旦到了“发声”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声音”往往是最激烈、最有破坏性。
不过,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不见得无效,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民主社会更有效。这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先,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群体面临“退出”问题。这些国家要么是一党制国家,要么是一党独大国家。在前者,根本就不存在“退出”的选择,因为没有反对党的存在。唯一的“退出”就是向国外“移民”,但这个选择反而降低了对原来社会的压力,这种“退出”对原来的社会毫无益处。
在后者,因为一党独大,人们对合法存在的小党的效用存有怀疑,往往也不做“退出”的选择。这种局面决定了威权主义国家“发声”的“艺术”和“质量”。因为具有风险,人们就要讲究“发声”的艺术,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用的方式“发声”;而“发声”的艺术也往往提高“声音”的质量。
其次,执政者的忧虑和主动解决。威权也意味着责任。如果执政者足够理性,就必须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一党独大国家,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或者说,执政党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执政者深知“一旦发声便是深仇大恨”的道理,也深知“决堤”所能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所能造成的破坏,因此,为了避免大面积“决堤”现象的产生,执政党就必须主动“倾听”社会所发出的“声音”,主动解决问题,满足社会的需要。
唯一不同的是,“发声者”或“声音组织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执政党不希望现存“声音”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潜在的反对党),所以往往对这些角色实行高压管控政策。西方一般认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声音”无效,但这个论断并不符合经验证据,因为从经验来看,威权主义国家的诸多“声音”在一定条件下,也促成诸多有意义的实际政策变化,有些变化甚至较之民主国家更能反映社会的变化。
第二,“堰塞湖”内部和外部的水位落差关系。很简单,“堰塞湖”内部水位与外面水位落差越大,“决堤”时刻所产生的冲击力就越大;反之,两者的落差越小,“决堤”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决堤”,所造成的冲击力也不会太强烈。
社会运动的强度其实也是如此。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差异过大,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例如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初期(也就是从没有民主到有民主的转型时期),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甚至很暴力;反之,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差异不大,社会运动往往趋于平和,例如一个已经民主化的社会,社会运动(即要求更多的民主)不会像初期那样激烈和具有暴力性。
理解这种“落差关系”对执政者防止社会剧变、维持秩序也具有意义,即“落差”问题不仅可以解决,也可以预防;但如果被忽视、不去解决,日子久了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落差变得越来越大)。
其一,执政者可以对社会抗议进行“疏导”工作,正如可以人工炸掉“堰塞湖”的堵塞物。炸掉堵塞物就是让“堰塞湖”内部的水和外部的水融合在一起。如上所说,这里的“成本”就是如何处理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其二,提高外部的水量,让外部的水位和“堰塞湖”内部的水位差不多一样高,使得内部水量对外部没有冲击力,甚至有可能高过内部水位,这样彻底消除“堰塞湖”。这种情形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不过,这种现象并不难观察到。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因为内地经济落后,生活困难,人们大规模(非法)逃亡到香港,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准急剧提高,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形也可以应用到两岸关系。如果随着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各方面权利逐渐实现,香港、台湾和内地(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和台湾社会运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