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去年春天,国内一位高三学生给在美国教书的我打来电话,平时我会因为昂贵的费用而挂掉电话改用短信联系,但这一次我没有犹豫就接起了这个国际长途,因为他有特权。前年暑假我去都江堰某高中支教的时候到他们班做过一次讲座,那天他来得最晚,坐在轮椅上,一个同学推他进了教室,后来我得知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他失去了双腿。去美国后我们联系过几次,他曾给我发过一张震前自己的照片,穿着黑白相间的背心,秀着他强壮的手臂。虽然身体残障,他仍然保持着打篮球的爱好,表现得十分积极乐观。
这次他打来越洋电话,我估计一定是有要事,如我所料,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都不理想,加上内心想要报答父母朋友照顾之恩的强烈愿望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有些力不从心。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退路,看到其他年轻人读书不成下海经商或去深圳打工都混得还行,问我人生是否除了通过读书进一个好学校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我当然理解他的心思,也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我也表露了我的担忧,毕竟于他来说高考考个好分数进入一个较好的大学是最优选择。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很多基础设施、教育环境、残疾人待遇都还在缓慢发展,一个好大学能给他提供最大化的便利和机会。如果在学业上有更高追求,他甚至应当考虑在未来去欧美攻读硕士,因为相比目前中国的环境,欧美社会对残疾人士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电话那头的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创造同样辉煌的人生;电话这头的我只能抱以祝福和希望,等待他的好消息。
来到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后,我不断感受到学校和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照顾。工作不久,我参加了学校网站的编辑培训,在添加图片这一环节,培训师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后台编辑时添加内置的图片文字说明。起初我并不理解,因为一张主题很明显的图并没有添加文字说明的必要,而且会浪费时间。后来培训师解释这样的注释是为盲人或其他有阅读障碍的人考虑而设计的,当他们的鼠标移到图片上时,专门的软件会播放图片文字说明,即使盲人也可以顺利阅读网站内容。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给我带来了一种关于人文情怀的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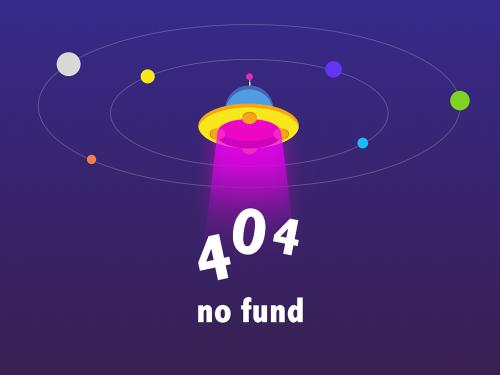
威廉玛丽学院
感动还在继续。在一个朋友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环节除了在大屏幕上显示即时字幕外,还有一位手语老师在一旁翻译,如此一来可以完全照顾到听障人士。在体育馆这几千位家长中,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也许只有很少数,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被遗忘。
身体障碍人士也同样没有被遗忘。除了在机场看到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肢残人士接机外,我还在长途汽车站见识到了残障人士的特权。一次我坐车去纽约,原本是下午两点左右发车,但是由于人很多,头一班车我没有排上。再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终于挤上了下一班车,而在我后面仍有大队人马在排队。但在我上车找座的时候,发现一位女士坐在轮椅上,占了前后三排总共六个座位的空间。我相信这一幕在国内是很难发生的。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离超市门口最近的停车位都是为残疾人预留,就连麦当劳设在户外的桌子都特地为坐轮椅的人设计了几个没有凳子的位子,等等。我一直都很忌讳“残疾人”这个称呼,因为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残疾”这一定语,而非“人”本身。我在波士顿最古老的地铁上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指示牌——“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人在前,残疾在后,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在我所在的大学,有很多残疾人员工。每天中午我去学校食堂买三明治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位肢残的先生在收银台忙碌。他只用单臂就能完成很多常人需要两只手才能完成的动作,尽管可能会占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学生并没有为此不耐烦。我常常看到他跟学生打招呼、热络地聊天,没有任何人向他投去异样的眼光。
自1990年7月26日《美国残疾人保护法》签署至今,美国政府和社会对残疾人权益的保护从基础设施到就业保障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改变。2010年,奥巴马在白宫庆祝该法案通过20年,并下令要求联邦政府提高残疾人雇员比例。1991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开始施行,2006年中国则加上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但其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就以基础设施来说,连中国大中城市的道路、地铁、公交等也缺乏配套的残障设施,残疾人没有他人帮助寸步难行,更遑论融入社会、正常学习和工作了。据中国残联推算,中国目前已有残疾人8500万,但如此庞大数量的残疾人,仿佛都在公共生活之外,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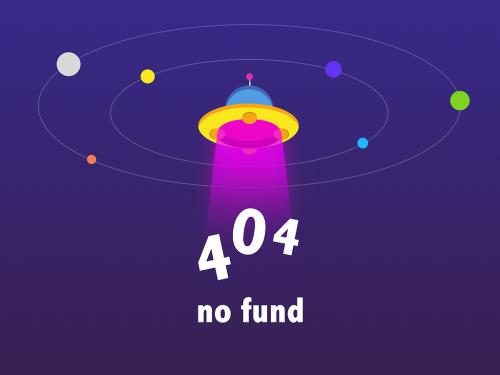
政策上保障残疾人的权益只是第一步,观念上的改变更为关键。而这种观念,既包括旁人的看法,也包含残疾人自身的认识。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在家乡四川的一所益智学校做志愿者,里面有二十几位患有先天听障的学生。与这所学校结缘,是由于我的一位儿时好友也在这所学校就读。这些孩子基本都住校,父母大多都在农村,几个月才出现一次,来送些衣物和吃的。他们唯一的一间教室很小很破旧,学生们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是在一张水泥桌上打乒乓球。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存在,而知道的人也仅仅听说这是一所“聋哑学校”。我常常跟人辩解他们并不哑,只是聋而已。我的那位儿时好友和我聊天的时候,常常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他的父母也有类似的忧虑。23岁那年,他高中毕业了,先是在装饰公司做搬运工,几个月后换了工作,在一家手机店卖手机、贴膜,老板没因为他有听力障碍而压低他的薪水,他也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高兴。前不久我见到他,他带着女友在江边散步,用着苹果手机,精神状态很好。他向我要了一张美元,说以后想去美国玩。
在美国,我的一位学生也向往去中国玩。他在大学学中文两年了,非常聪明,腿脚不便并没有阻碍他向往中国的心。他申请到了两份奖学金,在北大进修了一年,周游了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还去了香港和台湾。他的一位任课老师说,他从不自卑,在课上总是带头发言,很能调动班里的气氛。平日里,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的生理缺陷,只会羡慕他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他是学生最高荣誉的获得者,每个年级仅有四人获得此荣誉,获奖者可以申请基金支持自己的研究项目)。我每次见到他,都被他积极、激情的人生态度所感染。在这所知名的高校,他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及制度上的照顾,可以十分容易地获取资源,以使自己取得更大的发展。在人们和他自己的眼里,“残疾”这个定语将永远被放在后面,甚至被忽略。
我是多么担心那位高三学生因压力过大而懈怠最后放弃了大学,怕他以后要走的路太艰难,尤其是在工作方面。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一年多过去了,他已经在四川的一所大学度过了大一的时光,读的是会计专业,他自称“比较适合我的身体状况”。2008年的地震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突然的变化,包括永远的残疾。但是有些东西一直都没变,比如他开朗的个性和对篮球的热爱。今年他参加了某时尚杂志的封面明星选拔赛,获得了成都赛区的人气王称号。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和阳光,对这个社会充满期待。我也期待这个社会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能让他何时何地都获得尊重和平等的待遇,能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去美国看一场现场的nba球赛。“你还在坚持打篮球吗?”我问他。“当然在啊!那是我的最爱,我会一直打下去!”他坚定地说。
去年春天,国内一位高三学生给在美国教书的我打来电话,平时我会因为昂贵的费用而挂掉电话改用短信联系,但这一次我没有犹豫就接起了这个国际长途,因为他有特权。前年暑假我去都江堰某高中支教的时候到他们班做过一次讲座,那天他来得最晚,坐在轮椅上,一个同学推他进了教室,后来我得知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他失去了双腿。去美国后我们联系过几次,他曾给我发过一张震前自己的照片,穿着黑白相间的背心,秀着他强壮的手臂。虽然身体残障,他仍然保持着打篮球的爱好,表现得十分积极乐观。
这次他打来越洋电话,我估计一定是有要事,如我所料,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都不理想,加上内心想要报答父母朋友照顾之恩的强烈愿望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他有些力不从心。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退路,看到其他年轻人读书不成下海经商或去深圳打工都混得还行,问我人生是否除了通过读书进一个好学校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性。我当然理解他的心思,也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我也表露了我的担忧,毕竟于他来说高考考个好分数进入一个较好的大学是最优选择。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很多基础设施、教育环境、残疾人待遇都还在缓慢发展,一个好大学能给他提供最大化的便利和机会。如果在学业上有更高追求,他甚至应当考虑在未来去欧美攻读硕士,因为相比目前中国的环境,欧美社会对残疾人士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电话那头的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创造同样辉煌的人生;电话这头的我只能抱以祝福和希望,等待他的好消息。
来到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后,我不断感受到学校和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照顾。工作不久,我参加了学校网站的编辑培训,在添加图片这一环节,培训师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后台编辑时添加内置的图片文字说明。起初我并不理解,因为一张主题很明显的图并没有添加文字说明的必要,而且会浪费时间。后来培训师解释这样的注释是为盲人或其他有阅读障碍的人考虑而设计的,当他们的鼠标移到图片上时,专门的软件会播放图片文字说明,即使盲人也可以顺利阅读网站内容。这是这个国家第一次给我带来了一种关于人文情怀的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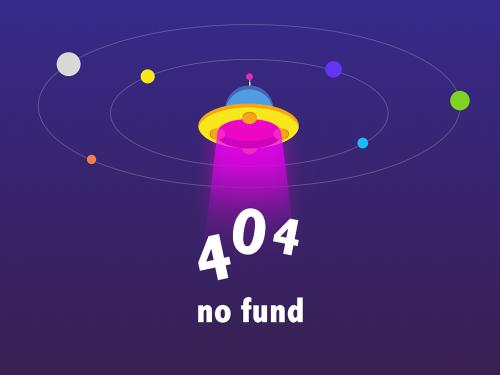
威廉玛丽学院
感动还在继续。在一个朋友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环节除了在大屏幕上显示即时字幕外,还有一位手语老师在一旁翻译,如此一来可以完全照顾到听障人士。在体育馆这几千位家长中,有听力障碍的人群也许只有很少数,但是在这里他们没有被遗忘。
身体障碍人士也同样没有被遗忘。除了在机场看到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肢残人士接机外,我还在长途汽车站见识到了残障人士的特权。一次我坐车去纽约,原本是下午两点左右发车,但是由于人很多,头一班车我没有排上。再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终于挤上了下一班车,而在我后面仍有大队人马在排队。但在我上车找座的时候,发现一位女士坐在轮椅上,占了前后三排总共六个座位的空间。我相信这一幕在国内是很难发生的。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离超市门口最近的停车位都是为残疾人预留,就连麦当劳设在户外的桌子都特地为坐轮椅的人设计了几个没有凳子的位子,等等。我一直都很忌讳“残疾人”这个称呼,因为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残疾”这一定语,而非“人”本身。我在波士顿最古老的地铁上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指示牌——“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人在前,残疾在后,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在我所在的大学,有很多残疾人员工。每天中午我去学校食堂买三明治的时候,都会遇见一位肢残的先生在收银台忙碌。他只用单臂就能完成很多常人需要两只手才能完成的动作,尽管可能会占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学生并没有为此不耐烦。我常常看到他跟学生打招呼、热络地聊天,没有任何人向他投去异样的眼光。
自1990年7月26日《美国残疾人保护法》签署至今,美国政府和社会对残疾人权益的保护从基础设施到就业保障各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改变。2010年,奥巴马在白宫庆祝该法案通过20年,并下令要求联邦政府提高残疾人雇员比例。1991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开始施行,2006年中国则加上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但其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就以基础设施来说,连中国大中城市的道路、地铁、公交等也缺乏配套的残障设施,残疾人没有他人帮助寸步难行,更遑论融入社会、正常学习和工作了。据中国残联推算,中国目前已有残疾人8500万,但如此庞大数量的残疾人,仿佛都在公共生活之外,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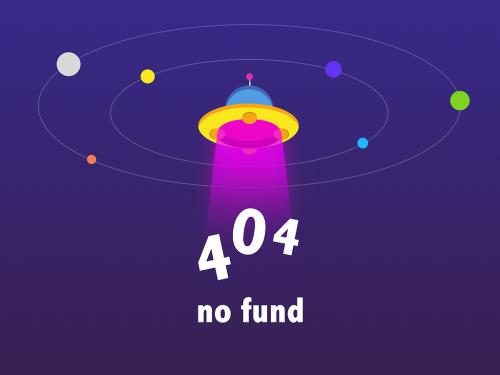
政策上保障残疾人的权益只是第一步,观念上的改变更为关键。而这种观念,既包括旁人的看法,也包含残疾人自身的认识。从高中开始,我就一直在家乡四川的一所益智学校做志愿者,里面有二十几位患有先天听障的学生。与这所学校结缘,是由于我的一位儿时好友也在这所学校就读。这些孩子基本都住校,父母大多都在农村,几个月才出现一次,来送些衣物和吃的。他们唯一的一间教室很小很破旧,学生们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是在一张水泥桌上打乒乓球。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存在,而知道的人也仅仅听说这是一所“聋哑学校”。我常常跟人辩解他们并不哑,只是聋而已。我的那位儿时好友和我聊天的时候,常常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他的父母也有类似的忧虑。23岁那年,他高中毕业了,先是在装饰公司做搬运工,几个月后换了工作,在一家手机店卖手机、贴膜,老板没因为他有听力障碍而压低他的薪水,他也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高兴。前不久我见到他,他带着女友在江边散步,用着苹果手机,精神状态很好。他向我要了一张美元,说以后想去美国玩。
在美国,我的一位学生也向往去中国玩。他在大学学中文两年了,非常聪明,腿脚不便并没有阻碍他向往中国的心。他申请到了两份奖学金,在北大进修了一年,周游了中国大陆的很多城市,还去了香港和台湾。他的一位任课老师说,他从不自卑,在课上总是带头发言,很能调动班里的气氛。平日里,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的生理缺陷,只会羡慕他所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他是学生最高荣誉的获得者,每个年级仅有四人获得此荣誉,获奖者可以申请基金支持自己的研究项目)。我每次见到他,都被他积极、激情的人生态度所感染。在这所知名的高校,他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及制度上的照顾,可以十分容易地获取资源,以使自己取得更大的发展。在人们和他自己的眼里,“残疾”这个定语将永远被放在后面,甚至被忽略。
我是多么担心那位高三学生因压力过大而懈怠最后放弃了大学,怕他以后要走的路太艰难,尤其是在工作方面。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一年多过去了,他已经在四川的一所大学度过了大一的时光,读的是会计专业,他自称“比较适合我的身体状况”。2008年的地震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突然的变化,包括永远的残疾。但是有些东西一直都没变,比如他开朗的个性和对篮球的热爱。今年他参加了某时尚杂志的封面明星选拔赛,获得了成都赛区的人气王称号。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和阳光,对这个社会充满期待。我也期待这个社会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能让他何时何地都获得尊重和平等的待遇,能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去美国看一场现场的nba球赛。“你还在坚持打篮球吗?”我问他。“当然在啊!那是我的最爱,我会一直打下去!”他坚定地说。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