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笔者翻阅程映虹先生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知秘鲁有一个“光辉道路”——毛泽东思想“南美版”,折腾出很大动静,成千上万人逝去。毛泽东晚年惦记着“世界革命”,原来毛泽东思想不仅遍布神州大地,波及东南亚、东西欧,还远渡重洋,远惠南美。
历史渊源
“光辉道路”(shining path)乃秘鲁共产党激进派别。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生于1934年),巨商私生子,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着迷激进思想,崇拜斯大林、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就朝拜心中圣地——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在那黎明诞生之处》。毕业后,成为哲学教授,不久蜚声校园。学生对他的滔滔口才佩服不已,呼为“香波”,意为沾上一点,大脑就会被“洗得清澈透明”,并持续散发“余香”。古兹曼的“暴力哲学”,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古兹曼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裂,世界各国共产党重新站队,许多国家共产党分裂,“光辉道路”最初乃秘鲁共产党“红旗”支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古兹曼成为秘共亲华派代表,受到中共关注。1965年,古巴共产党站稳脚跟后,开始向拉美输出革命,秘共亲华派又分裂出亲古派。此时,古巴经济只能依靠苏联东欧,只有这些共产国家进口古巴农产品,卡斯特罗必须紧跟苏联。于是,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开骂毛泽东。如此这般,秘共亲华派与亲古派没有妥协余地。
1966~1968年,古兹曼赴华,接受中联部培训,学习游击战,并于1966年秋在天安门下遥见“红太阳”毛泽东。他深深接受了中国教官的叮嘱:“只要思想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回国后,古兹曼以哲学教授头衔、从中国取回真经,一跃成为秘共“红太阳”——理论大师 指路明灯。古兹曼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要走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道路——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他跟着中共批评古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信徒们也开始称呼他为安第斯山的“红太阳”,喊出“冈扎洛主席万岁!”(“冈扎洛”是古兹曼党内用名)。
1970年,古兹曼依托国立华曼嘎大学,将秘共触须伸向秘鲁各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及外围组织。1973~1975年,“光辉道路”掌控秘鲁部分高校学生会,实质性影响秘鲁知识青年。
“光辉道路”组织严密,入伙程序复杂。每个申请者必须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积极参与小组聚会,探讨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再经长期考察,完成各项任务,证明忠诚与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核心小组,成为“战士”。
古兹曼搬用延安经验,也搞“整风”,要求干部学文件、统一思想、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指说1930年后直到他之前的秘鲁共产党,都犯了倾向性错误。经反复运动,他将“冈扎洛思想”深深植入其信徒内心。
1980年前,古兹曼多次被捕,每次都由“光辉道路”聘请律师雄辩获释。“资产阶级”给了他相当的政治自由,而他仍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报以革命的暴力。
暴力革命
1970年代末,秘鲁军政府还政文官,全国筹备大选,多数左派积极准备参选,唯“光辉道路”感觉大难临头。该组织中一些老战士受“和平过渡”思潮影响(组织内称“腐蚀”),质疑“人民战争”与暴力途径的合理性,古兹曼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因为,接受“和平竞选”,等于自动交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否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精髓。
“光辉道路”拒绝参选,开始行动。古兹曼鼓动追随者:
我们虽然是少数,但最后胜利一定在我们这一边!
首战袭击一处乡村投票站,砸毁票箱、烧毁选票。“光辉道路”自称代表印第安农民的利益,号召推翻秘鲁军政府,要求按他们的“主义”治理秘鲁。最初,活动范围在山区——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经济落后、社会组织真空地带点燃星星之火。“光辉道路”从仇富的贫穷农民那里找到支持者,乡下人为他们提供食宿、通风报信,一些青年农民还加入组织。作为“投名状”,新成员会被安排杀死一名警察或官吏(甚至贫民),这是断其后路,使其与组织共存亡。不过,“光辉道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很难打开局面,鲜有信众,未能渗入秘鲁全国性的各种工会,未能代表最想代表的工人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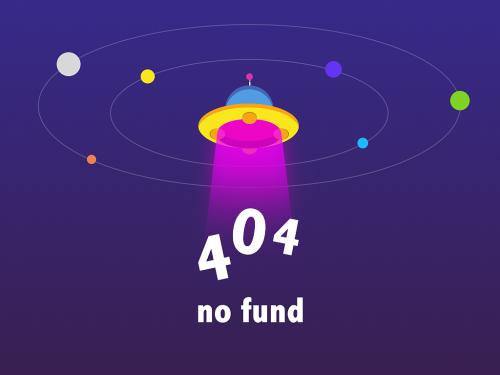
“光辉道路”的成员
“光辉道路”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以筹集经费;他们还砍掉选民食指(选票上须留食指指纹)。暗杀、袭击警所、破坏选举站……在大街小巷散发“人民战争”传单。“光辉道路”成为秘鲁城乡谈虎色变的组织。
1980年底,首都利马大街吊出几条血淋淋的死狗,上贴一纸条,纸条上写有:teng hsiao-p'ing。中国使馆亦遭炸弹袭击。因中国文革后启动改革开放,绝对“毛粉”的古兹曼感觉犹晴天霹雳,认为国际共运继赫鲁晓夫之后遭遇又一次“修正主义灾难”。古兹曼认为像文革这样的“继续革命”,必须制度化常态化,才能保证革命“永不变色”。他与柬共布尔布特一样,都认为毛的文革不彻底,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才使中国“红旗落地”。
“光辉道路”祭出马列毛之后的“第四把刀子”——“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认为世界革命的火炬,历史性地传递到他手里,自己就是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
“光辉道路”逻辑混沌,东鳞西爪,甚至有时指黑为白。“光辉道路”一位26岁女党员被捕后,在狱中仍认为“暴力”与“站在人民一边”乃同义词。至于把拥有一辆自行车者视为富人而对其惩罚,她回答:“任何战争都有代价,每天六万儿童挣扎在饥饿中,难道不是代价吗?”这位坚定的“光辉道路”女性还将中国1989年的社会运动解读为反修运动——中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反对修正主义。“光辉道路”虽以“思想解放”为号召,却对领袖“冈扎洛主席”顶礼膜拜。“光辉道路”成员除了同志,一般没有其他朋友,婚恋对象多半也是自己人即同志。
古兹曼一度想联络“亚得里亚海岸的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但人家更属意秘共“红旗”派,未理睬他。因此,“光辉道路”判认阿尔巴尼亚也是沦落的修正主义。
笔者翻阅程映虹先生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知秘鲁有一个“光辉道路”——毛泽东思想“南美版”,折腾出很大动静,成千上万人逝去。毛泽东晚年惦记着“世界革命”,原来毛泽东思想不仅遍布神州大地,波及东南亚、东西欧,还远渡重洋,远惠南美。
历史渊源
“光辉道路”(shining path)乃秘鲁共产党激进派别。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生于1934年),巨商私生子,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着迷激进思想,崇拜斯大林、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就朝拜心中圣地——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在那黎明诞生之处》。毕业后,成为哲学教授,不久蜚声校园。学生对他的滔滔口才佩服不已,呼为“香波”,意为沾上一点,大脑就会被“洗得清澈透明”,并持续散发“余香”。古兹曼的“暴力哲学”,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古兹曼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裂,世界各国共产党重新站队,许多国家共产党分裂,“光辉道路”最初乃秘鲁共产党“红旗”支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古兹曼成为秘共亲华派代表,受到中共关注。1965年,古巴共产党站稳脚跟后,开始向拉美输出革命,秘共亲华派又分裂出亲古派。此时,古巴经济只能依靠苏联东欧,只有这些共产国家进口古巴农产品,卡斯特罗必须紧跟苏联。于是,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开骂毛泽东。如此这般,秘共亲华派与亲古派没有妥协余地。
1966~1968年,古兹曼赴华,接受中联部培训,学习游击战,并于1966年秋在天安门下遥见“红太阳”毛泽东。他深深接受了中国教官的叮嘱:“只要思想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回国后,古兹曼以哲学教授头衔、从中国取回真经,一跃成为秘共“红太阳”——理论大师 指路明灯。古兹曼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要走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道路——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他跟着中共批评古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信徒们也开始称呼他为安第斯山的“红太阳”,喊出“冈扎洛主席万岁!”(“冈扎洛”是古兹曼党内用名)。
1970年,古兹曼依托国立华曼嘎大学,将秘共触须伸向秘鲁各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及外围组织。1973~1975年,“光辉道路”掌控秘鲁部分高校学生会,实质性影响秘鲁知识青年。
“光辉道路”组织严密,入伙程序复杂。每个申请者必须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积极参与小组聚会,探讨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再经长期考察,完成各项任务,证明忠诚与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核心小组,成为“战士”。
古兹曼搬用延安经验,也搞“整风”,要求干部学文件、统一思想、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指说1930年后直到他之前的秘鲁共产党,都犯了倾向性错误。经反复运动,他将“冈扎洛思想”深深植入其信徒内心。
1980年前,古兹曼多次被捕,每次都由“光辉道路”聘请律师雄辩获释。“资产阶级”给了他相当的政治自由,而他仍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报以革命的暴力。
暴力革命
1970年代末,秘鲁军政府还政文官,全国筹备大选,多数左派积极准备参选,唯“光辉道路”感觉大难临头。该组织中一些老战士受“和平过渡”思潮影响(组织内称“腐蚀”),质疑“人民战争”与暴力途径的合理性,古兹曼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因为,接受“和平竞选”,等于自动交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否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精髓。
“光辉道路”拒绝参选,开始行动。古兹曼鼓动追随者:
我们虽然是少数,但最后胜利一定在我们这一边!
首战袭击一处乡村投票站,砸毁票箱、烧毁选票。“光辉道路”自称代表印第安农民的利益,号召推翻秘鲁军政府,要求按他们的“主义”治理秘鲁。最初,活动范围在山区——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经济落后、社会组织真空地带点燃星星之火。“光辉道路”从仇富的贫穷农民那里找到支持者,乡下人为他们提供食宿、通风报信,一些青年农民还加入组织。作为“投名状”,新成员会被安排杀死一名警察或官吏(甚至贫民),这是断其后路,使其与组织共存亡。不过,“光辉道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很难打开局面,鲜有信众,未能渗入秘鲁全国性的各种工会,未能代表最想代表的工人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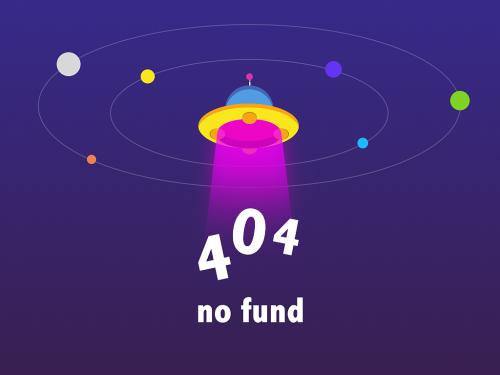
“光辉道路”的成员
“光辉道路”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以筹集经费;他们还砍掉选民食指(选票上须留食指指纹)。暗杀、袭击警所、破坏选举站……在大街小巷散发“人民战争”传单。“光辉道路”成为秘鲁城乡谈虎色变的组织。
1980年底,首都利马大街吊出几条血淋淋的死狗,上贴一纸条,纸条上写有:teng hsiao-p'ing。中国使馆亦遭炸弹袭击。因中国文革后启动改革开放,绝对“毛粉”的古兹曼感觉犹晴天霹雳,认为国际共运继赫鲁晓夫之后遭遇又一次“修正主义灾难”。古兹曼认为像文革这样的“继续革命”,必须制度化常态化,才能保证革命“永不变色”。他与柬共布尔布特一样,都认为毛的文革不彻底,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才使中国“红旗落地”。
“光辉道路”祭出马列毛之后的“第四把刀子”——“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认为世界革命的火炬,历史性地传递到他手里,自己就是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
“光辉道路”逻辑混沌,东鳞西爪,甚至有时指黑为白。“光辉道路”一位26岁女党员被捕后,在狱中仍认为“暴力”与“站在人民一边”乃同义词。至于把拥有一辆自行车者视为富人而对其惩罚,她回答:“任何战争都有代价,每天六万儿童挣扎在饥饿中,难道不是代价吗?”这位坚定的“光辉道路”女性还将中国1989年的社会运动解读为反修运动——中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反对修正主义。“光辉道路”虽以“思想解放”为号召,却对领袖“冈扎洛主席”顶礼膜拜。“光辉道路”成员除了同志,一般没有其他朋友,婚恋对象多半也是自己人即同志。
古兹曼一度想联络“亚得里亚海岸的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但人家更属意秘共“红旗”派,未理睬他。因此,“光辉道路”判认阿尔巴尼亚也是沦落的修正主义。
行为点滴
为表示自己的存在与力量,“光辉道路”不时搞一些革命活动——
1980年,捣毁阿亚库乔区一投票站。
1982年3月,打开阿亚库乔区监狱,放走200多名囚犯。
1983年,袭击卢卡纳玛律卡村,杀害69名村民(包括23名孩子)。
1986年8月,炸弹袭击经济财政部、能源矿业部、劳动部。
1990年6月,袭击黄塔村,杀20名村民(包括妇女儿童),焚烧40所农居。
1992年2月11日,在利马同时制造36起爆炸,炸死两名美使馆岗警。
1992年6月5日凌晨,引爆载有一辆600公斤炸药的汽车,炸毁一家利马电视台,死伤20余人。
1992年7月16日利马繁华商业区,引爆两辆装有300公斤炸药的汽车,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座建筑受损。
2001年12月,袭击美国大使馆(未遂)。
2003年6月9日凌晨,袭击安第斯山区一处天然气管道工地,绑架60名人质,包括3名警察、7名外国人,抢走施工炸药。
2003年7月11日,在山区丛林伏击一支30名海军陆战队的巡逻队,打死7人、打伤10人。
1992年,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秘鲁藤森政府在清剿中逮捕了古兹曼,“光辉道路”活动开始减少。次年,古兹曼在狱中与政府签署《和平协定》,但余部仍有零星暴力袭击活动。美国将“光辉道路”列为恐怖组织。2006年10月13日,古兹曼被判终身监禁。继任者是奥斯卡•拉米雷斯•杜兰德(óscar ramírez durand),1999年被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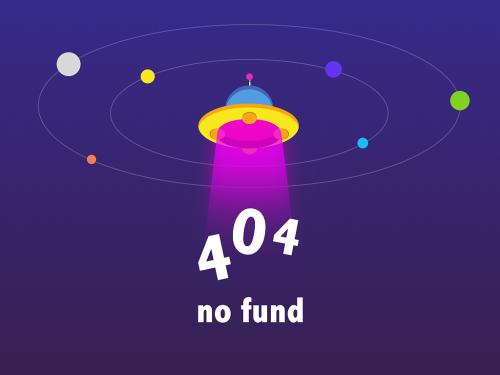
秘鲁政府军解救出“光辉道路”劫持的人质
1980~1992年,“光辉道路”使秘鲁付出成千上万的生命,许多社会设施被毁,农民纷纷逃进城市。连安第斯山区农民也对“光辉道路”无节制的袭击渐生厌倦,更对暴力胁迫深感恐惧,许多地区的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自卫。于是,“光辉道路”更不分对象地进攻,全社会都成为他们的报复对象,原本作为争取对象的贫穷农民,也成了“革命对象”。自然,“光辉道路”也因此走上越来越窄的歧路——失去各社会群体的支持后,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失去“光辉”。
经验教训
在现阶段,暴力革命虽失去大规模发动与成功的时代条件,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与极度贫穷仍是各式暴力革命的温床。每个时代会有这样那样的“理想者”——希望通过革命改变社会改变命运。古兹曼的信徒,多半出自贫苦家庭的大学生(其时秘鲁大学免费)。可见,革命思想是首先在青年学生中着床。思想不仅引导价值方向,也深刻引领行动。
红色思潮及古兹曼吸引信徒的几个特征:
1.宏大壮阔但缥缈混沌的哲学思辨,以“宇宙终极真理”论证偏激思潮的“科学性”,很能迷惑线性思维的知识青年。
2.革命与艺术结合的浪漫激情,点燃信徒改变社会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红色狂热。
3.暴力行动对红色青年甚具诱惑,他们不耐烦于长期艰难的宣传鼓动,“立即行动”能使他们看到革命的“效果”。
4.“光辉道路”领导层与其他国家激进共产主义党派类似,由狂热的红色知识分子组成。
5.多数成员政治倾向粗糙且情绪化,并将政治责任统统交给领袖。
6.偏激狭仄,唯我独革。“光辉道路”认为:古巴的卡斯特罗搞的亦非一场真正革命,“一小撮资产阶级官僚控制着古巴”;阿尔巴尼亚也由修正主义把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虽有一些正确思想,但没有一个正确的党。只有“光辉道路”才是世界革命的真正代表,只有安第山的“红太阳”——冈扎洛主席,才是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
7.谴责别人不劳而获,而自己不仅不劳,还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
8.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同时也获得杀人资格,以摆脱道德顾忌——自己的生命可付出,他人的生命也可放弃。
9.具备宗教圣战特征: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版,第231~252、258页)。
10.“光辉道路”也信奉切•格瓦拉的“暴力催生论”——革命条件可以由少数战士用暴力去创造去营建,古巴革命就是在不具备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革命者的主动性与革命热情所促成。但这种“暴力催生论”被“光辉道路”再次证谬。
结语
南美版暴力革命组织“光辉道路”的轨迹,呈现了暴力革命中携带的谬论。现代文明条件下,真理毋须佩剑守护“诞生”,也不能依赖暴力证明“正确”。因为,很多真理凭常识亦可识别。即便深奥一些的真理,也应等待被认知,不应强迫他人接受。
相关简介:裴毅然,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所访问学者。原题《秘鲁“光辉道路”活动略议》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