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东非:你如何解决一个像厄立特里亚那样的问题?
1.这一问题是如何显现出来的?
问题出在厄立特里亚——还有一大批国家喜欢它。从2013年到2014年,在欧盟、瑞士和挪威的厄立特里亚人避难申请者数量翻了一番,达到47000多人。但这并不是这些难民的全部数量(在移民危机期间,2015年,厄立特里亚人的数量一直保持不变,而叙利亚人的申请数量增加了500%,阿富汗人的增加了300%,伊拉克人的增加了200%,阿尔巴尼亚人的申请数量增加了一倍)。厄立特里亚人的申请(10%是举目无亲的儿童)也没有成问题的苛求性。更确切地说,欧盟认为它影响不了阿斯马拉的政权(阿斯马拉为厄立特里亚首都,代指厄立特里亚政府——译者注),也影响不了移民流的根源问题。
厄立特里亚自2000年与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威权和高度军事化政权的控制之下,该政权仍以总统阿费沃基(afwerki)为中心。被形容为一个“围城国家”(siege state),或者被简单地称为“非洲之角的朝鲜”,厄立特里亚政府有偏执、内向的名声。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权,因与邻国的边界争端而陷入困境,并被联合国安理会应非洲联盟请求而实施的经济制裁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内经济来打造公众支持,它就会从孤立之中和感觉外部世界对它怀有敌意之中汲取能量。
但是,尽管在战争之后有对政治自由的镇压,厄立特里亚难民并不总是担忧他们的生活或害怕受到迫害。丹麦红十字会一项有争议的分析表明,他们经常逃避失业、逃避延长服兵役的前景。然而,如果欧盟当局给93%的申请者提供庇护,那是因为遣返他们将违反“不驱回”(non-refoulement)原则:这些人是逃离那个国家的脱逃者。厄立特里亚认为这是一种叛国的罪行;据报道,对该罪行的惩罚是终身监禁或死刑。
对欧洲官员来说,这种特殊的移民流可以说是欧盟迄今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厄立特里亚人不是逃离像叙利亚、伊拉克或阿富汗这样的热点冲突区或失败国家;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可能会稳定和得到改革的地方。他们也不是从尼日利亚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迁出——这些国家可能会因为经济投资和外交上被点名批评而被诱导合作。相反,他们正从一个专制但尚在运行的国家中逃离,该国是欧盟在不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援助原则的情况下无法真正接近的。

到达欧洲的厄立特里亚难民
在一个似乎越来越被划分为像叙利亚这样的战区、像尼日利亚这样自信的“发展之星”和像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冻结国家的世界里,正是后者似乎为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们积聚了最多的问题。
2.欧盟最初的诊断如何?
在2015年的早些时候,似乎源源不断的叙利亚人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对“永久流动”的担忧——关于非正规移民的永久流入。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让这些担忧之心放了下来,并让欧盟有信心更有力地应对移民的安全和经济驱动因素。但是现在,当注意力迅速回到地中海中部时,旧的担忧再次浮现。
就厄立特里亚而言,欧盟发现自己打交道的是一个既不会崩溃也不会合作的政权,这个政权只会使自己永久化,不断向欧洲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欧洲不得不允许这些人留下来。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每个月有5000人从厄立特里亚逃离。如果小小的厄立特里亚能产生这种看似不可阻挡的人流,那么其他不合时宜的政权——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南奥塞梯、赤道几内亚、缅甸、冈比亚、白罗斯(belarus)——又如何呢?由于叙利亚、利比亚或伊拉克的中央政府未能在国家领土上彰显其权威而在这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分离地区又如何呢?
这引发了根本性的问题——关于欧盟是否会继续致力于国际难民制度的问题。像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国家是新老问题的有力组合——它们将现代的互联互通与冷战式的孤立相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政府面临大规模的移民潮,并怀疑它们是否能坚持它们对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承诺。然而,它们选择了这样做,因为它们相信全球化和现代的互联互通将使它们可在源头上进行干预,并解决移民的驱动因素。厄立特里亚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风格政权的例子,它不受外界影响,但它的国民可以利用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来进行远距离迁移。
的确,从国内出发的厄立特里亚人比离开更开放社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花更长的时间到达欧洲。尼日利亚人或科特迪瓦人能够在他们计划自己的旅程之前,很早把钱转移到萨赫勒地区的蛇头身上,或者很早联系上在欧洲的侨民。但厄立特里亚人也一样,他们是在越来越多地建立自己的走私网络。厄立特里亚的不法分子在利比亚确立了自己的永久存在,在那里他们管理着一个蛇头网络,该网络恰恰往回延伸到了厄立特里亚的边境部门。
欧盟一些国家的官员认为,这种情况需要冷静思考:如果欧洲要保持其境内难民接待的承诺,这就为境外一些基本的权力政治提供了正当性。他们坦率地谈到,欧盟有必要在东非起自厄立特里亚的过境路线上采取一项缓冲政策。
3.欧盟最初的政策回应如何?
欧盟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更下游的大的地区势力,以遏制人口流动。如果欧盟不能在厄立特里亚自身内部阻止移民流,那么下一个最佳选择就是在苏丹、埃及的边境合作和警察合作,以打破偷渡网络。
2013年,欧盟已经开始与从厄立特里亚到利比亚的过境路线上包括埃及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甚至突尼斯(突尼斯被包括是因为其现在正为欧盟驻利比亚边境援助特派团提供容身之地)在内的一连串国家进行谈判。这一举措将成为“喀土穆进程”(khartoum process),呼应了欧盟与西非国家的长期对话。但是,鉴于“拉巴特进程”(rabat process)覆盖与西非在欧侨民的关系、汇款便利化等积极议题,“喀土穆进程”专注于狭窄的执法问题:在西非,对于和像尼日利亚、科特迪瓦这样的“发展之星”一起来缓解移民的根源以及快速减轻像尼日尔、马里这样的过境国的压力,欧盟持乐观态度;但是,在非洲之角,欧盟充其量只能希望过境国来压制移民流。
2014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两个对话的区别得到了体现。通过与西非的交换条件,“拉巴特进程”得到了新动力:如果西非国家改进对移民的控制,欧盟同意“支持移民的发展潜力”。这使“拉巴特进程”与欧盟已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采取的移民合作模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盟将增加合法移民的机会和侨汇流动,以便在非正规移民问题上获得合作。与此同时,“喀土穆进程”只得到了一个中心环节:执法。欧盟指望从其发展预算和针对在东非执法的欧洲内部安全基金(european internal security fund)中释放资金。
唯一的光明面是欧盟不必利用其庞大的开支权力来哄骗东非路线上的国家来合作——这一狭隘的焦点实际上是该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在2015年担任“喀土穆进程”主席的埃及)所要求的。
早在2012年,甚至在突尼斯、摩洛哥参加了欧盟提出的关于人口流动和安全的对话之时,埃及已经对欧盟关于这一对话的提议表示不屑——这一对话是成熟的人口流动伙伴关系的先导,将结合作为对开罗控制边境的回报的埃及人移民到欧洲的机会。埃及似乎不希望使自己依赖欧盟。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地区领导,并维持着一个连接从沙特阿拉伯到美国的主要外部大国的网络。绝大多数来自埃及的移民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不是欧洲。至于高技能移民,他们会前往美国等目的地,而那些想要前往欧洲的埃及专业人士,在现有的蓝卡制度下很容易获得资格。因此,开罗提出了自己与欧盟合作的方案:不附加条件的欧洲资金。
4.专家意见如何?
学者们紧张地关注着欧盟与开罗的接洽,他们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欧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或者是在源头上与专制的厄立特里亚进行合作,或者是在下游的埃及、苏丹创建缓冲区。仅仅因为欧盟不能与厄立特里亚合作,并不能证明其他地方的压制措施是正当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自行解决——来自厄立特里亚(人口只有500万)的人口流动将会自动枯竭。学者们认为,过去十年里每个涌向欧盟的大的移民潮都是这样的故事——首先是非正规移民的持续渐增,然后是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每一次,潜在移民的存量都自我耗尽,不论过境国采取的反制政策如何。
过去,学者们对欧盟与过境国、源头国的交易不太担心,因为这通常涉及欧盟为合法移民和侨汇提供新的渠道——比如在西非开始采用的人口流动伙伴关系等政策。但欧盟对起自厄立特里亚的过境路线的处理似乎标志着方向的根本性改变。在“喀土穆进程”下,欧盟不仅是推进生硬的执法政策,而且使自己依赖于缓冲国,并面临开罗方面或喀土穆方面的勒索——它们可能正声称会阻止厄立特里亚人的流动,而厄立特里亚人的流动[实际上]早已缩减。学者们说,如果欧盟以这种方式与苏丹、埃及接洽,将对整个地区造成永久、不必要的损害。
的确,欧盟没有直接向苏丹政府提供任何资金用于边境控制。它仅仅派出了一个实况调查团,以评估向苏丹边境部门提供设备是否可行,以及为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等国际机构在该地区的工作提供资金是否可行。但有人担心,即便如此,也可能使欧盟受到苏丹政客的讹诈。苏丹迫切希望欧盟设立边境训练特派团,显然将其视为获得国际承认的手段,并将其作为取消国际制裁的理由。苏丹政府也因利用援助机构而闻名。它将呼吁欧盟做出支持,然后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将采用其惯常的伎俩,敲诈那些随后到达的非政府组织。
这个教训很简单。多年来,欧盟一直被赋予令人敬畏的权力来帮助管理国际边境,而这些权力不应该被用于遏制。专家们说,苏丹、摩洛哥和约旦都在利用移民危机来巩固其有争议的边界,而欧盟仅仅是为了阻止人的流动而向它们表示尊重。欧盟未能参与到像也门这样的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利雅得实际上阻止了人们逃离自己在那里展开的轰炸行动。而且,当欧盟成员国们接受并承认难民时,专家们认为,它们经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破坏源头国,而不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人道主义义务感。
5.欧盟是如何容纳专家意见的?
欧盟适时地开始寻求更为积极的第三种选择,进一步深入过境路线:与非洲之角本身的“发展之星”埃塞俄比亚合作。这是欧盟尝试从黎凡特移植其新的发展-人道主义方法,并尝试在埃塞俄比亚为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阻止人们从非洲之角中迁出,不过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的确,欧盟从一开始没有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这种积极的关注。它是通过迂回的途径实现的,而且只有在欧盟耗尽了与苏丹、埃及合作的选项之后,以及耗尽了达成一件遣返非正规在欧洲生活的埃塞俄比亚人协议的选项之后。欧盟最初在埃塞俄比亚的重点合乎逻辑地是遣返和边境控制:埃塞俄比亚人口众多,是1亿国民的家园,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潜在外流移民数量可能会使来自厄立特里亚的潜在外流移民数量相形见绌。欧盟成员国提出了为埃塞俄比亚人提供更多合法移民选择和学习场所的建议。但在这个问题上,亚的斯亚贝巴内部意见分歧,谈判陷入僵局。
事后看来,欧盟实际上认为,它最终以这种创造就业岗位计划的形式获得了更好的选择。大多数非正规的埃塞俄比亚移民正朝海湾(“海湾”指波斯湾——译者注)方向迁移。而且,欧盟各国政府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乐意为埃塞俄比亚学生提供优惠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scheme)位置,正是因为他们有自愿再次离开的名声。最终,难民收容协议比遣返协议对欧盟更有价值。
6.现状核实如何?
然而,随着欧盟更好地理解了埃塞俄比亚的动机,它开始意识到,在那里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并不是第一眼看上去那么容易。有人怀疑,在谈判者的经典“两级博弈”中,埃塞俄比亚精明的总理充分利用了国内对他回旋余地的约束,以迫使欧盟做出让步。
在有关遣返协议的初步谈判中,埃塞俄比亚总理以其外交背景发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如果这是与欧洲确保关系的一种方式,他就不只是准备帮助欧盟遣返移民。但是,令他明显意外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安全部门破坏了他的形象,它们说它们害怕罪犯、恐怖分子和其他可能谎称拥有埃塞俄比亚国籍的人从欧洲回国。安全部门甚至拒绝与欧盟外交官们交谈,总理只能表示他的尴尬。作为善意的表达,他表示愿意在其他有争议的领域做出让步。他的政府将改进现有的方案,使厄立特里亚人离开难民营、融入劳动力市场。
但是,现在布鲁塞尔有人担心,埃塞俄比亚的同意太容易而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做出“让步”:外交官们推测,埃塞俄比亚正在利用移民危机,在方式上与苏丹、埃及等其他过境国没有什么不同。亚的斯亚贝巴已经获得欧盟的支持,建造两个工业园区,为当地居民和难民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但在布鲁塞尔,有人担心,埃塞俄比亚总理没有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商业论证来证明该计划将为难民创造工作机会。埃塞俄比亚政府似乎是在利用移民危机达到国内目的,将其作为一种手段——通过给其支持者创造就业计划来巩固政府。埃塞俄比亚显然也希望将欧盟拉入该地区的权力政治。它的希望是在其与苏丹、埃及的争端中改变态势,当然也要加深国际上对厄立特里亚政权的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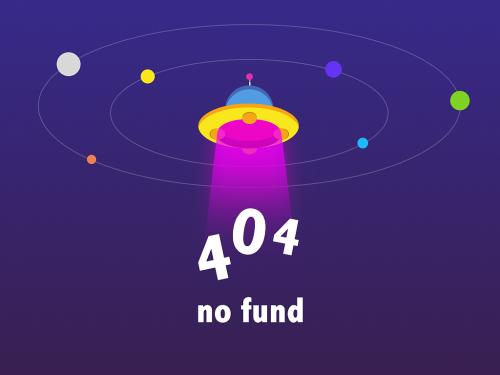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一个工业园区内的工厂
此外,亚的斯亚贝巴还希望加强其在附近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海湾国家一直威胁说,如果亚的斯亚贝巴方面在卡塔尔、也门的争端中站错队,就驱逐埃塞俄比亚移民。讽刺的是,如果亚的斯亚贝巴和布鲁塞尔当初选择让埃塞俄比亚人更多地去欧洲,那可能会更好地满足它们的利益。即使程度小,那也会减轻埃塞俄比亚对海湾市场的依赖。同时,那也可能迫使埃塞俄比亚和欧盟解决移民率仍然很低的一些原因,以及解决许多埃塞俄比亚侨民确实是返回家园的一些原因:埃塞俄比亚的土地权利是声名狼藉地糟糕,这意味着,因为担心失去财产,很少有人会长期移居。亚的斯亚贝巴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进展缓慢,因为攫取土地使其能够承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有助于使其成为“发展之星”。
现在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局势恶化了,边境和移民问题只会加剧竞争。通过提醒阿斯马拉说它们收容了大量的厄立特里亚工人并随时可以驱逐他们,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将厄立特里亚拉入它们与卡塔尔的争端中。卡塔尔对厄立特里亚与沙特阿拉伯结盟的反应是,从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之间有争议的边界撤走了自己的400名观察员。在卡塔尔争端期间一直试图保持中立的索马里,激怒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它们威胁要停止资助邦特兰海岸警卫队(邦特兰是索马里的一个自治区域——译者注)。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手忙脚乱:亚的斯亚贝巴与沙特阿拉伯结盟,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国民被从穆斯林重地逐回,将打乱自己微妙的宗教平衡,并将抬高它17%的失业率,而该国的创造就业岗位计划易于偏爱政府的支持者。
7.真正的问题原来是什么?
出于原则原因,欧盟拒绝与厄立特里亚就移民的根源问题进行合作。但实际上,这相当于地缘政治的遏制:欧盟加深了厄立特里亚的国际孤立,并在更下游形成了缓冲国。这只会加剧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如果欧盟不改变它的做法,它就有可能陷入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这样的移民过境国之间的竞争。毕竟,欧盟依赖这些国家来阻止人的流动,而且它在那里缺乏其平常的积极手段:这些国家对进入欧洲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欧洲的发展领域支出也附带了太多的改革条件。因此,欧盟是容易受到像苏丹这样的国家利用,苏丹提供边境合作,以换取欧盟在更多至关重要问题(例如,尼罗河水问题)上提供支持:从厄立特里亚前往欧洲的移民流沿着其他物体流动的路径走——诸如水和货物的路径。像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老战略对手并不一定对这些物体流动的可持续管理感兴趣:它们往往只是想打败另一方。
欧盟并不是唯一一个作为单一问题参与者的外部力量。美国在非洲之角有一个单一的重点,即反恐,包括对厄立特里亚实施制裁——因为厄立特里亚支持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al-shabaab)。相比之下,来自中国驻吉布提基地的中国人则在宣传一种“丝绸之路”叙事,该叙事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人口流动管理愿景;而这似乎引起了非洲之角积极的兴趣。欧洲官员现在认识到,移民流的区域管理也可能释放出同样积极的动力。毕竟,人的流动实际上是非洲之角的国家都关心的重要事情,即使赴欧洲移民的具体问题不属于其核心利益。甚至苏丹也在参与,而且只要区域移民问题摊开亮明,苏丹就不再阻碍人权对话。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更为积极的区域移民合作,很明显,欧盟最终将不得不在源头、在厄立特里亚采取行动:这是布鲁塞尔能够避免被拖入与苏丹这类地方进行“零和博弈”式缓冲区交易的唯一途径。当厄立特里亚于2015年年末来到谈判桌前时,它表示已准备好在更深层次的发展领域关系上进行合作。2016年1月,欧盟初步承诺,截至2020年,把2亿欧元花在厄立特里亚,专注于能源基础设施、财务管理和实施联合国领导的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出的建议。2017年年初,欧盟承诺向该国的创造就业岗位计划提供1300万欧元。欧洲方面不抱任何幻想,事实是过去25年与厄立特里亚接触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望告终,但移民问题使接触好于遏制。
8.欧盟最终进行了何种调整?
2016年年中,管理“喀土穆进程”的民政事务官员们和外交官们决定尝试将他们的工作与更先进的“拉巴特进程”更好地相结合,非洲之角的官员们开始参加向西非学习的会议。这一举动让欧盟或多或少地直接比较了这两个进程中的政治动力,很明显,这两个进程都没有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在西非路线上,欧盟可能过于乐观地与源头国就移民的根源问题进行合作,并对与脆弱的过境国合作的范围过于悲观。在非洲之角,它太喜欢依赖像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过境国,因为在厄立特里亚,它没有看到从源头来处理根源问题的真正机会。
至于在这两条路线上与过境国的合作,欧盟在西非与脆弱的尼日尔合作的体验是非常积极的,不像与埃及、苏丹那样更强大的东非地区大国的合作。这是因为,在尼日尔,发展领域的合作作为对其困境的一种反应是真正有意义的。尼日尔是欧盟可以引入有效的创造就业岗位计划的地方:在阿加德兹(agadez)这样的地区,小规模的就业创造计划能够为那些为移民和偷渡业务提供服务的公民创造“替代生计”。这些措施并没有在东非的过境国真正起作用,在那里它主要意味着为腐败的边防人员创造“替代生计”。在像尼日利亚这样的移民源头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在尼日利亚,欧盟从来没有希望创造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来劝阻年轻人的移民。
在这两条路线的源头合作的比较中,非洲之角的情况并不像最初担心的那样惨淡。变得明朗的是,与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国家合作毕竟是可能的。在阿斯马拉,欧洲官员们发现,一个家长式作风的政权正烦恼于人口的流失。也有报道称,该政府确实允许国民从欧洲回国,即使只是回国旅游观光,这表明其对外部经济来源的依赖。诚然,厄立特里亚官员仍然对欧洲的干涉心存重重疑虑,但在该国获得独立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们表现出对改善国家状况的兴趣。这与快速发展的西非移民源头国的情况相比是有利的:根据一名欧盟成员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是防贪污的,从中得不到个人私利”,西非移民源头国的政治精英会对欧洲的发展领域支出表现出有限的兴趣。
9.长期导向是什么?
欧盟最近开始接触政治孤立的国家,不仅面向欧盟南边比如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地方,而且面向东边家门口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
历史上,欧盟与六个正式组成“东部伙伴关系”的国家中的五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有着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已经准备好阻止移民流在前往欧盟的途中过境,通常是为了换取它们自己的国民进入欧盟的特权。问题恰在于它们自己的内部边界问题——它们的争议边界和分离地区。这五个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有这样的问题,而欧盟在其多边睦邻政策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它开始处理一个边界问题,它将需要处理所有边界问题。此外,“东部伙伴关系”中唯一没有此类问题的国家是白罗斯——这是最孤立的国家,也是欧盟历来对其采取最大程度不干涉政策的国家。
在2014年前后,欧盟暂时决定将边境合作纳入“东部伙伴关系”的多边轨道,尽管不是通过正面解决边界争议。相反,它试图在一个相对没有争议的事务(它们在黑海和里海共享的海上边界)上鼓励合作。几乎在这一举措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黑海边界突然有争议。但这些事件也使白罗斯与俄罗斯疏远,并将其推入欧盟一边。白罗斯是六国中唯一没有领土问题的国家,它现在向布鲁塞尔表达了它的担忧,即它与俄罗斯的疏远对自己的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在那之前,白罗斯自愿提供了连接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地方之间的部分陆桥;现在有人担心莫斯科方面可能会攫取其部分领土)。
就像在厄立特里亚,欧盟也发现了意外的合作机会。白罗斯认为,它可以利用“东部伙伴关系”多边轨道来传播自己的移民和边境管理模式。它想在穿越其领土的越南移民流问题上进行合作。明斯克方面甚至热衷于和欧盟谈判一种人口流动伙伴关系,尽管这将使其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及面临社会层面的人员往来。由于欧盟很好地对待移民,白罗斯渴望其公民获得欧盟的准入权。当它的国民到海湾国家工作时,明斯克发现他们在那里的糟糕待遇迫使它进行干预。换句话说,欧盟,一个试图设定标准的先进的后国家机构,是白罗斯不干涉风格的最大保证者。
此外,就像在非洲之角,欧盟也发现,它在东欧和亚洲的移民外交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的手段。向东,欧盟是两个移民对话的当事方——“布达佩斯进程”和“海牙进程”。俄罗斯官员们表示,他们认为这些对话是至关重要的论坛;与其说是为了讨论移民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为,欧盟将维持这两个进程,即使在它关闭与莫斯科的其他沟通渠道时。换句话说,移民对话是莫斯科向布鲁塞尔提出广泛政治议题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这也使欧盟可以阻止俄罗斯把移民问题“武器化”,即防止它利用东欧国家对其劳动力市场的依赖作为汇款的来源。
东非:你如何解决一个像厄立特里亚那样的问题?
1.这一问题是如何显现出来的?
问题出在厄立特里亚——还有一大批国家喜欢它。从2013年到2014年,在欧盟、瑞士和挪威的厄立特里亚人避难申请者数量翻了一番,达到47000多人。但这并不是这些难民的全部数量(在移民危机期间,2015年,厄立特里亚人的数量一直保持不变,而叙利亚人的申请数量增加了500%,阿富汗人的增加了300%,伊拉克人的增加了200%,阿尔巴尼亚人的申请数量增加了一倍)。厄立特里亚人的申请(10%是举目无亲的儿童)也没有成问题的苛求性。更确切地说,欧盟认为它影响不了阿斯马拉的政权(阿斯马拉为厄立特里亚首都,代指厄立特里亚政府——译者注),也影响不了移民流的根源问题。
厄立特里亚自2000年与埃塞俄比亚发生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威权和高度军事化政权的控制之下,该政权仍以总统阿费沃基(afwerki)为中心。被形容为一个“围城国家”(siege state),或者被简单地称为“非洲之角的朝鲜”,厄立特里亚政府有偏执、内向的名声。这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权,因与邻国的边界争端而陷入困境,并被联合国安理会应非洲联盟请求而实施的经济制裁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内经济来打造公众支持,它就会从孤立之中和感觉外部世界对它怀有敌意之中汲取能量。
但是,尽管在战争之后有对政治自由的镇压,厄立特里亚难民并不总是担忧他们的生活或害怕受到迫害。丹麦红十字会一项有争议的分析表明,他们经常逃避失业、逃避延长服兵役的前景。然而,如果欧盟当局给93%的申请者提供庇护,那是因为遣返他们将违反“不驱回”(non-refoulement)原则:这些人是逃离那个国家的脱逃者。厄立特里亚认为这是一种叛国的罪行;据报道,对该罪行的惩罚是终身监禁或死刑。
对欧洲官员来说,这种特殊的移民流可以说是欧盟迄今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厄立特里亚人不是逃离像叙利亚、伊拉克或阿富汗这样的热点冲突区或失败国家;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可能会稳定和得到改革的地方。他们也不是从尼日利亚等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迁出——这些国家可能会因为经济投资和外交上被点名批评而被诱导合作。相反,他们正从一个专制但尚在运行的国家中逃离,该国是欧盟在不从根本上损害发展援助原则的情况下无法真正接近的。

到达欧洲的厄立特里亚难民
在一个似乎越来越被划分为像叙利亚这样的战区、像尼日利亚这样自信的“发展之星”和像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冻结国家的世界里,正是后者似乎为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们积聚了最多的问题。
2.欧盟最初的诊断如何?
在2015年的早些时候,似乎源源不断的叙利亚人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对“永久流动”的担忧——关于非正规移民的永久流入。欧盟与土耳其达成的协议让这些担忧之心放了下来,并让欧盟有信心更有力地应对移民的安全和经济驱动因素。但是现在,当注意力迅速回到地中海中部时,旧的担忧再次浮现。
就厄立特里亚而言,欧盟发现自己打交道的是一个既不会崩溃也不会合作的政权,这个政权只会使自己永久化,不断向欧洲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欧洲不得不允许这些人留下来。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每个月有5000人从厄立特里亚逃离。如果小小的厄立特里亚能产生这种看似不可阻挡的人流,那么其他不合时宜的政权——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南奥塞梯、赤道几内亚、缅甸、冈比亚、白罗斯(belarus)——又如何呢?由于叙利亚、利比亚或伊拉克的中央政府未能在国家领土上彰显其权威而在这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分离地区又如何呢?
这引发了根本性的问题——关于欧盟是否会继续致力于国际难民制度的问题。像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国家是新老问题的有力组合——它们将现代的互联互通与冷战式的孤立相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政府面临大规模的移民潮,并怀疑它们是否能坚持它们对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承诺。然而,它们选择了这样做,因为它们相信全球化和现代的互联互通将使它们可在源头上进行干预,并解决移民的驱动因素。厄立特里亚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风格政权的例子,它不受外界影响,但它的国民可以利用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来进行远距离迁移。
的确,从国内出发的厄立特里亚人比离开更开放社会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花更长的时间到达欧洲。尼日利亚人或科特迪瓦人能够在他们计划自己的旅程之前,很早把钱转移到萨赫勒地区的蛇头身上,或者很早联系上在欧洲的侨民。但厄立特里亚人也一样,他们是在越来越多地建立自己的走私网络。厄立特里亚的不法分子在利比亚确立了自己的永久存在,在那里他们管理着一个蛇头网络,该网络恰恰往回延伸到了厄立特里亚的边境部门。
欧盟一些国家的官员认为,这种情况需要冷静思考:如果欧洲要保持其境内难民接待的承诺,这就为境外一些基本的权力政治提供了正当性。他们坦率地谈到,欧盟有必要在东非起自厄立特里亚的过境路线上采取一项缓冲政策。
3.欧盟最初的政策回应如何?
欧盟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更下游的大的地区势力,以遏制人口流动。如果欧盟不能在厄立特里亚自身内部阻止移民流,那么下一个最佳选择就是在苏丹、埃及的边境合作和警察合作,以打破偷渡网络。
2013年,欧盟已经开始与从厄立特里亚到利比亚的过境路线上包括埃及和苏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甚至突尼斯(突尼斯被包括是因为其现在正为欧盟驻利比亚边境援助特派团提供容身之地)在内的一连串国家进行谈判。这一举措将成为“喀土穆进程”(khartoum process),呼应了欧盟与西非国家的长期对话。但是,鉴于“拉巴特进程”(rabat process)覆盖与西非在欧侨民的关系、汇款便利化等积极议题,“喀土穆进程”专注于狭窄的执法问题:在西非,对于和像尼日利亚、科特迪瓦这样的“发展之星”一起来缓解移民的根源以及快速减轻像尼日尔、马里这样的过境国的压力,欧盟持乐观态度;但是,在非洲之角,欧盟充其量只能希望过境国来压制移民流。
2014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两个对话的区别得到了体现。通过与西非的交换条件,“拉巴特进程”得到了新动力:如果西非国家改进对移民的控制,欧盟同意“支持移民的发展潜力”。这使“拉巴特进程”与欧盟已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采取的移民合作模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盟将增加合法移民的机会和侨汇流动,以便在非正规移民问题上获得合作。与此同时,“喀土穆进程”只得到了一个中心环节:执法。欧盟指望从其发展预算和针对在东非执法的欧洲内部安全基金(european internal security fund)中释放资金。
唯一的光明面是欧盟不必利用其庞大的开支权力来哄骗东非路线上的国家来合作——这一狭隘的焦点实际上是该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在2015年担任“喀土穆进程”主席的埃及)所要求的。
早在2012年,甚至在突尼斯、摩洛哥参加了欧盟提出的关于人口流动和安全的对话之时,埃及已经对欧盟关于这一对话的提议表示不屑——这一对话是成熟的人口流动伙伴关系的先导,将结合作为对开罗控制边境的回报的埃及人移民到欧洲的机会。埃及似乎不希望使自己依赖欧盟。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地区领导,并维持着一个连接从沙特阿拉伯到美国的主要外部大国的网络。绝大多数来自埃及的移民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不是欧洲。至于高技能移民,他们会前往美国等目的地,而那些想要前往欧洲的埃及专业人士,在现有的蓝卡制度下很容易获得资格。因此,开罗提出了自己与欧盟合作的方案:不附加条件的欧洲资金。
4.专家意见如何?
学者们紧张地关注着欧盟与开罗的接洽,他们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欧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两难的抉择:或者是在源头上与专制的厄立特里亚进行合作,或者是在下游的埃及、苏丹创建缓冲区。仅仅因为欧盟不能与厄立特里亚合作,并不能证明其他地方的压制措施是正当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自行解决——来自厄立特里亚(人口只有500万)的人口流动将会自动枯竭。学者们认为,过去十年里每个涌向欧盟的大的移民潮都是这样的故事——首先是非正规移民的持续渐增,然后是急剧上升和急剧下降。每一次,潜在移民的存量都自我耗尽,不论过境国采取的反制政策如何。
过去,学者们对欧盟与过境国、源头国的交易不太担心,因为这通常涉及欧盟为合法移民和侨汇提供新的渠道——比如在西非开始采用的人口流动伙伴关系等政策。但欧盟对起自厄立特里亚的过境路线的处理似乎标志着方向的根本性改变。在“喀土穆进程”下,欧盟不仅是推进生硬的执法政策,而且使自己依赖于缓冲国,并面临开罗方面或喀土穆方面的勒索——它们可能正声称会阻止厄立特里亚人的流动,而厄立特里亚人的流动[实际上]早已缩减。学者们说,如果欧盟以这种方式与苏丹、埃及接洽,将对整个地区造成永久、不必要的损害。
的确,欧盟没有直接向苏丹政府提供任何资金用于边境控制。它仅仅派出了一个实况调查团,以评估向苏丹边境部门提供设备是否可行,以及为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等国际机构在该地区的工作提供资金是否可行。但有人担心,即便如此,也可能使欧盟受到苏丹政客的讹诈。苏丹迫切希望欧盟设立边境训练特派团,显然将其视为获得国际承认的手段,并将其作为取消国际制裁的理由。苏丹政府也因利用援助机构而闻名。它将呼吁欧盟做出支持,然后苏丹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将采用其惯常的伎俩,敲诈那些随后到达的非政府组织。
这个教训很简单。多年来,欧盟一直被赋予令人敬畏的权力来帮助管理国际边境,而这些权力不应该被用于遏制。专家们说,苏丹、摩洛哥和约旦都在利用移民危机来巩固其有争议的边界,而欧盟仅仅是为了阻止人的流动而向它们表示尊重。欧盟未能参与到像也门这样的地方,原因很简单——因为利雅得实际上阻止了人们逃离自己在那里展开的轰炸行动。而且,当欧盟成员国们接受并承认难民时,专家们认为,它们经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破坏源头国,而不是因为它们有一种人道主义义务感。
5.欧盟是如何容纳专家意见的?
欧盟适时地开始寻求更为积极的第三种选择,进一步深入过境路线:与非洲之角本身的“发展之星”埃塞俄比亚合作。这是欧盟尝试从黎凡特移植其新的发展-人道主义方法,并尝试在埃塞俄比亚为厄立特里亚难民和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阻止人们从非洲之角中迁出,不过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的确,欧盟从一开始没有对埃塞俄比亚采取这种积极的关注。它是通过迂回的途径实现的,而且只有在欧盟耗尽了与苏丹、埃及合作的选项之后,以及耗尽了达成一件遣返非正规在欧洲生活的埃塞俄比亚人协议的选项之后。欧盟最初在埃塞俄比亚的重点合乎逻辑地是遣返和边境控制:埃塞俄比亚人口众多,是1亿国民的家园,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潜在外流移民数量可能会使来自厄立特里亚的潜在外流移民数量相形见绌。欧盟成员国提出了为埃塞俄比亚人提供更多合法移民选择和学习场所的建议。但在这个问题上,亚的斯亚贝巴内部意见分歧,谈判陷入僵局。
事后看来,欧盟实际上认为,它最终以这种创造就业岗位计划的形式获得了更好的选择。大多数非正规的埃塞俄比亚移民正朝海湾(“海湾”指波斯湾——译者注)方向迁移。而且,欧盟各国政府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乐意为埃塞俄比亚学生提供优惠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scheme)位置,正是因为他们有自愿再次离开的名声。最终,难民收容协议比遣返协议对欧盟更有价值。
6.现状核实如何?
然而,随着欧盟更好地理解了埃塞俄比亚的动机,它开始意识到,在那里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并不是第一眼看上去那么容易。有人怀疑,在谈判者的经典“两级博弈”中,埃塞俄比亚精明的总理充分利用了国内对他回旋余地的约束,以迫使欧盟做出让步。
在有关遣返协议的初步谈判中,埃塞俄比亚总理以其外交背景发出了强烈的合作愿望:如果这是与欧洲确保关系的一种方式,他就不只是准备帮助欧盟遣返移民。但是,令他明显意外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安全部门破坏了他的形象,它们说它们害怕罪犯、恐怖分子和其他可能谎称拥有埃塞俄比亚国籍的人从欧洲回国。安全部门甚至拒绝与欧盟外交官们交谈,总理只能表示他的尴尬。作为善意的表达,他表示愿意在其他有争议的领域做出让步。他的政府将改进现有的方案,使厄立特里亚人离开难民营、融入劳动力市场。
但是,现在布鲁塞尔有人担心,埃塞俄比亚的同意太容易而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做出“让步”:外交官们推测,埃塞俄比亚正在利用移民危机,在方式上与苏丹、埃及等其他过境国没有什么不同。亚的斯亚贝巴已经获得欧盟的支持,建造两个工业园区,为当地居民和难民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但在布鲁塞尔,有人担心,埃塞俄比亚总理没有提供真正令人信服的商业论证来证明该计划将为难民创造工作机会。埃塞俄比亚政府似乎是在利用移民危机达到国内目的,将其作为一种手段——通过给其支持者创造就业计划来巩固政府。埃塞俄比亚显然也希望将欧盟拉入该地区的权力政治。它的希望是在其与苏丹、埃及的争端中改变态势,当然也要加深国际上对厄立特里亚政权的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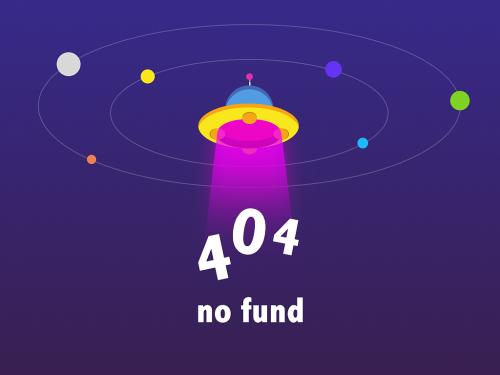
埃塞俄比亚一个工业园区内的工厂
此外,亚的斯亚贝巴还希望加强其在附近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海湾国家一直威胁说,如果亚的斯亚贝巴方面在卡塔尔、也门的争端中站错队,就驱逐埃塞俄比亚移民。讽刺的是,如果亚的斯亚贝巴和布鲁塞尔当初选择让埃塞俄比亚人更多地去欧洲,那可能会更好地满足它们的利益。即使程度小,那也会减轻埃塞俄比亚对海湾市场的依赖。同时,那也可能迫使埃塞俄比亚和欧盟解决移民率仍然很低的一些原因,以及解决许多埃塞俄比亚侨民确实是返回家园的一些原因:埃塞俄比亚的土地权利是声名狼藉地糟糕,这意味着,因为担心失去财产,很少有人会长期移居。亚的斯亚贝巴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进展缓慢,因为攫取土地使其能够承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有助于使其成为“发展之星”。
现在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局势恶化了,边境和移民问题只会加剧竞争。通过提醒阿斯马拉说它们收容了大量的厄立特里亚工人并随时可以驱逐他们,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将厄立特里亚拉入它们与卡塔尔的争端中。卡塔尔对厄立特里亚与沙特阿拉伯结盟的反应是,从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之间有争议的边界撤走了自己的400名观察员。在卡塔尔争端期间一直试图保持中立的索马里,激怒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它们威胁要停止资助邦特兰海岸警卫队(邦特兰是索马里的一个自治区域——译者注)。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手忙脚乱:亚的斯亚贝巴与沙特阿拉伯结盟,因为它担心自己的国民被从穆斯林重地逐回,将打乱自己微妙的宗教平衡,并将抬高它17%的失业率,而该国的创造就业岗位计划易于偏爱政府的支持者。
7.真正的问题原来是什么?
出于原则原因,欧盟拒绝与厄立特里亚就移民的根源问题进行合作。但实际上,这相当于地缘政治的遏制:欧盟加深了厄立特里亚的国际孤立,并在更下游形成了缓冲国。这只会加剧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如果欧盟不改变它的做法,它就有可能陷入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这样的移民过境国之间的竞争。毕竟,欧盟依赖这些国家来阻止人的流动,而且它在那里缺乏其平常的积极手段:这些国家对进入欧洲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欧洲的发展领域支出也附带了太多的改革条件。因此,欧盟是容易受到像苏丹这样的国家利用,苏丹提供边境合作,以换取欧盟在更多至关重要问题(例如,尼罗河水问题)上提供支持:从厄立特里亚前往欧洲的移民流沿着其他物体流动的路径走——诸如水和货物的路径。像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老战略对手并不一定对这些物体流动的可持续管理感兴趣:它们往往只是想打败另一方。
欧盟并不是唯一一个作为单一问题参与者的外部力量。美国在非洲之角有一个单一的重点,即反恐,包括对厄立特里亚实施制裁——因为厄立特里亚支持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al-shabaab)。相比之下,来自中国驻吉布提基地的中国人则在宣传一种“丝绸之路”叙事,该叙事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人口流动管理愿景;而这似乎引起了非洲之角积极的兴趣。欧洲官员现在认识到,移民流的区域管理也可能释放出同样积极的动力。毕竟,人的流动实际上是非洲之角的国家都关心的重要事情,即使赴欧洲移民的具体问题不属于其核心利益。甚至苏丹也在参与,而且只要区域移民问题摊开亮明,苏丹就不再阻碍人权对话。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更为积极的区域移民合作,很明显,欧盟最终将不得不在源头、在厄立特里亚采取行动:这是布鲁塞尔能够避免被拖入与苏丹这类地方进行“零和博弈”式缓冲区交易的唯一途径。当厄立特里亚于2015年年末来到谈判桌前时,它表示已准备好在更深层次的发展领域关系上进行合作。2016年1月,欧盟初步承诺,截至2020年,把2亿欧元花在厄立特里亚,专注于能源基础设施、财务管理和实施联合国领导的人权普遍定期审议所提出的建议。2017年年初,欧盟承诺向该国的创造就业岗位计划提供1300万欧元。欧洲方面不抱任何幻想,事实是过去25年与厄立特里亚接触的每一次尝试都以失望告终,但移民问题使接触好于遏制。
8.欧盟最终进行了何种调整?
2016年年中,管理“喀土穆进程”的民政事务官员们和外交官们决定尝试将他们的工作与更先进的“拉巴特进程”更好地相结合,非洲之角的官员们开始参加向西非学习的会议。这一举动让欧盟或多或少地直接比较了这两个进程中的政治动力,很明显,这两个进程都没有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在西非路线上,欧盟可能过于乐观地与源头国就移民的根源问题进行合作,并对与脆弱的过境国合作的范围过于悲观。在非洲之角,它太喜欢依赖像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过境国,因为在厄立特里亚,它没有看到从源头来处理根源问题的真正机会。
至于在这两条路线上与过境国的合作,欧盟在西非与脆弱的尼日尔合作的体验是非常积极的,不像与埃及、苏丹那样更强大的东非地区大国的合作。这是因为,在尼日尔,发展领域的合作作为对其困境的一种反应是真正有意义的。尼日尔是欧盟可以引入有效的创造就业岗位计划的地方:在阿加德兹(agadez)这样的地区,小规模的就业创造计划能够为那些为移民和偷渡业务提供服务的公民创造“替代生计”。这些措施并没有在东非的过境国真正起作用,在那里它主要意味着为腐败的边防人员创造“替代生计”。在像尼日利亚这样的移民源头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在尼日利亚,欧盟从来没有希望创造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来劝阻年轻人的移民。
在这两条路线的源头合作的比较中,非洲之角的情况并不像最初担心的那样惨淡。变得明朗的是,与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国家合作毕竟是可能的。在阿斯马拉,欧洲官员们发现,一个家长式作风的政权正烦恼于人口的流失。也有报道称,该政府确实允许国民从欧洲回国,即使只是回国旅游观光,这表明其对外部经济来源的依赖。诚然,厄立特里亚官员仍然对欧洲的干涉心存重重疑虑,但在该国获得独立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们表现出对改善国家状况的兴趣。这与快速发展的西非移民源头国的情况相比是有利的:根据一名欧盟成员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是防贪污的,从中得不到个人私利”,西非移民源头国的政治精英会对欧洲的发展领域支出表现出有限的兴趣。
9.长期导向是什么?
欧盟最近开始接触政治孤立的国家,不仅面向欧盟南边比如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地方,而且面向东边家门口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
历史上,欧盟与六个正式组成“东部伙伴关系”的国家中的五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有着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这些国家已经准备好阻止移民流在前往欧盟的途中过境,通常是为了换取它们自己的国民进入欧盟的特权。问题恰在于它们自己的内部边界问题——它们的争议边界和分离地区。这五个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有这样的问题,而欧盟在其多边睦邻政策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它开始处理一个边界问题,它将需要处理所有边界问题。此外,“东部伙伴关系”中唯一没有此类问题的国家是白罗斯——这是最孤立的国家,也是欧盟历来对其采取最大程度不干涉政策的国家。
在2014年前后,欧盟暂时决定将边境合作纳入“东部伙伴关系”的多边轨道,尽管不是通过正面解决边界争议。相反,它试图在一个相对没有争议的事务(它们在黑海和里海共享的海上边界)上鼓励合作。几乎在这一举措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黑海边界突然有争议。但这些事件也使白罗斯与俄罗斯疏远,并将其推入欧盟一边。白罗斯是六国中唯一没有领土问题的国家,它现在向布鲁塞尔表达了它的担忧,即它与俄罗斯的疏远对自己的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在那之前,白罗斯自愿提供了连接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其他地方之间的部分陆桥;现在有人担心莫斯科方面可能会攫取其部分领土)。
就像在厄立特里亚,欧盟也发现了意外的合作机会。白罗斯认为,它可以利用“东部伙伴关系”多边轨道来传播自己的移民和边境管理模式。它想在穿越其领土的越南移民流问题上进行合作。明斯克方面甚至热衷于和欧盟谈判一种人口流动伙伴关系,尽管这将使其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及面临社会层面的人员往来。由于欧盟很好地对待移民,白罗斯渴望其公民获得欧盟的准入权。当它的国民到海湾国家工作时,明斯克发现他们在那里的糟糕待遇迫使它进行干预。换句话说,欧盟,一个试图设定标准的先进的后国家机构,是白罗斯不干涉风格的最大保证者。
此外,就像在非洲之角,欧盟也发现,它在东欧和亚洲的移民外交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的手段。向东,欧盟是两个移民对话的当事方——“布达佩斯进程”和“海牙进程”。俄罗斯官员们表示,他们认为这些对话是至关重要的论坛;与其说是为了讨论移民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为,欧盟将维持这两个进程,即使在它关闭与莫斯科的其他沟通渠道时。换句话说,移民对话是莫斯科向布鲁塞尔提出广泛政治议题的一种手段。反过来,这也使欧盟可以阻止俄罗斯把移民问题“武器化”,即防止它利用东欧国家对其劳动力市场的依赖作为汇款的来源。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