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本文系7月31日谌旭彬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堂讲座的整理,谌老师系腾讯历史频道编辑,“短史记”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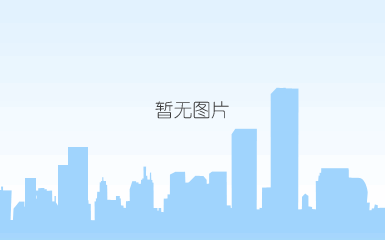
《秦制两千年》,作者签名版,南翔书苑有售
一、什么是秦制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而是久已有之的概念。
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
谭嗣同这句话,正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解释。现代人则不同,因为那是过去了的历史。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总结,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和百姓,建,意味着贵族对封地和百姓拥有治理权。也就是封地里的生产资料属于贵族,劳动力也属于贵族。封建贵族拥戴王权(皇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皇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王权(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王权(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从秦汉到明清,我们一般将之称为“封建时代”,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封而不建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贵族与高级官僚的名下有土地、有爵位,也有俸禄可领,但他们不能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不能治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也不能去处理封地里的政务。它是一种抽离了具体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的“抽象化封建”,或者叫“空洞化封建”。
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会致力于消灭那些有影响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最后造就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当然,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在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重视维护农夫们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农民其实很难从重农抑商政策中获益,汉文帝推行重农抑商,结果农民们纷纷转行去做商人,“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最后只好“驱民而归之农”,用行政力量强行将这些百姓赶回农田。大约同时代的晁错也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其实,商业能让资源与劳动力得到更好的配置,擅长纺织丝绸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纺织丝绸上,生产出更多的丝绸,擅长种植粮食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种植粮食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是“做大蛋糕”的思路。但秦制不是这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不是“做大蛋糕”。
二、秦制的兴亡
按欧阳修和谭嗣同们的看法,秦制从秦帝国一直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这中间,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当然,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全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那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化的原因可以总结?
我把“兴”放在后面,先说“亡”。按我的粗浅理解,从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王朝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了中原。
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一项是官僚集团,另一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和运转。如果这两项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王朝就岌岌可危。
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结合,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从流民蜕变为武装力量。
我认为从秦代到秦代,所有王朝的灭亡都不出这三点原因,没有例外。不同的是,小部分王朝亡于其中一点,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便是统治基础中的军队造反。大部分王朝的灭亡,则同时具备其中两条甚至三条原因。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它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很自然地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明帝国当然只有灭亡一条路可以走。

明朝灭亡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
传统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我觉得,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既不是行不行仁政,也不是领导者有没有雄才大略,而是这个政权有没有建立起一套足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后以萧何为首功,将他排在功劳榜的第一位,就是因为萧何为刘邦建立起了一套非常稳定有效的汲取机制。《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刘邦与项羽争战了五年之久,“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经常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是萧何源源不断地从关中汲取人力和物力,将之送往前线,让刘邦最终得以击败了项羽。
遗憾的是,这种稳定而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往往是非常狠的。这里的狠,指的是对治下的老百姓狠。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对百姓非常残酷,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以往说曹操实施屯田政策,一般都视为仁政。其实曹魏的屯田政策是没有多少温情可言的。它的民屯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也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它的军屯比民屯更狠,内中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士”就是屯田兵。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总之,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也正是这种缺乏温情的屯田制度,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让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第二个话题,是秦制政权夺得天下后,所谓的“治世”“盛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我对此持比较悲观的看法。我在书中用了两章来讲这个事。一章谈的是贞观之治。其实,贞观时代的老百姓过得并不好,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家庭,耗尽全部力气,不考虑苛捐杂税,也只能勉强过上一种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食的生活。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说,今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来逃避朝廷的劳役,不但要治罪,劳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百姓们自残手足的做法,归咎于“隋末遗风”,吕思勉就批评他是胡说,理由是“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劳役太沉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砍自己的手和脚呢?
还有一章谈的是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皇帝,但在他的治下,北宋的百姓也过得很惨,同样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司马光的亲身见闻,是自从实施了“乡户衙前”政策之后,“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因为衙前这个差役是要让底层百姓免费为官府去承担种种运作成本,家庭资产满足条件者就会被选中,然后一年衙前两年衙前做下来,必定倾家荡产。为了逃避倾家荡产,百姓们普遍不敢追求财富,宁愿做不够资格承担衙前差役的穷人。这是个恶性循环,百姓们不敢求富,官府就只好降低资产标准,于是百姓们只好再次“主动”变得更贫穷。
三、秦制下的民众
最后要谈的,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除了安于命运之外,还能采取哪些生存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自然是努力去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通俗一点讲,就是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北宋的江西人疯狂鸡娃,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非常坏,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且收益难以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寻求有力量者的庇护。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也就是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也就是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西汉人贾谊当年也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这是“封建”尚未空洞化的时代,底层百姓可以选择的方式。待到“封建”空洞化了,或者说“封而不建”了,百姓们便只能连人带地荫庇到那些在纳税服役方面享有特权的士绅名下。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有大变故的时代——其实,寻常时代也会有,只是烈度不一定会引起时代记录者们的注意。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民众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一切认识之人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对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其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关于汉武帝时代百姓们的这种消极反抗,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也提供过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们家在东莱(今烟台、威海一带)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了。当地的老人们还说:本朝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国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国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萧望之讲的,其实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关于消极反抗的故事。汉武帝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国营,由官府控制渔民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捕获上来的鱼全部交给官府,由官府来出售和分配。其结果,便是渔民失去了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成了官府无限制盘剥的对象。他们敌不过皇权,为了减轻伤害,只能选择消极怠工,骗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说海里不出鱼了。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它只在某些时段成立,而不是在所有时段里成立。两千年秦制史上,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因为频繁征伐钱不够用,便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便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也就是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代,才在御史大夫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减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当然完全无助于改变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而且很快又恢复了原状。到了东汉的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的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管窥这段故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一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违天逆道”的惨剧,也就是孩子生下来,便被母亲给弄死了。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女婴,而是男女婴皆杀。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哪里受得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他先制定了特殊的地方政策,说杀害子女者与杀人同罪,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第二段史料出自晋代的《零陵先贤传》。里面提到,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的百姓很感激他,把地名给改了,叫做“更生乡”,也就是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
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是很少见的。他们的救济措施,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普遍性的悲惨遭遇。所以,类似的生下孩子便杀掉的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史料。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刘大中说,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知道百姓们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便要给朝廷缴纳紬绢,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没有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生了女儿也不养。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许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也存在了150多年。当然,不是说所有南宋底层百姓都在杀孩子。但南宋不同时期的官员们不断地在奏章里谈这件事,足以显示它是一种常见的、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这种以自戕来减轻外部制度性伤害的史实,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叙述中很少被提及,但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脉络,不能把它当成支线,当成历史脉络里可有可无的枝节。我觉得,它是千万秦民真实的生存底色。
以上种种,当然也并不是要将中国的古代史说成一团漆黑。先秦有讲求民本、提倡仁政的孔孟,汉代也有敢于公开责备桑弘羊苦苛百姓的贤良文学,明代也有人敢于反对删节《孟子》,敢于批判阉党。《诗经》《楚辞》《史记》与《盐铁论》是光芒万丈的遗产,唐诗宋词元曲与明代的市井文学也是传诵千古的宝藏。秦制从秦汉到明清维系了两千多年,那些伟大的心魂和伟大的作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有一种说法,阅读历史应该怀有从“理解之同情”生发出来的温情。我想,这温情最该指向那些普通底层百姓,最该关心他们在历史上的命运起伏,而非相反。毕竟我自己也是底层百姓。这也是《秦制两千年》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
谢谢诸位。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的不好,请多谅解。
(本文系7月31日谌旭彬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堂讲座的整理,谌老师系腾讯历史频道编辑,“短史记”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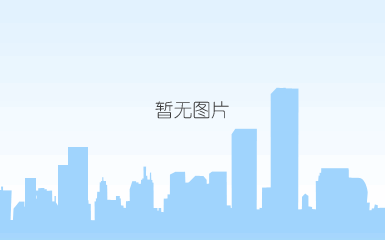
《秦制两千年》,作者签名版,南翔书苑有售
一、什么是秦制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而是久已有之的概念。
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
谭嗣同这句话,正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解释。现代人则不同,因为那是过去了的历史。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总结,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和百姓,建,意味着贵族对封地和百姓拥有治理权。也就是封地里的生产资料属于贵族,劳动力也属于贵族。封建贵族拥戴王权(皇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皇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王权(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王权(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从秦汉到明清,我们一般将之称为“封建时代”,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封而不建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贵族与高级官僚的名下有土地、有爵位,也有俸禄可领,但他们不能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不能治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也不能去处理封地里的政务。它是一种抽离了具体的所有权与治理权的“抽象化封建”,或者叫“空洞化封建”。
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会致力于消灭那些有影响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最后造就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极大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总量。当然,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在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重视维护农夫们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农民其实很难从重农抑商政策中获益,汉文帝推行重农抑商,结果农民们纷纷转行去做商人,“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最后只好“驱民而归之农”,用行政力量强行将这些百姓赶回农田。大约同时代的晁错也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其实,商业能让资源与劳动力得到更好的配置,擅长纺织丝绸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纺织丝绸上,生产出更多的丝绸,擅长种植粮食者可以将精力放在种植粮食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是“做大蛋糕”的思路。但秦制不是这样,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不是“做大蛋糕”。
二、秦制的兴亡
按欧阳修和谭嗣同们的看法,秦制从秦帝国一直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这中间,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当然,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全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那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化的原因可以总结?
我把“兴”放在后面,先说“亡”。按我的粗浅理解,从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王朝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了中原。
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一项是官僚集团,另一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和运转。如果这两项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王朝就岌岌可危。
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结合,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从流民蜕变为武装力量。
我认为从秦代到秦代,所有王朝的灭亡都不出这三点原因,没有例外。不同的是,小部分王朝亡于其中一点,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便是统治基础中的军队造反。大部分王朝的灭亡,则同时具备其中两条甚至三条原因。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它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很自然地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明帝国当然只有灭亡一条路可以走。

明朝灭亡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
传统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我觉得,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既不是行不行仁政,也不是领导者有没有雄才大略,而是这个政权有没有建立起一套足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最后以萧何为首功,将他排在功劳榜的第一位,就是因为萧何为刘邦建立起了一套非常稳定有效的汲取机制。《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刘邦与项羽争战了五年之久,“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经常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是萧何源源不断地从关中汲取人力和物力,将之送往前线,让刘邦最终得以击败了项羽。
遗憾的是,这种稳定而有效率的汲取系统,往往是非常狠的。这里的狠,指的是对治下的老百姓狠。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对百姓非常残酷,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以往说曹操实施屯田政策,一般都视为仁政。其实曹魏的屯田政策是没有多少温情可言的。它的民屯近似于一种农奴制度。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终身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不但没有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也包括给长官做家奴,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它的军屯比民屯更狠,内中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士”就是屯田兵。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曹操还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官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总之,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也正是这种缺乏温情的屯田制度,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让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第二个话题,是秦制政权夺得天下后,所谓的“治世”“盛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我对此持比较悲观的看法。我在书中用了两章来讲这个事。一章谈的是贞观之治。其实,贞观时代的老百姓过得并不好,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家庭,耗尽全部力气,不考虑苛捐杂税,也只能勉强过上一种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食的生活。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说,今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来逃避朝廷的劳役,不但要治罪,劳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里把百姓们自残手足的做法,归咎于“隋末遗风”,吕思勉就批评他是胡说,理由是“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如果不是劳役太沉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砍自己的手和脚呢?
还有一章谈的是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备受赞誉的皇帝,但在他的治下,北宋的百姓也过得很惨,同样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司马光的亲身见闻,是自从实施了“乡户衙前”政策之后,“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因为衙前这个差役是要让底层百姓免费为官府去承担种种运作成本,家庭资产满足条件者就会被选中,然后一年衙前两年衙前做下来,必定倾家荡产。为了逃避倾家荡产,百姓们普遍不敢追求财富,宁愿做不够资格承担衙前差役的穷人。这是个恶性循环,百姓们不敢求富,官府就只好降低资产标准,于是百姓们只好再次“主动”变得更贫穷。
三、秦制下的民众
最后要谈的,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除了安于命运之外,还能采取哪些生存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境况。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自然是努力去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通俗一点讲,就是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北宋的江西人疯狂鸡娃,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非常坏,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且收益难以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寻求有力量者的庇护。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也就是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也就是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西汉人贾谊当年也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这是“封建”尚未空洞化的时代,底层百姓可以选择的方式。待到“封建”空洞化了,或者说“封而不建”了,百姓们便只能连人带地荫庇到那些在纳税服役方面享有特权的士绅名下。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有大变故的时代——其实,寻常时代也会有,只是烈度不一定会引起时代记录者们的注意。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民众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一切认识之人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作为对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其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关于汉武帝时代百姓们的这种消极反抗,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也提供过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们家在东莱(今烟台、威海一带)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了。当地的老人们还说:本朝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国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了。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国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萧望之讲的,其实是一个古老而惨烈的关于消极反抗的故事。汉武帝以无远弗届的皇权垄断山海,将捕鱼业变成国营,由官府控制渔民在固定时间去固定区域劳作,捕获上来的鱼全部交给官府,由官府来出售和分配。其结果,便是渔民失去了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成了官府无限制盘剥的对象。他们敌不过皇权,为了减轻伤害,只能选择消极怠工,骗那些管控者和汲取者,说海里不出鱼了。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境。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它只在某些时段成立,而不是在所有时段里成立。两千年秦制史上,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
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因为频繁征伐钱不够用,便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便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也就是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到汉元帝时代,才在御史大夫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减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当然完全无助于改变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而且很快又恢复了原状。到了东汉的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的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管窥这段故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一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违天逆道”的惨剧,也就是孩子生下来,便被母亲给弄死了。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女婴,而是男女婴皆杀。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哪里受得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他先制定了特殊的地方政策,说杀害子女者与杀人同罪,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第二段史料出自晋代的《零陵先贤传》。里面提到,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的百姓很感激他,把地名给改了,叫做“更生乡”,也就是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
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是很少见的。他们的救济措施,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普遍性的悲惨遭遇。所以,类似的生下孩子便杀掉的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我给大家分享一段史料。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
“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刘大中说,臣我以前做过地方官,知道百姓们最痛苦的负担是丁盐紬绢。养了儿子便要给朝廷缴纳紬绢,所以愚民宁愿杀子来逃避;养了女儿又没有资产将她嫁出去,所以生了女儿也不养。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许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也存在了150多年。当然,不是说所有南宋底层百姓都在杀孩子。但南宋不同时期的官员们不断地在奏章里谈这件事,足以显示它是一种常见的、值得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这种以自戕来减轻外部制度性伤害的史实,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叙述中很少被提及,但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脉络,不能把它当成支线,当成历史脉络里可有可无的枝节。我觉得,它是千万秦民真实的生存底色。
以上种种,当然也并不是要将中国的古代史说成一团漆黑。先秦有讲求民本、提倡仁政的孔孟,汉代也有敢于公开责备桑弘羊苦苛百姓的贤良文学,明代也有人敢于反对删节《孟子》,敢于批判阉党。《诗经》《楚辞》《史记》与《盐铁论》是光芒万丈的遗产,唐诗宋词元曲与明代的市井文学也是传诵千古的宝藏。秦制从秦汉到明清维系了两千多年,那些伟大的心魂和伟大的作品也延续了两千多年。有一种说法,阅读历史应该怀有从“理解之同情”生发出来的温情。我想,这温情最该指向那些普通底层百姓,最该关心他们在历史上的命运起伏,而非相反。毕竟我自己也是底层百姓。这也是《秦制两千年》这本书最关心的问题。
谢谢诸位。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的不好,请多谅解。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