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5期(2017年4月))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对于和日本建立东海危机管控(crisis management)机制的政策,涵盖2008年谈判开始至2015年底陷入僵局这一时期。在这七年中,中国从不情愿的谈判者变成中断谈判者,最终又接受恢复谈判,但却设置了谈判涉及的相对主权收益的高标准。本文认为,尽管东亚发生海上事变的风险正在上升,但在安全领域的“信任建立”(confidence-building)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圈传统上拒绝这种规范)上,中国的社会化进展非常缓慢。结论是,对于危机管控谈判,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用其来确保诸多外交目标(这些目标与主权、势力均衡相关联),而非把其当作纯粹为了构建安全与稳定而冻结现状的工具。
[关键词]东海 钓鱼岛 尖阁诸岛 危机管控 海上安全 建立信任措施
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和东海的与日本划界问题是中国余留的两个领土争端,也是北京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这两个争端已成为中日关系不稳的根源,并伴有军事冲突的风险,其中不仅有中日之间在东亚的总体战略性竞争引发的风险,而且有在争议区域的更具体军事活动引起的风险,这些军事活动在恶化的情势中会导致未经筹划的对抗。由于中国决定在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区域特别是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区域(日本在行政上控制着该岛,并且不承认关于该岛存在着主权争端)确立更日常的存在,第二类风险近年来已大幅上升。[1]
中国领土争端政策的历史表明,在一定的情况下它愿意妥协达成最终的边界协定。傅泰林(taylor fravel)阐述了反直觉的国内的不安全感是造成陆地边界谈判做出妥协的一个因素,而议价能力的下降是造成军事紧张升级的一个因素。傅阐明,对于海上争端,中国不断以拖延相待,其间有两次决定在南海使用武力——在西沙(1974年)和南沙(1988年)针对越南。拖延恰恰是邓小平在东海和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建议,他1978年时说出如下名言:双方应把“这样的问题放一下”,因为这个问题“不要紧”,“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然而,近年来,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紧张导致中日关系议程上出现了危机管控谈判,而要通过谈判解决主权争端,似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在边界谈判方面,中国有着长期纪录,但在达成危机管控安排以减少与海上争端相关的意外危机方面,中国没有纪录。2002年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不具约束性的,虽然这一宣言阻止了南海主权声索方新的占领,但没有阻止当前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紧张关系的循环、海上的危险僵局。台湾海峡和两岸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在政治紧张时期降低事变风险的危机管控机制范例。
对于积极和自己进行海上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偏向于回避和它们达成降低军事安全风险的协定?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分析了人民解放军专家对大量危机管控文献的开发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冷战概念、美国智库在当代向北京同行推广危机管控观念的更多努力这两点的理论影响。他得出结论,尽管危机管控这一主题明显获得更多的注意,许多中国特色把危机管控路径的影响限制在决策领域:人民解放军特定的战术性概念,一种“中国例外主义的景象”,以及缺乏强有力的危机管控机构和机制。人们发现,达成“信任建立协定”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的谈判策略,尤其是当有政治风险时中国事实上一贯要求把对总体原则的认可作为开始技术性会谈的前提条件,在领土争端上显然就是如此。本文本质上是限制性地采用危机管控这一概念,指涉在争议领土上军事力量的行为和沟通方面(以及就战略信任而言的潜在的积极的政治外溢效应);在该领域,设置政治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会倾向于和主权关联,而主权问题恰恰是危机管控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规避的。
本文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附着于危机管控的外交政策目标:从2008年开始,到2015年底陷入僵局的与日本关于东海海空联络机制(macm)的谈判。海空联络机制被设想为方便中日军事力量的联络,以防止近距离接触时发生意外冲突。实质上,它只包括军事安全风险。在本文分析的七年间,中国从不情愿的谈判者变成中断谈判者,最终又接受恢复谈判,但却设置了谈判涉及的相对主权收益的高标准。本文认为,尽管东亚发生海上事变的风险正在上升,但在安全领域的“信任建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圈传统上拒绝这种规范)上,中国的社会化进展非常缓慢。结论是,对于危机管控谈判,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用其来确保诸多外交目标(这些目标与主权、势力均衡相关联),而非把其当作纯粹为了构建安全与稳定而冻结现状的工具。这显示中国对于东海的外交政策并非为了构建稳定的现状,而是被对政治与领土收益的追求所驱动,于是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同时,分析表明,虽然中国的战略圈并非完全相信“危机管控”对于降低军事事变风险的有效性,但对危机管控观念的支持正在相对升高。
一、中日东海危机管控谈判概览
在2015年10月初,日本媒体报道与中国构建东海海空联络机制的谈判已陷入僵局。《解放军报》简单报道说“方案被中国拒绝”。日方说原因是中国“反对日方的不把机制适用于双方的领海和领空的提议”。对日本而言,把机制延伸到领海和领空将等于承认中国对日本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诸岛上的主权的挑战。根据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小谷哲男的说法,“如果机制适用于领海,中国会误解他们只要(和日本)联络就能闯入”。在中国方面,一位与谈判有关的军事分析家辩称,日方提议最终文件中应该明确认可把争议岛屿周围12海里的区域排除在外,这个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无益的,因为没有一个危机管控安排把争议极大的地理区域排除在外”。尽管双方表达了降低军舰、执法船、渔船间意外冲突风险的意愿,整个谈判进程展示了在争议海域的主权和有效管理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海空联络机制是中日间三个危机管控磋商渠道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军方对军方层级的(见表一)。在东海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日于2007年开启危机管控谈判,目标是增进政治层级和军事对军事层级的联络、建立信任。两个推动力是第一任安倍政府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他们在2007年峰会期间做出了政治推动。他们的即刻关注点是鉴于双方舰船在东海的存在,要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升级为全面危机。2007年时的谈判并没有后来2012年底时那样的紧迫感,而是被设想为在如下两个领土争端未解决的背景下建立军事信任的尝试:钓鱼岛/尖阁诸岛主权争端和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端(见地图一)。根据一名日本高官非正式的说法,日方的目标也是构建一种过程,在该过程中,与中国军方的定期互动将会对政治关系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表一:中日危机管控机制
|
|
渠道建立时间 |
政府机构 |
目标 |
|
海空联络机制 |
2008年 |
国防部/防卫省 |
防止军事力量间的意外冲突 |
|
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
2012年 |
外交部/外务省率领的海洋政策政府代表团 |
建立海洋事务上的政治信任 |
|
海上搜救协议 |
1977年;2012年原则共识 |
外交部/外务省、日本海上保安厅和中国海事局 |
搜录救助联合行动 |
来源:james przystup、john bradford和james manicom:《中日海上信任建立和联络机制》, 载于《pacnet通讯》第67期,2013年8月20日,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67-japan-china-maritime-confidence-building-and-communications-mechanisms(2016年8月4日访问)。

关于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当时称为“海上联络机制”(mcm))的第一轮会谈于2008年4月21日于北京举行。率领者是双方的国防部/防卫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和日本国防卫省国际政策课。双方加入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的构成突显了在日中关系更广泛的图景中会谈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是唯一由双方军方领导的进行中的谈判。
在2012年9月被中方中断之前,总共有三轮会谈(见表二)。在2012年6月的会议上,日中联合工作组达成谅解,原则同意建立由三根主要支柱构成的海上联络机制:1)年度会议和定期专家会议;2)两国防务部门间的高级别热线;3)军舰和军机间的直接联络(以及关于共用的无线电频率的协定)。如一位参与谈判的日方官员所提到的,2012年6月达成的谅解是好到足以付诸实施并本来能开始执行的,但政治使中日关系达到新的最为紧张的程度。直至2015年初,中日谈判者仍然要基于2012年双方同意的三个结构要素来讨论一个可能达成的协定。
表二:中日海空联络机制(macm)谈判大事记
|
日期 |
成就 |
|
2008年4月21日,北京 |
工作组首次会议 |
|
2010年7月26日,东京 |
讨论机制的整体结构 |
|
2012年6月28、29日,北京 |
在以三根支柱为基础的机制结构上达成原则共识 |
|
2015年1月12日,东京 |
恢复会谈,决定把机制扩大到也覆盖航空器间的联络;决定“早日落实机制” |
|
2015年6月 |
讨论技术细节,重申早日落实的重要性 |
来源:james przystup、john bradford和james manicom:《中日海上信任建立和联络机制》, 载于《pacnet通讯》第67期,2013年8月20日,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67-japan-china-maritime-confidence-building-and-communications-mechanisms(2016年8月4日访问);日本首相及其内阁:内阁官房长官记者招待会,2015年1月13日,http://japan.kantei.go.jp/tyoukanpress/201501/13_a.html(2016年3月11日访问);与日本外交政策高级分析员的往来电子邮件,2016年1月。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尖阁诸岛三座岛屿[2]。作为报复,中国政府中断了大部分沟通渠道。专家学者间的二轨安全对话甚至都被取消。对三座岛屿的购买,中国媒体称之为“国有化”,被新华社形容为“极其危险”,被《人民日报》形容为“二战后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挑战”。中国战略圈的主流分析是把日本的决定看成对现状的单方面转变,照此看法,就需要进行报复以重建平衡、构筑新的现状。例如,解放军海军智库的一名高级军官张军社阐述了这种叙事:“钓鱼岛的现状在搁置争议原则下已经持续了约40年,而一年多之前,当日本政府发起‘购买’和‘国有化’该岛的单方面举动时,现状被打破。”在会谈中断期间,紧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此予以详述。在安倍首相2013年12月26日参拜东京靖国神社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参拜“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为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制造了新的严重障碍”,并说,日方将要“为此承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此,中方把两国外交的正常化——包括危机管控谈判的恢复——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姿态联系起来。
在中断了近三年之后,谈判最终于2015年1月在“四点共识”(中文一般这样称呼)的基础上恢复,四点共识系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特别顾问谷内正太郎于2014年11月在北京达成。这些共识是紧张但又非常审慎的外交磋商的结果,包含关于历史问题的表述,在“战略互惠”基础上意图发展两国关系的声明,承诺谈判建立危机管控机制。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共识为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上任后的第一次——冷淡的——峰会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见是在2014年11月北京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间隙进行的。中国外交部说峰会是应日方要求举行的,结果是决定落实“四点共识”。北京最高政治级别的认可是实现会谈恢复的真正转折点。
2015年1月12日在东京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中,双方同意机制也应该覆盖空中冲突的风险,不只集中于海上的危险邂逅。双方还同意早日落实机制。2013年11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双方飞机有一系列危险的近距离接触,继之有了上述新机制。于是,机制的名称变为“海空联络机制”。一位日方与会者形容氛围是“友好”和“非常有建设性的”。第五轮会谈于2015年6月举行,完成了与航空器间联络有关的技术性细节。双方2015年久拖不决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公开书面协议还是应该内容保密;根据在东京的采访,日方坚持公开协议。然而,结果是,关键的阻碍因素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而是和协议覆盖的地理范围有关;中方坚持协议也应适用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的12海里领海;根据中国专家的说法,日方坚持明确把该区域排除在最终协议之外,而非不说明协议适用的地理范围。
正如第二部分所述,2012年后,事变风险陡升,部分是因为中国执法机构参与了争端,同时日本海上保安也做出了更大的反应。海空联络机制没有覆盖执行机构的活动。双方进行的平行磋商“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汇聚了与海上安全活动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包括中国国家海洋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笔者撰写本文时,这些磋商并没有打算要达成管理两国海警活动的具体协议,而只是充当非常初级的建立信任尝试,因为较之军方,海警更缺少双边互动。几位日本安全专家倡议,一旦完成,军方对军方的危机管控机制还应当延伸到执法机构的活动。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5期(2017年4月))
[摘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对于和日本建立东海危机管控(crisis management)机制的政策,涵盖2008年谈判开始至2015年底陷入僵局这一时期。在这七年中,中国从不情愿的谈判者变成中断谈判者,最终又接受恢复谈判,但却设置了谈判涉及的相对主权收益的高标准。本文认为,尽管东亚发生海上事变的风险正在上升,但在安全领域的“信任建立”(confidence-building)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圈传统上拒绝这种规范)上,中国的社会化进展非常缓慢。结论是,对于危机管控谈判,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用其来确保诸多外交目标(这些目标与主权、势力均衡相关联),而非把其当作纯粹为了构建安全与稳定而冻结现状的工具。
[关键词]东海 钓鱼岛 尖阁诸岛 危机管控 海上安全 建立信任措施
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主权问题和东海的与日本划界问题是中国余留的两个领土争端,也是北京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这两个争端已成为中日关系不稳的根源,并伴有军事冲突的风险,其中不仅有中日之间在东亚的总体战略性竞争引发的风险,而且有在争议区域的更具体军事活动引起的风险,这些军事活动在恶化的情势中会导致未经筹划的对抗。由于中国决定在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区域特别是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区域(日本在行政上控制着该岛,并且不承认关于该岛存在着主权争端)确立更日常的存在,第二类风险近年来已大幅上升。[1]
中国领土争端政策的历史表明,在一定的情况下它愿意妥协达成最终的边界协定。傅泰林(taylor fravel)阐述了反直觉的国内的不安全感是造成陆地边界谈判做出妥协的一个因素,而议价能力的下降是造成军事紧张升级的一个因素。傅阐明,对于海上争端,中国不断以拖延相待,其间有两次决定在南海使用武力——在西沙(1974年)和南沙(1988年)针对越南。拖延恰恰是邓小平在东海和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建议,他1978年时说出如下名言:双方应把“这样的问题放一下”,因为这个问题“不要紧”,“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然而,近年来,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的紧张导致中日关系议程上出现了危机管控谈判,而要通过谈判解决主权争端,似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在边界谈判方面,中国有着长期纪录,但在达成危机管控安排以减少与海上争端相关的意外危机方面,中国没有纪录。2002年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不具约束性的,虽然这一宣言阻止了南海主权声索方新的占领,但没有阻止当前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之间紧张关系的循环、海上的危险僵局。台湾海峡和两岸关系并没有提供一个在政治紧张时期降低事变风险的危机管控机制范例。
对于积极和自己进行海上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偏向于回避和它们达成降低军事安全风险的协定?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分析了人民解放军专家对大量危机管控文献的开发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冷战概念、美国智库在当代向北京同行推广危机管控观念的更多努力这两点的理论影响。他得出结论,尽管危机管控这一主题明显获得更多的注意,许多中国特色把危机管控路径的影响限制在决策领域:人民解放军特定的战术性概念,一种“中国例外主义的景象”,以及缺乏强有力的危机管控机构和机制。人们发现,达成“信任建立协定”面临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国的谈判策略,尤其是当有政治风险时中国事实上一贯要求把对总体原则的认可作为开始技术性会谈的前提条件,在领土争端上显然就是如此。本文本质上是限制性地采用危机管控这一概念,指涉在争议领土上军事力量的行为和沟通方面(以及就战略信任而言的潜在的积极的政治外溢效应);在该领域,设置政治前提是有问题的,因为会倾向于和主权关联,而主权问题恰恰是危机管控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规避的。
本文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附着于危机管控的外交政策目标:从2008年开始,到2015年底陷入僵局的与日本关于东海海空联络机制(macm)的谈判。海空联络机制被设想为方便中日军事力量的联络,以防止近距离接触时发生意外冲突。实质上,它只包括军事安全风险。在本文分析的七年间,中国从不情愿的谈判者变成中断谈判者,最终又接受恢复谈判,但却设置了谈判涉及的相对主权收益的高标准。本文认为,尽管东亚发生海上事变的风险正在上升,但在安全领域的“信任建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圈传统上拒绝这种规范)上,中国的社会化进展非常缓慢。结论是,对于危机管控谈判,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用其来确保诸多外交目标(这些目标与主权、势力均衡相关联),而非把其当作纯粹为了构建安全与稳定而冻结现状的工具。这显示中国对于东海的外交政策并非为了构建稳定的现状,而是被对政治与领土收益的追求所驱动,于是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同时,分析表明,虽然中国的战略圈并非完全相信“危机管控”对于降低军事事变风险的有效性,但对危机管控观念的支持正在相对升高。
一、中日东海危机管控谈判概览
在2015年10月初,日本媒体报道与中国构建东海海空联络机制的谈判已陷入僵局。《解放军报》简单报道说“方案被中国拒绝”。日方说原因是中国“反对日方的不把机制适用于双方的领海和领空的提议”。对日本而言,把机制延伸到领海和领空将等于承认中国对日本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尖阁诸岛上的主权的挑战。根据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专家小谷哲男的说法,“如果机制适用于领海,中国会误解他们只要(和日本)联络就能闯入”。在中国方面,一位与谈判有关的军事分析家辩称,日方提议最终文件中应该明确认可把争议岛屿周围12海里的区域排除在外,这个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无益的,因为没有一个危机管控安排把争议极大的地理区域排除在外”。尽管双方表达了降低军舰、执法船、渔船间意外冲突风险的意愿,整个谈判进程展示了在争议海域的主权和有效管理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海空联络机制是中日间三个危机管控磋商渠道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军方对军方层级的(见表一)。在东海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中日于2007年开启危机管控谈判,目标是增进政治层级和军事对军事层级的联络、建立信任。两个推动力是第一任安倍政府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他们在2007年峰会期间做出了政治推动。他们的即刻关注点是鉴于双方舰船在东海的存在,要防止海上意外事件升级为全面危机。2007年时的谈判并没有后来2012年底时那样的紧迫感,而是被设想为在如下两个领土争端未解决的背景下建立军事信任的尝试:钓鱼岛/尖阁诸岛主权争端和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划界争端(见地图一)。根据一名日本高官非正式的说法,日方的目标也是构建一种过程,在该过程中,与中国军方的定期互动将会对政治关系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
表一:中日危机管控机制
|
|
渠道建立时间 |
政府机构 |
目标 |
|
海空联络机制 |
2008年 |
国防部/防卫省 |
防止军事力量间的意外冲突 |
|
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
2012年 |
外交部/外务省率领的海洋政策政府代表团 |
建立海洋事务上的政治信任 |
|
海上搜救协议 |
1977年;2012年原则共识 |
外交部/外务省、日本海上保安厅和中国海事局 |
搜录救助联合行动 |
来源:james przystup、john bradford和james manicom:《中日海上信任建立和联络机制》, 载于《pacnet通讯》第67期,2013年8月20日,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67-japan-china-maritime-confidence-building-and-communications-mechanisms(2016年8月4日访问)。

关于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当时称为“海上联络机制”(mcm))的第一轮会谈于2008年4月21日于北京举行。率领者是双方的国防部/防卫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和日本国防卫省国际政策课。双方加入了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的构成突显了在日中关系更广泛的图景中会谈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是唯一由双方军方领导的进行中的谈判。
在2012年9月被中方中断之前,总共有三轮会谈(见表二)。在2012年6月的会议上,日中联合工作组达成谅解,原则同意建立由三根主要支柱构成的海上联络机制:1)年度会议和定期专家会议;2)两国防务部门间的高级别热线;3)军舰和军机间的直接联络(以及关于共用的无线电频率的协定)。如一位参与谈判的日方官员所提到的,2012年6月达成的谅解是好到足以付诸实施并本来能开始执行的,但政治使中日关系达到新的最为紧张的程度。直至2015年初,中日谈判者仍然要基于2012年双方同意的三个结构要素来讨论一个可能达成的协定。
表二:中日海空联络机制(macm)谈判大事记
|
日期 |
成就 |
|
2008年4月21日,北京 |
工作组首次会议 |
|
2010年7月26日,东京 |
讨论机制的整体结构 |
|
2012年6月28、29日,北京 |
在以三根支柱为基础的机制结构上达成原则共识 |
|
2015年1月12日,东京 |
恢复会谈,决定把机制扩大到也覆盖航空器间的联络;决定“早日落实机制” |
|
2015年6月 |
讨论技术细节,重申早日落实的重要性 |
来源:james przystup、john bradford和james manicom:《中日海上信任建立和联络机制》, 载于《pacnet通讯》第67期,2013年8月20日,https://www.csis.org/analysis/pacnet-67-japan-china-maritime-confidence-building-and-communications-mechanisms(2016年8月4日访问);日本首相及其内阁:内阁官房长官记者招待会,2015年1月13日,http://japan.kantei.go.jp/tyoukanpress/201501/13_a.html(2016年3月11日访问);与日本外交政策高级分析员的往来电子邮件,2016年1月。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尖阁诸岛三座岛屿[2]。作为报复,中国政府中断了大部分沟通渠道。专家学者间的二轨安全对话甚至都被取消。对三座岛屿的购买,中国媒体称之为“国有化”,被新华社形容为“极其危险”,被《人民日报》形容为“二战后对中国主权最严重的挑战”。中国战略圈的主流分析是把日本的决定看成对现状的单方面转变,照此看法,就需要进行报复以重建平衡、构筑新的现状。例如,解放军海军智库的一名高级军官张军社阐述了这种叙事:“钓鱼岛的现状在搁置争议原则下已经持续了约40年,而一年多之前,当日本政府发起‘购买’和‘国有化’该岛的单方面举动时,现状被打破。”在会谈中断期间,紧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此予以详述。在安倍首相2013年12月26日参拜东京靖国神社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参拜“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为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制造了新的严重障碍”,并说,日方将要“为此承担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此,中方把两国外交的正常化——包括危机管控谈判的恢复——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姿态联系起来。
在中断了近三年之后,谈判最终于2015年1月在“四点共识”(中文一般这样称呼)的基础上恢复,四点共识系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特别顾问谷内正太郎于2014年11月在北京达成。这些共识是紧张但又非常审慎的外交磋商的结果,包含关于历史问题的表述,在“战略互惠”基础上意图发展两国关系的声明,承诺谈判建立危机管控机制。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共识为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上任后的第一次——冷淡的——峰会铺平了道路,这次会见是在2014年11月北京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间隙进行的。中国外交部说峰会是应日方要求举行的,结果是决定落实“四点共识”。北京最高政治级别的认可是实现会谈恢复的真正转折点。
2015年1月12日在东京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中,双方同意机制也应该覆盖空中冲突的风险,不只集中于海上的危险邂逅。双方还同意早日落实机制。2013年11月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双方飞机有一系列危险的近距离接触,继之有了上述新机制。于是,机制的名称变为“海空联络机制”。一位日方与会者形容氛围是“友好”和“非常有建设性的”。第五轮会谈于2015年6月举行,完成了与航空器间联络有关的技术性细节。双方2015年久拖不决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公开书面协议还是应该内容保密;根据在东京的采访,日方坚持公开协议。然而,结果是,关键的阻碍因素不是和这个问题有关,而是和协议覆盖的地理范围有关;中方坚持协议也应适用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周边的12海里领海;根据中国专家的说法,日方坚持明确把该区域排除在最终协议之外,而非不说明协议适用的地理范围。
正如第二部分所述,2012年后,事变风险陡升,部分是因为中国执法机构参与了争端,同时日本海上保安也做出了更大的反应。海空联络机制没有覆盖执行机构的活动。双方进行的平行磋商“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汇聚了与海上安全活动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包括中国国家海洋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笔者撰写本文时,这些磋商并没有打算要达成管理两国海警活动的具体协议,而只是充当非常初级的建立信任尝试,因为较之军方,海警更缺少双边互动。几位日本安全专家倡议,一旦完成,军方对军方的危机管控机制还应当延伸到执法机构的活动。
二、从反应式强势到支持海空联络机制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与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相撞。该事件激发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日方把中方船长和船员拘留了十天,中国政府谴责日本首次把其国内法施行于中国主张主权的领土从而单方面破坏了现状。虽然随后船员获释,但围绕撞船事件的事态发展——政治紧张、外交互詈、中国的反日示威、日本出现的反华情绪——清楚地表明此类事件能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最坏的情形能到把两国推向武力冲突边缘。这是一个先例——它说明作为稳定工具的危机管控的重要性。
中日在对海空联络机制的看法上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达成危机管控机制已是安倍政府的优先事项。日本2014年的防卫白皮书提到,考虑到最近两军间的冲突危险事件,机制的建立已成“当务之急”。日本防卫省把机制形容为旨在避免“意外冲突和防止海上空中无法预料的后果升级为军事冲突或政治问题,以及增强相互理解和互信关系,加强防务合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在北京远未达到压倒性程度,那里的官方话语强调在恢复谈判之前日本改变态度的重要性。结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保持着如下观念:危机管控机制是日本的方案,首先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无论是中国外交部还是更广泛的中国战略圈都没有把危机管控规划为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相反,把它规划为为了战略稳定且只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让步。实际上,中国把危机管控谈判关联到两个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取得日本承认钓鱼岛/尖阁诸岛存在主权争议;改变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特别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做法,该问题被中国视为两国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
中国的战略叙事表达围绕着如下观念进行:对于钓鱼岛/尖阁诸岛,在日本“单方面国有化”之后,中国必须达成新的现状。为了这一目的,中国政府在东海选择了公开对抗政策,持续展开攻势。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在一份报告中,把中国的做法恰当地形容为“反应式强势”[3]。攻势的目的是达到对该岛管理进行争夺的形势——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该目标,但通过三个关键决定来静悄悄地追求。中国决策者寻求的新现状是两国军队和执法机构的巡逻船将定期在该岛周围和东海争议区域相遇。结果,不仅在政治和外交层面,而且在更基本的对该岛日常管理层面,日本的主权主张将会受到挑战。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双方间事变风险陡增。
首先,中国决定派遣日常巡逻船进入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领海和毗连区。图一显示了中国巡逻船在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领海(12海里)和毗连区(24海里)出现的频次。数据显示在2012年之前出现在领海的极其个别。转折点是2012年9月,有13次巡逻,是作为对日本政府把三座岛屿“国有化”的反应,这表明北京把巡逻构想为一种报复性举动,以重构新的现状。2012年9月至2013年10月,月度峰值有规律的出现,反映出政治关系高度紧张,并增大了意外冲突的风险。在2013年4月和8月,日方识别出的中国船进入12海里以内区域分别有25和28次。另一个转折点是2013年10月,巡逻实现“常态化”,每月约10次在该岛领海巡逻。峰值后巡逻频次的稳定证明,中国已赢得以日本对该岛的行政管理为对象的常规争夺。

对中国在东海危机管控上的做法起关键决定作用的是中国执法能力的快速现代化。在这方面,中国海洋执法机构的改革是关键转折点,使中国能把关于巡逻的战略标准化和系统化。201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改革中国的海洋执法机构,将四个机构合并为新成立的中国海警局。印有新的海警标识的中国船于2013年7月首次亮相。根据日本高官的说法,一支典型的海警巡逻船队由三艘船组成,除了越来越大的约5000吨级,大多是1000到3000吨级;海警船队正改装解放军海军的护卫舰来服役,并已采用解放军海军中现役的江凯级护卫舰054-a的设计来建造新的4000吨级海警船。较之由解放军海军负责日常巡逻,由中国海警局和国家海洋局受权负责已使紧张局势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并试图向国内外发出该问题是内政的政治信号。
其次,2012年后,中国在争议岛屿上方的空中存在也陡增。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日本在东海、钓鱼岛/尖阁诸岛上方的防空识别区(adiz)有重叠(见地图一)。尽管这是世界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却明显是一个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即挑战日本对该岛的管理——也是针对国家购岛行为的报复性举动。防空识别区的划设也意在改变全球对于东海动态的报道。中国的防务分析人员经常抱怨日本在公共外交上拥有优势,因为它发布中国闯入其领土的数据(本文所用),塑造全世界分析家的思维,型构国际上的公共辩论。防空识别区划设后,中国的英文媒体开始发布日本闯入中国防空识别区的信息。虽然中国明显缺少能力来完全执行防空识别区规程、拦截日本或美国的所有军机,但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宣告为中国增加在该区域的空中巡逻频次铺平了道路,并创造了基于国内法的支持巡逻合法性的论据。2012年12月,当与日本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时,中国只有一架航空器(属于国家海洋局)飞入该岛的空域;而自从防空识别区宣告后,在该岛北方东海内的飞行已增多。关于这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一个有价值的指标是日本航空自卫队升空拦截的数量(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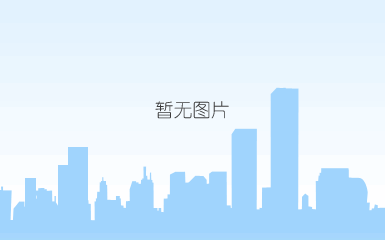
第三,解放军海军也增加了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附近的存在。2015年11月,一艘“东调”级解放军海军侦察船被识别出在该岛南方的毗连区活动。2016年6月,一艘解放军海军军舰被发现首次在24海里以内区域活动,日本政府召见中国大使。这标志着,在中国海军军舰数次靠近该岛后,局势升级,并可能与危机管控谈判停止有关,因为僵局的根源首次成为具体的安全问题,即在该区域的解放军海军军舰被纳入或排除出最终协议。一般而论,中国海军关于该岛的战略是通过执法机构显示力量,避免派遣海军军舰。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执法机构的船释放的政治信号是这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例行的公开的安全活动。第二,执法机构的出场保证了把冲突控制在较低水平,即使船上装备了一些武器。最后,执法船如果离得近,能得到解放军海军军舰的支持,近来南海的几个事例表明了这一点。
由于武装船只和飞机的出现增加,对危机管控协议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一系列的冲突危险事件表明了这一点(见表三)。2014年夏季之后,转折点出现。这年9月,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在青岛举行。这是继2012年5月的首次会议后的第二次会议。双方代表达成共识,“原则同意重新启动两国防务部门早日落实海上联络机制的磋商”。随后,2014年11月,四点共识达成,安倍与习近平在北京会面。这一时间线显示,在关于两国关系更广泛状况的共识正式达成之前,中国决定恢复关于联络机制的谈判。
表三:东海冲突危险和军事事件列表(2013~2015年)
|
日期 |
事件 |
备注 |
|
2013年1月19日 |
一艘中国护卫舰在东海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 |
解放军否认事实,日本军方为保护情报搜集能力而拒绝发布证据 |
|
2013年1月30日 |
一艘中国海军军舰在东海争议岛屿附近用火控雷达锁定一艘日本驱逐舰 |
解放军否认事实,日本军方为保护情报搜集能力而拒绝发布证据 |
|
2014年5月24日 |
日本谴责中国的距日本飞机12米的危险飞行 |
|
|
2014年6月11日 |
在两国防空识别区重叠区域,两架日本f-15战机飞入距中国图-154飞机30米以内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 |
中国国防部发布录像视频,谴责日本“严重影响飞行安全” |
来源:《日本抗议中国船的雷达行为》,bbc新闻,2013年2月5日,www.bbc.com/news/world-asia-21337444(2016年8月4日访问);《日本可能发布数据证实中国雷达事件》,路透社,2013年2月8日,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china-idusbre91801b20130209(2016年8月4日访问);黄瑞黎:《日本抗议中国军机近距离飞掠,中国抨击日本的抗议举动》,路透社,2014年6月12日,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japan-planes-iduskbn0en0l720140612(2016年8月4日访问)。
中国为什么从以对抗和强硬为中心的政策转到重启军事外交?当2014年“四点原则共识”只是模糊地处理了中国为与日本防务部门恢复会谈所设的前提条件时,这一问题值得一问。四点共识不包括日本承认存在主权争端,但包括认识到“围绕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不包括日本承诺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但提到“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可能如同它读起来那样含糊,文件的用语成功化解了中国的敏感;它实际上由中国专家提出,为习近平和安倍晋三领导下的中日关系设置新路径。该文件反映了“创造模糊空间”的政治决定。本文接下来的部分讨论该政治决定的可能原因。
三、中国专家对于和日本开展危机管控的看法
在中国的战略圈里,危机管控是一个比较新的术语。中国传统上把与对手谈判安全事务看成要么是软弱的信号,要么是谋求政治让步的手段。在中国的海域周边,包括东海、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安全事务专家再三推荐危机管控和信任建立,两者也在一轨和二轨级别被频繁讨论,但中国和对手间没有达成约束性协定。在南海,自从2002年中国和东盟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没有取得进展;该宣言不具约束性,假定是为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签署铺平道路。2015年12月,在台湾马英九第二任期非常晚的阶段,在良好政治关系的背景下(新加坡习马会后),在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竞选冲刺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间最终建立了军事热线。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异常紧张的各时期,台湾方面系统性地提出信任建立措施而被北京拒绝,除非台北接受主权方面的重要让步。
在中国,作为安全事务研究院所的一个研究领域,危机管控吸引了一定的注意。江忆恩描述了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军方的关键研究机构(国防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国家安全部(一研究院)主要受它们研究的美国关于同一主题的成果启发,如何开发大量危机管控理论文献的。在塑造中国的危机管控思维上,美中关系危机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要。江忆恩提到,传统的军事战术思维和危机管控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适用于中国,并易于减慢危机管控提倡者的进展。而总的说来,关于和日本的危机管控谈判的有深度的中文出版物极其有限,并且中文里支持该观念的观点甚至更少——尽管两者都存在。
中国的分析人员赞同危机管控机制具有临时性——通过在定义上完全区别于尝试解决危机。主要的分界线涉及他们是否看到通过降低军事事变或局势升级的风险来稳定关系、以防发生意外冲突的价值。对北京的海洋安全专家的采访表明很多人认为事变风险最终与“政治意愿”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有高层的政治决定要避免危险行为,就没有事变。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员倾向于把危机管控和“战略互信”概念联系起来,主张只有后者才为稳定的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危机管控谈判体现了过于微观的方法,只有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互信才能避免军事事变;他把这种论点和民族主义话语结合起来,提出危机管控是西方工具,不适合亚洲国家。和中国智库的定期交流显示,这种思想派别处于支配地位,尽管这是一个定性评估。
一些中国学者表现出不支持和日本开展危机管控。北京大学的初晓波认为,众所周知的汉语词“危机”由汉字“危”和“机”组成,在西方被广泛评论为揭示了中国对待危机的特定方法,实际上却限制了中国的思维,因为大部分学者倾向于仅仅在寻求战略机遇的意义上分析危机。他也提到,没有舆论领袖公开支持危机管控这一观念。
同时,由于出现涉及解放军的近距离接触,中国的危机评估取得进展,使中国一些分析人员认识到与日本之间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例如,中国军方分析人员承认存在四种事变情形:
●领海之外涉及海军、执法机构或渔船的冲突;
●领海之内的冲突;
●个人登岛;
●在争议区域进行的监视和侦察活动引发的军事事变。
关于安全风险水平的认知转变明显是塑造中国在危机管控谈判上的做法的一个因素。然而,第二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认识到能通过谈判获得政治利益。例如,赵通(清华大学)认为,四点共识达成后,危机管控谈判就是逻辑上的下一步。他论述,对于中国而言,危机管控有三个目标:(1)在各自捍卫“实际控制权”的过程中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2)避免重大事故和突发事件引发事态升级;(3)避免在主权和历史问题上的局部性事件对两国关系造成全面性冲击。第一点是最有趣的,因为它显示中国乐意冻结新现状,由此日本将接受中国船在钓鱼岛/尖阁诸岛周围活动,这将等于日本默认共同管理该岛的理念——这是安倍政府非常反对的事。
同样,于铁军(北京大学)观察到中国已在东海成功达到阶段性目标,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存在着主权争议,从而推倒了日本说法的关键内容。在谈判的整个七年中,尽管仍然有待官方确认,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中国在谋求非常具体的外交成果。中国战略圈中一位非常突出的危机管控提倡者张沱生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一点:
●任何一方的人员都不应踏上该岛或进入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定的12海里领海线内;
●双方都应克制,不在岛上从事建造或其他活动;
●在该岛及其周围海域附近,任何一方都不应部署军事设施;
●两国执法船应保持适当距离。
四、中国的选择:政治收益先于军事安全风险
和日本的危机管控谈判失败在一个可预见的问题上,即主权问题和对现状性质的不同理解上——恰恰是要达成切实成果所需要搁置的因素。中方坚持协议适用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12海里区域,日方认为这是要消解日本对该岛实际管理权的深层图谋。中方的要求沿袭了在2012年9月日本公开购买三座岛屿后中国采取的决策模式,所有这些决策导致了对日本在该岛管理权的实际争夺,日本的管理权以前未受到挑战——至少在海上未受到挑战。最终,似乎中国设法为自己在钓鱼岛/尖阁诸岛周围的争议领海巡逻获得更安全的环境——在2008年开始谈判前,自己只是极其个别地在该海域活动。
除了上述核心障碍,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特别是2015年谈判恢复后,日方虽然一直承诺完成谈判,但有两点主要的安全关切,事关机制的有效性。第一点是中国可能利用机制和谈判来“把日本对事变的应对中和掉,使日本军方受约束而采取低于正常比例的响应”。第二点与机制的可持续性及功效有关。在签署协议获得外交收益之后,中国军方会遵守协议的规定吗?机制能幸免于由历史或其他问题所致的两国关系下一次恶化吗?只要机制没有建立,这些就依然是假设性问题,但它们显示了东京对中国军事政策的高度不信任。
总结中国在危机管控谈判上的做法和谈判在中国东海政策中的作用,似乎服务于两个主要目标:
●第一,中国关于危机管控谈判的外交展示了其对于和日本关系状况的总体评估。换句话说,它反映了更大的关切,而不是用来改善总体关系的工具。在2014年夏,似乎北京做出决定来缓解与日本的紧张关系,这导致决定恢复会谈——该决定甚至在四点共识达成之前就已做出。
●第二,在东海的特定情况中,北京描述为单方面破坏原状的日本政府购岛行为发生后,用危机管控谈判来确保新现状。换句话说,中国设法用谈判来巩固已获得的收益——从北京的角度看,这些收益是通过2012年底以来执法机构前所未有的巡逻次数激增获得的。
该分析显示中国在危机管控和信任建立上的做法,极大程度上由寻求政治收益决定,与安全方面的目标没有充分关联;军事事变风险显然不是中国在和日本谈判上总体做法的主要决定因素,也从来没能被个别拿出来作为应被单独处理的独立变量。
(相关简介:杜懋之(mathieu duchtel),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和中国项目副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刊于《神州展望》(china perspectives)杂志2016年第3期,2016年3月14日收稿,2016年8月4日采用;经作者和该杂志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说法,“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很明确,而且我国现在还有效地控制着该诸岛。根本不存在围绕尖阁诸岛必须解决的领有权的问题”。来源:日本外务省网站,“关于尖阁诸岛”,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senkaku(2016年3月11日访问)。
[2]这三座岛屿是南小岛、北小岛和钓鱼岛,以前为栗原家族所有。日本政府购买的目的是将其国有化,以阻止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极端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的类似计划,石原意欲把这三岛并入东京都的行政管辖范围,他解释称,针对中国的声索,日本当局没有充分地保卫“尖阁诸岛”。
[3]国际危机组织:《危险水域:岩礁上的中日关系》,载于《亚洲报告》第245期,2013年4月8日,第12~15页。该报告把反应式强势定义如下:“北京以另一方的行动作为强硬回应的理由,并改变事态以对自己有利。”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