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三是契约的运用在其政治边界内。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运行的,一旦突破这个共同体、将它扩展至更广泛的人群,就可能被侵蚀。在20世纪来临之前,契约关系在民族国家的适用范围,都还是十分有限的,当时真正有公民身份或有选举权的公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率还很小。
契约往往会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坐在“五月号”上来到北美的那些人,具有相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这种同质性是契约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
以民族国家及相关制度为主要表现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充的秩序,而是有其内在限制,此乃民族国家的“初心”。时至今日,原初契约安在?早已被突破了,公民普遍只想着自己的权利而不想付出,民主已演变成民粹主义,国家的政治边界已屡被拓展。
当一种本来有着政治限制的制度设定,被一步步寄予无限的期望时,就如同初始设计可以载重一吨的马车,现在装上了十吨的货物,它还能像以往那样拉得动吗?这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内生之困,也是当前欧洲许多国家乱象丛生的基本成因。
十余年前,在欧盟50岁生日的时候,一些美国报纸曾“隔岸观火”,指出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动大军、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与族群冲突、对共同的欧洲未来缺乏共识,以及欧洲政客在这些问题面前的无能为力等,使欧洲“正在掉进历史的垃圾堆”。心高气傲的欧洲人,曾对此愤愤不平。然而,自2008年西方金融和债务危机以来,每当欧洲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还有多少是关于欧洲的好消息?
最新让欧洲“闹心”的事情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在西班牙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的几番交锋下,后者还是正式宣布独立。西班牙政府、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都纷纷表达了“不同意”。这事情目前已陷入政治僵局,后继发展恐怕不会美妙。而把它与2014年的苏格兰公投、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放到一块,欧洲近几年来,已是“脱”声一片。一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才刚刚联到一起的欧洲,为什么又重新出现了离散化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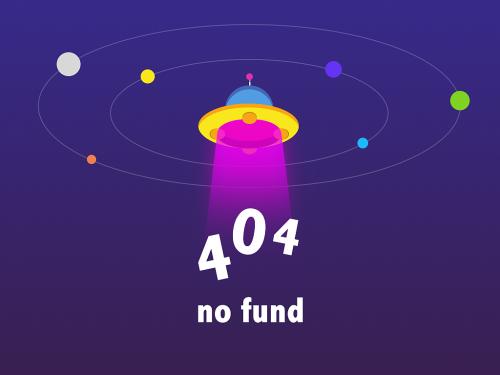
欧洲显然“病”了,而且“病”得不浅。一“脱”了之的背后,主要原因,不外是构成欧盟的一些国家,乃至国家内部的不同构成,对共同的欧洲或各自国家的前景,已经不再抱有期望。“哀莫大于心死”,既然同在一锅未来已没有好饭可吃,那不如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大难临头各自飞”也。
尽管欧洲人还是不愿承认,但欧洲进一步奔向衰败,却是日益明显。欧洲——大而言之是整个西方,为何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不如人意?笔者近年侧重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当前的“西方病”,一是回溯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初心,从中剖解西方“现代性”的制度极限;二是以中国人文传统所重视的道统与治统论,来观察西方国家的道治失衡和政治失败。本文先谈前一个角度,后者另文再述。
“现代性”的概念,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如洪钟大吕,在欧美学者眼中,它是总结近代以来,欧洲文明为什么后来胜出的关键词汇。与“现代”偏重于物质层面不同,“现代性”更多指向近世以来,西方独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整套观念革新与制度重构,它的落实,又表现为欧洲普遍发生由传统的封建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的转变。
封建国家为什么要废除,民族国家是如何发生的?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喜欢从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来寻找“国家理由”启蒙话语所倡导的人性解放、权利平等、自由意志,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引路人”。但曾经经历过英国内战、后来写作了《利维坦》的英国人霍布斯,以及亲身领导了北美独立运动和制宪会议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他们的想法却与此明显不同。
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元勋,当年在推动新国家诞生时,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乃是来自外部的生存威胁和内部的无政府状态。而霍布斯当年所忧心的,则是英国的内部动乱,他在《利维坦》中的一些话,可能会让现在的人们听起来很不悦耳,比如他说:“人们由于读了这些希腊和拉丁著作家的书,所以从小就在自由的虚伪外衣下养成了一种习惯,赞成暴乱,造成肆无忌惮地控制主权者的行为,然而又再控制这些控制者,结果弄得血流成河,所以我可以老实地说一句:任何东西所付出的代价,都不像我们西方世界学习希腊和拉丁文著述所付出的代价那样大”。
霍布斯、华盛顿等人在推动英美两国的民族国家形成时,他们所定义的“现代性”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契约,更接近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本原,其要在于三点:
一是公民美德与国家责任相匹配。这个政治契约是双向的承诺,不只要求国家为民众做些什么,也要求公民为国家做些什么。国家对公民的责任,主要是提供安全保护;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是要以自己的合适行动,维护国家的稳定存在和政治的有效运行。
二是精英治理与民众意愿相协调。民族国家的早期样态,民主并不是主要内容,民众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有限,精英阶层对国家的领导,在反映自身利益、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需要照顾到民众的意愿;而民众则尊重精英治理的现实,服从现有政治安排。
三是契约的运用在其政治边界内。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运行的,一旦突破这个共同体、将它扩展至更广泛的人群,就可能被侵蚀。在20世纪来临之前,契约关系在民族国家的适用范围,都还是十分有限的,当时真正有公民身份或有选举权的公民,在整个人口中占比率还很小。
契约往往会以一定的文化认同为前提。坐在“五月号”上来到北美的那些人,具有相同的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这种同质性是契约能够成立的重要前提。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
以民族国家及相关制度为主要表现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充的秩序,而是有其内在限制,此乃民族国家的“初心”。时至今日,原初契约安在?早已被突破了,公民普遍只想着自己的权利而不想付出,民主已演变成民粹主义,国家的政治边界已屡被拓展。
当一种本来有着政治限制的制度设定,被一步步寄予无限的期望时,就如同初始设计可以载重一吨的马车,现在装上了十吨的货物,它还能像以往那样拉得动吗?这正是西方“现代性”的内生之困,也是当前欧洲许多国家乱象丛生的基本成因。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