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今年除夕,我乘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蒸汽火车,从喜马拉雅山腰的小镇kurseong爬上大吉岭。
山顶酒吧有男女和我搭话,“你从哪里来?”
“班加罗尔”,我脱口而出,出口才反应过来,笑着补了一句“我来自中国,现在住在班加罗尔”。
过去半年,我的生活产生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折叠”——从不停奔跑的中国,到总是慢一拍的印度。从知名的财新,加入在班加罗尔刚刚起步的科技新媒体志象网。
从2015年夏天到财新实习起,我就像踏上了一辆飞速前进但不知终点的列车。财新给了年轻记者最宝贵的快速成长的机会,只要肯付出多努力,实习记者也有做杂志稿甚至封面的机会。
直到带我入门的记者接连离职,我不得不考虑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但当时我也没想过,来自中国十八线县城的甘肃姑娘,会和一群印度人一起,记录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没有天猫超市、支付宝、高铁、美团外卖的日子里,我终于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规则和节奏,不再被人潮推着走,看似跑得快却总是内心惶恐。
但改变也正在发生。来不及买菜时,我会用big basket下单,生鲜蔬菜两小时送到家;偶尔犯懒不想做饭时,我也在zomato或者swiggy点外卖,坐等一大份印式中餐送上门。街边的小店里,也随处可见paytm、谷歌支付、亚马逊支付的二维码,只可惜我没有印度身份证,没法体验一把。
这种局外人的角色,也让我有了再一次去观察科技对生活影响的机会,此前身处其中,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回到过去,带着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科技给人和社会带来的改变,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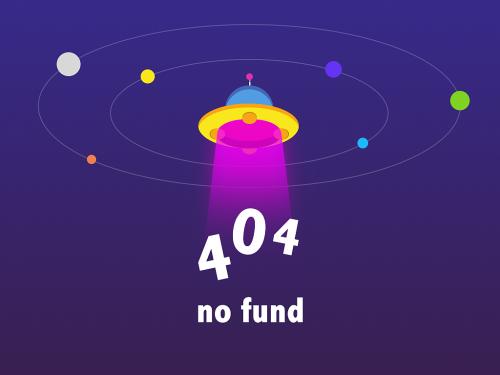
班加罗尔
“印度农村有厕所吗?”
春节后回到老家,有天晚上,和我爸坐在客厅里聊天。他说,自从我去了印度,他经常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一些印度的新闻。然后,他问我,印度是不是像微信说的那样强奸高发、没有厕所?
我拿出1月份去同事p老家玩的照片给他看。
p在班加罗尔长大,但爸妈退休后就回了村里。村子在离班加罗尔250公里外的泰米尔纳德邦。凌晨1点,我们上了火车,四小时后到达,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
到了村里,我终于理解了他之前说的,他父亲为什么退休后不愿再住在班加罗尔。
村口往前走大概五百米,有一片开阔的空地,同事说,他小时候一到晚上,全村的人都会聚在这里看电视。再走进去一点,就是一座的寺庙,寺庙旁边就是他家,一座独栋小院子。
一进门,叔叔开始热情介绍起他的花园。他之前在班加罗尔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了38年,可以流畅地用日常英文交流。
院子里,他种了芒果树、橄榄树、香蕉树、番石榴树,种了辣椒、番茄、茄子、芹菜等蔬菜,还有数不清我没法说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吃完饭,我们经过一片空地的时候,同事突然笑起来,跟我们说这里曾经是村民解决“日常大事”的地方。
在中国热映的印度电影《厕所英雄》里,印度人对“洁净”的概念与中国人有着天壤之别,大小便解决在家里,这无法接受,就释放在大自然之中。也因此,男性、女性、小孩子往往有着各自约定俗成时间段,女性最早,在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结对去上厕所,小孩子则一般在上学之前。
两位印度男同事还调侃我,明天要早起了。
再往前走一段,是一间看上去已经不再使用的房子。同事说,这是大概4年前政府给村里建的公共厕所。“因为刚开始村民都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里,所以就只能在村里建公共厕所。”他说。
但两三年前,村民慢慢开始在自己家里建厕所,慢慢的,公共厕所也就被弃之不用了。
现在,同事家里不仅有马桶,还有空调和热水器。每天早上,都会有卡车开进村里,兜售新鲜蔬菜,“现在什么都有啦。”叔叔解释。
当然,这无法代表整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整个印度来说,也是比较富裕和发展得比较好的,同事一家更是村里备受尊敬的家庭。
跟我们一起去的另一个同事a,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子里,比哈尔是印度相对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地区,情况就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尽相同。
他告诉我,尽管政府给每户村民都发放建厕所的补贴,但还是有些村民就是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他们就是喜欢在开放的地方解决,哈哈。”但因为政府派人检查禁止露天方便,他估计,他的村子里有厕所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我爸听完,紧锁的眉头也并没有解开,他叹了一口气,说,“还不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泥腿子出身的我爸,自己就是从农村里长大的,在考上警察学校之前,他还在家里干了一年的农活。即便是到现在,他也是四兄弟里唯一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
而我是家里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读了硕士的小孩。上大学后,所有人都觉得我要“有大出息”。但可惜我一直都在选择做一个少数派:从法学转投新闻、从顶尖的媒体辞职、又来了印度。
回到村里看爷爷奶奶那天,我第一次不再抗拒他们的嘘寒问暖,我坐在爷爷旁边,他问我在印度的生活,还问了一个让我忍俊不禁的问题。他说,“印度人是不是都只活到三四十岁啊?”
我笑了一下,又给他看了我们在村里和同事的爸爸妈妈拍的照片。
在照片里,叔叔露出了和善的微笑,阿姨依旧一脸严肃——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女孩,在她家里制造了太多意外:想在屋顶睡帐篷、不顾她劝阻骑着踏板车出门、还把穿着纱丽下面的小背心走出了卧室,我能感觉到她的不悦,但当我们围坐在她身边时,还是拍到了一张好照片。
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一大早,我赶到南苑机场飞回去。这条航线去年才开,飞机上有很多第一次坐飞机的家乡人。在他们拿出手机拍飞机的时候,我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他们让我想起了熟悉的印度人。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熟悉”有多自然。
回家的第二天,我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过两年再看吧。”我敷衍道。
十八岁离家去武汉读书之后,“家”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毕业之初,“家”是北京那一间15平米的出租屋。而现在,五千公里之外德干高原上那座曾经的“花园之城”更让我有归属感。
11月底回国一周,深夜返回班加罗尔,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了小区门口的餐馆里,点了一个masala dosa,“finally it feels like home”,我在instagram上说。
这次回国也才几天,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去。
和印度同事出去采访的时候,每次到堵车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们讲“曾经的班加罗尔”——没有堵车、草木芬芳、四季宜人的地方。随着软件外包巨头infosys和wipro的崛起,班加罗尔逐渐成为了it之城,再乘着21世纪这一股创业的春风,它又转身成为了创业之都。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曾经独立芬芳的小城,城市在林木花园中杂乱无章地开始生长,它不再是本地人眼中的那个班城。
但它于我而言已经足够可爱。
我住的小区靠近班加罗尔繁华的商业区indiranagar,早在上世纪末就被开发成了住宅区和办公楼。小区的住宅楼围成了一圈,中间有草坪、泳池,还有几十棵基本上跟五六层一样高的树。
生长在北方的我叫不上树的名字,周末的午后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或者坐在草坪上看会书,那些树都是我最沉默的好友。
杂乱也是可爱的。办公室离小区走路大概十分钟,我一般走外面靠马路的一条路,走多了,路边小店里的小哥看到我都会说morning,隔三差五还会碰到一个帅哥在路上遛狗。那天赶时间换了另一个方向的一条小路,一棵开满了粉色花朵的树突然凭空出现,惊艳之余,我才意识到班城的春天到了。
不管班加罗尔在本地人眼里经历了怎样的疯狂扩张,从北京搬过去的我还是觉得它有着小城的可爱。我无需坐两小时的地铁,突突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朋友家,路边到处都是卖小吃的,街角还有一家裁缝店。
二月初从班加罗尔离开的那天,雨季未到,它却下起了雨。
去年九月刚到班加罗尔的时候,正巧是雨季的最后一个月,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急促又轻盈的雨滴总会准时到来,半小时结束,留下空气中的草木香气。
今年的雨季不远了。
“印度人约会吗?”
在我缺席的这个春节,弟弟的婚礼成了家里最热门的话题。他年前刚订婚,计划在夏天办婚礼。在聊完弟弟的婚礼之后,人们也会将话题转移到我的身上。
一位叔叔问我,“印度人是不是很早结婚、生很多个孩子呀?”
在探探和blued进军印度市场的时候,一位中国的互联网人也在中印互联网创业群里提起这个话题,半开玩笑地问,“但是印度人约会吗?”“他们只跟自己的另一半出去吧?”
群里除了我,还有我的室友、印度女同事b。去往办公室的路上,我俩聊了聊这件事。她觉得又气又好笑,没想到在印度待过一年多的中国人,居然还对印度有着这样的印象。
她长我几岁,也没有结婚,在德里长大,之前在班加罗尔读书。我俩在九月初的同一天到的班加罗尔,共享一间大的空旷的公寓,一见就觉得特别投缘。
她有一个谈了多年的男友,也在德里做记者,是报道杀人放火的法治记者。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一直分分合合。在那间偌大的公寓里,我们分享彼此的心事,聊年龄增长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上带来的改变,做记者的自由与孤独,夜风微凉,我们坐在阳台上,低声细语都随着烟云飘走。
前段时间,她告诉我她想结婚了,想拥有自己的小家,一个稳定的陪伴。男友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她开始尝试跟朋友的朋友见面,寻找新的可能性。“我还挺开心的!虽然遇到的惊吓比惊喜还要多。”她鼓励我多尝试,不要很早就把自己的未来与某一个人绑定。
她还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们隔三差五就会约别的同事,晚上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临近午夜时分,她提议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三个人出门做了一辆突突车,到了indiranagar的一个冰激凌店。
我们点了冰激凌坐在店外的长椅上,看着店里坐的一对对情侣,亲密地低声细语。我和她相视一笑,“印度人约会吗?”
不可否认,我所接触的印度非常有限,身边能聊的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但随着印度的飞速城市化,这一人群也正在迅速壮大。我问朋友印度自由恋爱的比例,得到的答案都是“很少”,但在大城市,“先恋爱再安排”的类型越来越多。
我在indiranagar的酒吧区见过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女生,也在小镇见过身着黑袍坐在摩托车上,与丈夫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妻子。
不过,印度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中国要明显得多。
有天,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炙热》,其中一位女主角去邻村给自己的儿子找对象,儿子给妈妈打电话说,“你最好保证她很漂亮,不然你告诉她们家我可是要退货的!”
“退货”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问朋友是不是还有这么极端的情况存在。他说是的,在极少的地方。
有已婚同事曾问过我,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未婚同居很普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很惊讶。他和妻子是先结婚后恋爱,是纯粹的包办婚姻。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因为自由恋爱不被接受,结婚反倒成为了恋爱的前置条件。
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听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结局有喜有悲,但往往都因为外在阻力而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
有人和相识七八年的好朋友谈了恋爱,跨越宗教阻隔结为伴侣,两个人生活在班加罗尔,养了两只猫。还有一对跨宗教结为伴侣,他们的故事更是波折,女生跟大学男友登记结婚,等到确认信送到家里父母才知情,此后的十余年断绝往来,等到小孩出生才逐渐解冻。
还有一位朋友,跟大学女友谈了四年的恋爱,对方生在跨种姓家庭,女孩子似白纸一张,对种姓阻隔毫无概念,但男生家庭却坚决不同意,漫长的纠葛之后,两人黯然分手。
事情已经过去近五年,男生提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过。
在回国前,我还听说了有父母因为孩子自由恋爱而自杀的坏消息,更让我沮丧的是,父母并不是以此为要挟,而是真的觉得无颜面对周遭的非议。
这种“同侪压力”也出现在我爸妈的身上。有一次我爸跟我说,身边的朋友都有孙子带,他感觉自己像“一条孤独的老狗”。
幸而我还有个弟弟,今年正月十五,他和长他五岁的女友领了结婚证。父母的反对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几乎匿迹,他选择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接棒给我爸妈上了一堂放手教育课。
到班加罗尔的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还有另外一个女同事,坐在公寓的地板上边吃饭边聊天。她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自然聊起了学校,和学校里受欢迎的男同学。
我问她会有来自父母逼婚的压力吗,她说当然有,但也已经过了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前两年他们催得比较紧,看我无动于衷,现在也就不太说了。”她说。
“那他们希望你出去约会吗?”
“约会……他们希望我和那种’结婚备选对象’约会,而不是随便约会。”她冲我眨了眨眼。
“印度的记者什么样啊?”
从家里再回到北京,和之前的朋友见面聊了聊近况。他们基本上都还在国内的主流媒体做记者,奔跑在突发新闻的一线。
其中一位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学,有来自印度、日本、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同事。我们聊起了“外媒记者”。
她告诉我,一次大家讨论“该不该把直接引语给采访对象看”的问题,有几个记者寸步不移地坚持这是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是“没做好自己的分内之责,让采访对象来替自己做功课”。
“印度的记者和从业环境怎么样啊?”她问我。
在印度与同事朝夕相处的半年,我们有过数不清开怀大笑的时刻,唯一真的红过脸争吵过的问题就是新闻操作准则上的分歧。
去年十月,有一行二十多人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来印度考察市场,其中一个行程是拜访某国际风投公司的印度合伙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合伙人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分析了当时印度创投圈的焦点事件,说数据本地化是印度创业者为了避免竞争搞事情,说方言平台可能对facebook印度社交巨头的地位发起实质性的挑战。
除了我之外,当时还有印度的主编和另一位同事在场。
这些对记者来说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态,我们想整理成采访发布,对方公关部婉拒了,称事先并未知悉内容将作为采访,此时不便对外发声。
主编当即大为光火。当时我和他坐着突突车,在去往另一次采访的路上,因为这件事越吵声音越大,到了目的地才被迫消停,谁也没能说服谁。
“我们是一家媒体,他当时也知道有记者在场,既然觉得不便公开发声,那为什么当时要说这些话呢?”
“你说是这么说,但你应该也很清楚他当时能那么坦诚,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从中国来的创业者,而不是记者吧?”
“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事实,我们都有录音,我们也不需要他同意。”
“你说的没错。但我们作为媒体,也是需要维护采访对象的关系的呀。为了发这一次稿子,如果因此失去了一个采访对象,有必要吗?”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我有个好故事,我为什么不能发?”
“为了建立更长期的关系呀。”
“在印度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永远只会选择对大的媒体发声,同样一件事,我告诉《经济时报》可以到达更多的读者,我为什么告诉你?”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印度的媒体格局与美国类似,大媒体都由财团掌控,是自负盈亏的生意,媒体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候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搞个大新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印度的公司也更主动地去掌控舆论的主动权,大多都很愿意对外发声。
而中国公司却截然不同。很多时候,愿意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员工,给中国负责海外业务部门发的采访请求经常没有回应。
甚至有几次,在我们的稿子做完之后,中国公司那边又找上门来要求不发甚至撤稿。理由五花八门,印度员工未得到授权,印度员工不了解核心信息说的并不准确,信息对外披露将影响竞争。
一次对方公关找上门,甚至问我,是否给接受我采访的印度员工付了钱。还暗示我,他们可能会因为接受我的采访而工作不保。
“那就再写一篇稿子报道他们随便开人呀。”这样的事情三番两次地发生,印度同事开始调侃这是“typical chinese”。
我想曲线救国。撤稿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信源力所能及地做到了平衡,中国公司自己不发声是你们的事,现在既然觉得信息不准确,那不如争取一下你们更高层的人出来发声的机会。至少建立一个联系,而不是保持对立。
同事将信将疑。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第一次有一个媒体,是有来自两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在日常的相处里,在笑声和争吵中,逐渐突破强加在对方身上的刻板印象。
你会有心理落差吗?
我带着满身风尘和被晒伤的脸,还有一箩筐的好故事,见到了老朋友。“你看起来比之前开心多了耶!”仿佛小女孩揣在兜里的糖果被发现,却乐于跟大家分享。他们没有担心我吃得习不习惯,住得好不好,而是关心我快不快乐。
之前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一家公司的公关问我,“你从财新出来,会有心理落差吗?”
和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同事胡剑龙也问了我类似的问题。我当时没怎么犹豫,对我而言这份经历早就不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我也换了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
说遗憾是有的。毕业的时候,我的打算是在一个装备齐整的新闻编辑室干三年,打磨自己最基本的记者功底,也更直接地理解中国。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离开,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完全合格的记者。
开会的时候,我用英文说了一大段,非母语表达反而让我更自如地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在当时的我看来,留在北京做记者,在一个又一个机构之间跳来跳去,吐槽雾霾地铁和房价却束手无策,不是我十年后想成为的自己。
而且,他描述的愿景和正在尝试的努力,确实“忽悠”到了我。
作为一个人口与中国旗鼓相当、又国土相邻的大国,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确实少得可怜。在阿里、腾讯、头条、滴滴都把印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一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前赴后继飞往南亚次大陆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却很少听到来自印度的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中国也成为了包括印度在内新兴国家的标杆。中国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市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印度的年轻创业者和投资人们对这些信息求之若渴,却总觉得不足够。
前几天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投资人找到我,跟我聊了二十分钟的中国在线音频市场,他们想在印度投类似的项目。
聊完觉得开心,好像之前一直在想象的“bigger picture”突然落到了实处,希望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每周约两个投资人或者创业者见面,也收获了诸多惊喜,这位投资人就是其中之一。采访之前,我略微紧张,他见到我就开始问我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自然得聊了起来。
印度也彻底地治愈了我的轻微社交恐惧,一个人忙里偷闲地走了很多个地方,见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神奇的是,班加罗尔却始终如影随形。
春节假期在大吉岭,碰到一个在班加罗尔工作的人,聊了一下,是一位it工程师;之后到了斯里兰卡,半夜在青旅的阳台看月亮,旁边坐的男生说他也从班加罗尔来,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在外面碰到从班加罗尔来的人,一半可能是it工程师,另一半可能就是创业的。
班加罗尔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在印度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你是韩国人吗?”“你是日本人吗?”在他们眼里,一个中国的年轻女孩子一个人在印度,仍然是一件稀奇事。
但就是在这个很多人都为安全担忧的国家,我却尝试了很多之前想做都不敢做的事。在科钦海边的公路上,第一次骑摩托车的我把车开到了80公里,被我甩在身后的叔叔还对我按喇叭示意。
在pondicheery的海边,不会游泳的我慢慢朝着浪花往里走,让海浪温柔地扑进我的怀里,从此克服了对海的恐惧。
跨年夜,我在班加罗尔郊外的村子里,围着篝火坐,听一个欧洲小国的男生唱《加州旅馆》,看过午夜的烟火,在树上的帐篷里入眠。
这是我在北京从未感觉过的温柔。
在北京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关于残障人士的报道,他们大多活在暗处,抱团取暖。一天晚上,在班加罗尔的一个小公园里,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幕。
一个看上去是七八岁的小男孩腿脚不便,战战巍巍地小步向前挪动,他的妈妈站在两步开外的地方,轻声对他说着什么。我请身边的朋友为我翻译,她说的是,“不用怕,慢慢来,你不会摔倒的。摔倒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再站起来的。”
在班加罗尔,我也像这个男孩一样,努力克服对广阔世界欠缺的想象力。在异乡,我终于找到治愈的机会,重新赋予生活意义和快乐。
今年除夕,我乘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蒸汽火车,从喜马拉雅山腰的小镇kurseong爬上大吉岭。
山顶酒吧有男女和我搭话,“你从哪里来?”
“班加罗尔”,我脱口而出,出口才反应过来,笑着补了一句“我来自中国,现在住在班加罗尔”。
过去半年,我的生活产生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折叠”——从不停奔跑的中国,到总是慢一拍的印度。从知名的财新,加入在班加罗尔刚刚起步的科技新媒体志象网。
从2015年夏天到财新实习起,我就像踏上了一辆飞速前进但不知终点的列车。财新给了年轻记者最宝贵的快速成长的机会,只要肯付出多努力,实习记者也有做杂志稿甚至封面的机会。
直到带我入门的记者接连离职,我不得不考虑生活的其他可能性。但当时我也没想过,来自中国十八线县城的甘肃姑娘,会和一群印度人一起,记录在两个大国之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没有天猫超市、支付宝、高铁、美团外卖的日子里,我终于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生活的规则和节奏,不再被人潮推着走,看似跑得快却总是内心惶恐。
但改变也正在发生。来不及买菜时,我会用big basket下单,生鲜蔬菜两小时送到家;偶尔犯懒不想做饭时,我也在zomato或者swiggy点外卖,坐等一大份印式中餐送上门。街边的小店里,也随处可见paytm、谷歌支付、亚马逊支付的二维码,只可惜我没有印度身份证,没法体验一把。
这种局外人的角色,也让我有了再一次去观察科技对生活影响的机会,此前身处其中,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
回到过去,带着眼睛和耳朵去感受科技给人和社会带来的改变,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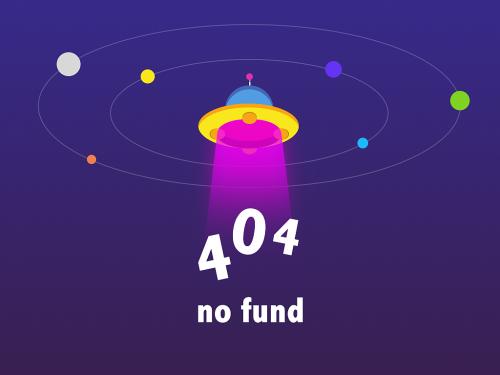
班加罗尔
“印度农村有厕所吗?”
春节后回到老家,有天晚上,和我爸坐在客厅里聊天。他说,自从我去了印度,他经常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一些印度的新闻。然后,他问我,印度是不是像微信说的那样强奸高发、没有厕所?
我拿出1月份去同事p老家玩的照片给他看。
p在班加罗尔长大,但爸妈退休后就回了村里。村子在离班加罗尔250公里外的泰米尔纳德邦。凌晨1点,我们上了火车,四小时后到达,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
到了村里,我终于理解了他之前说的,他父亲为什么退休后不愿再住在班加罗尔。
村口往前走大概五百米,有一片开阔的空地,同事说,他小时候一到晚上,全村的人都会聚在这里看电视。再走进去一点,就是一座的寺庙,寺庙旁边就是他家,一座独栋小院子。
一进门,叔叔开始热情介绍起他的花园。他之前在班加罗尔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了38年,可以流畅地用日常英文交流。
院子里,他种了芒果树、橄榄树、香蕉树、番石榴树,种了辣椒、番茄、茄子、芹菜等蔬菜,还有数不清我没法说出名字的花花草草。
吃完饭,我们经过一片空地的时候,同事突然笑起来,跟我们说这里曾经是村民解决“日常大事”的地方。
在中国热映的印度电影《厕所英雄》里,印度人对“洁净”的概念与中国人有着天壤之别,大小便解决在家里,这无法接受,就释放在大自然之中。也因此,男性、女性、小孩子往往有着各自约定俗成时间段,女性最早,在凌晨三四点就要起床结对去上厕所,小孩子则一般在上学之前。
两位印度男同事还调侃我,明天要早起了。
再往前走一段,是一间看上去已经不再使用的房子。同事说,这是大概4年前政府给村里建的公共厕所。“因为刚开始村民都不愿意把厕所建在自己家里,所以就只能在村里建公共厕所。”他说。
但两三年前,村民慢慢开始在自己家里建厕所,慢慢的,公共厕所也就被弃之不用了。
现在,同事家里不仅有马桶,还有空调和热水器。每天早上,都会有卡车开进村里,兜售新鲜蔬菜,“现在什么都有啦。”叔叔解释。
当然,这无法代表整个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在整个印度来说,也是比较富裕和发展得比较好的,同事一家更是村里备受尊敬的家庭。
跟我们一起去的另一个同事a,出生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一个村子里,比哈尔是印度相对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地区,情况就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尽相同。
他告诉我,尽管政府给每户村民都发放建厕所的补贴,但还是有些村民就是不愿意在家里建厕所,“他们就是喜欢在开放的地方解决,哈哈。”但因为政府派人检查禁止露天方便,他估计,他的村子里有厕所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我爸听完,紧锁的眉头也并没有解开,他叹了一口气,说,“还不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
泥腿子出身的我爸,自己就是从农村里长大的,在考上警察学校之前,他还在家里干了一年的农活。即便是到现在,他也是四兄弟里唯一一个“有稳定工作”的人。
而我是家里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读了硕士的小孩。上大学后,所有人都觉得我要“有大出息”。但可惜我一直都在选择做一个少数派:从法学转投新闻、从顶尖的媒体辞职、又来了印度。
回到村里看爷爷奶奶那天,我第一次不再抗拒他们的嘘寒问暖,我坐在爷爷旁边,他问我在印度的生活,还问了一个让我忍俊不禁的问题。他说,“印度人是不是都只活到三四十岁啊?”
我笑了一下,又给他看了我们在村里和同事的爸爸妈妈拍的照片。
在照片里,叔叔露出了和善的微笑,阿姨依旧一脸严肃——我这个突如其来的中国女孩,在她家里制造了太多意外:想在屋顶睡帐篷、不顾她劝阻骑着踏板车出门、还把穿着纱丽下面的小背心走出了卧室,我能感觉到她的不悦,但当我们围坐在她身边时,还是拍到了一张好照片。
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一大早,我赶到南苑机场飞回去。这条航线去年才开,飞机上有很多第一次坐飞机的家乡人。在他们拿出手机拍飞机的时候,我拿出手机拍下了他们,他们让我想起了熟悉的印度人。
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熟悉”有多自然。
回家的第二天,我妈小心翼翼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结束流浪?”
“过两年再看吧。”我敷衍道。
十八岁离家去武汉读书之后,“家”的概念一直在变化。毕业之初,“家”是北京那一间15平米的出租屋。而现在,五千公里之外德干高原上那座曾经的“花园之城”更让我有归属感。
11月底回国一周,深夜返回班加罗尔,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了小区门口的餐馆里,点了一个masala dosa,“finally it feels like home”,我在instagram上说。
这次回国也才几天,我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回去。
和印度同事出去采访的时候,每次到堵车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他们讲“曾经的班加罗尔”——没有堵车、草木芬芳、四季宜人的地方。随着软件外包巨头infosys和wipro的崛起,班加罗尔逐渐成为了it之城,再乘着21世纪这一股创业的春风,它又转身成为了创业之都。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了曾经独立芬芳的小城,城市在林木花园中杂乱无章地开始生长,它不再是本地人眼中的那个班城。
但它于我而言已经足够可爱。
我住的小区靠近班加罗尔繁华的商业区indiranagar,早在上世纪末就被开发成了住宅区和办公楼。小区的住宅楼围成了一圈,中间有草坪、泳池,还有几十棵基本上跟五六层一样高的树。
生长在北方的我叫不上树的名字,周末的午后搬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或者坐在草坪上看会书,那些树都是我最沉默的好友。
杂乱也是可爱的。办公室离小区走路大概十分钟,我一般走外面靠马路的一条路,走多了,路边小店里的小哥看到我都会说morning,隔三差五还会碰到一个帅哥在路上遛狗。那天赶时间换了另一个方向的一条小路,一棵开满了粉色花朵的树突然凭空出现,惊艳之余,我才意识到班城的春天到了。
不管班加罗尔在本地人眼里经历了怎样的疯狂扩张,从北京搬过去的我还是觉得它有着小城的可爱。我无需坐两小时的地铁,突突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朋友家,路边到处都是卖小吃的,街角还有一家裁缝店。
二月初从班加罗尔离开的那天,雨季未到,它却下起了雨。
去年九月刚到班加罗尔的时候,正巧是雨季的最后一个月,每天下午五点左右,急促又轻盈的雨滴总会准时到来,半小时结束,留下空气中的草木香气。
今年的雨季不远了。
“印度人约会吗?”
在我缺席的这个春节,弟弟的婚礼成了家里最热门的话题。他年前刚订婚,计划在夏天办婚礼。在聊完弟弟的婚礼之后,人们也会将话题转移到我的身上。
一位叔叔问我,“印度人是不是很早结婚、生很多个孩子呀?”
在探探和blued进军印度市场的时候,一位中国的互联网人也在中印互联网创业群里提起这个话题,半开玩笑地问,“但是印度人约会吗?”“他们只跟自己的另一半出去吧?”
群里除了我,还有我的室友、印度女同事b。去往办公室的路上,我俩聊了聊这件事。她觉得又气又好笑,没想到在印度待过一年多的中国人,居然还对印度有着这样的印象。
她长我几岁,也没有结婚,在德里长大,之前在班加罗尔读书。我俩在九月初的同一天到的班加罗尔,共享一间大的空旷的公寓,一见就觉得特别投缘。
她有一个谈了多年的男友,也在德里做记者,是报道杀人放火的法治记者。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一直分分合合。在那间偌大的公寓里,我们分享彼此的心事,聊年龄增长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上带来的改变,做记者的自由与孤独,夜风微凉,我们坐在阳台上,低声细语都随着烟云飘走。
前段时间,她告诉我她想结婚了,想拥有自己的小家,一个稳定的陪伴。男友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她开始尝试跟朋友的朋友见面,寻找新的可能性。“我还挺开心的!虽然遇到的惊吓比惊喜还要多。”她鼓励我多尝试,不要很早就把自己的未来与某一个人绑定。
她还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们隔三差五就会约别的同事,晚上来家里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晚上,我们喝了点酒,临近午夜时分,她提议想吃冰激凌。于是我们三个人出门做了一辆突突车,到了indiranagar的一个冰激凌店。
我们点了冰激凌坐在店外的长椅上,看着店里坐的一对对情侣,亲密地低声细语。我和她相视一笑,“印度人约会吗?”
不可否认,我所接触的印度非常有限,身边能聊的朋友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但随着印度的飞速城市化,这一人群也正在迅速壮大。我问朋友印度自由恋爱的比例,得到的答案都是“很少”,但在大城市,“先恋爱再安排”的类型越来越多。
我在indiranagar的酒吧区见过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女生,也在小镇见过身着黑袍坐在摩托车上,与丈夫没有任何肢体接触的妻子。
不过,印度的传统仍根深蒂固,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比中国要明显得多。
有天,和朋友一起看电影《炙热》,其中一位女主角去邻村给自己的儿子找对象,儿子给妈妈打电话说,“你最好保证她很漂亮,不然你告诉她们家我可是要退货的!”
“退货”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问朋友是不是还有这么极端的情况存在。他说是的,在极少的地方。
有已婚同事曾问过我,中国的大城市是不是未婚同居很普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后,他很惊讶。他和妻子是先结婚后恋爱,是纯粹的包办婚姻。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因为自由恋爱不被接受,结婚反倒成为了恋爱的前置条件。
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听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结局有喜有悲,但往往都因为外在阻力而焕发出不一样的色彩。
有人和相识七八年的好朋友谈了恋爱,跨越宗教阻隔结为伴侣,两个人生活在班加罗尔,养了两只猫。还有一对跨宗教结为伴侣,他们的故事更是波折,女生跟大学男友登记结婚,等到确认信送到家里父母才知情,此后的十余年断绝往来,等到小孩出生才逐渐解冻。
还有一位朋友,跟大学女友谈了四年的恋爱,对方生在跨种姓家庭,女孩子似白纸一张,对种姓阻隔毫无概念,但男生家庭却坚决不同意,漫长的纠葛之后,两人黯然分手。
事情已经过去近五年,男生提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过。
在回国前,我还听说了有父母因为孩子自由恋爱而自杀的坏消息,更让我沮丧的是,父母并不是以此为要挟,而是真的觉得无颜面对周遭的非议。
这种“同侪压力”也出现在我爸妈的身上。有一次我爸跟我说,身边的朋友都有孙子带,他感觉自己像“一条孤独的老狗”。
幸而我还有个弟弟,今年正月十五,他和长他五岁的女友领了结婚证。父母的反对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几乎匿迹,他选择了自己的另一半,也接棒给我爸妈上了一堂放手教育课。
到班加罗尔的第三天晚上,我和她还有另外一个女同事,坐在公寓的地板上边吃饭边聊天。她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自然聊起了学校,和学校里受欢迎的男同学。
我问她会有来自父母逼婚的压力吗,她说当然有,但也已经过了最剑拔弩张的时候。“前两年他们催得比较紧,看我无动于衷,现在也就不太说了。”她说。
“那他们希望你出去约会吗?”
“约会……他们希望我和那种’结婚备选对象’约会,而不是随便约会。”她冲我眨了眨眼。
“印度的记者什么样啊?”
从家里再回到北京,和之前的朋友见面聊了聊近况。他们基本上都还在国内的主流媒体做记者,奔跑在突发新闻的一线。
其中一位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学,有来自印度、日本、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同事。我们聊起了“外媒记者”。
她告诉我,一次大家讨论“该不该把直接引语给采访对象看”的问题,有几个记者寸步不移地坚持这是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是“没做好自己的分内之责,让采访对象来替自己做功课”。
“印度的记者和从业环境怎么样啊?”她问我。
在印度与同事朝夕相处的半年,我们有过数不清开怀大笑的时刻,唯一真的红过脸争吵过的问题就是新闻操作准则上的分歧。
去年十月,有一行二十多人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来印度考察市场,其中一个行程是拜访某国际风投公司的印度合伙人。面对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合伙人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分析了当时印度创投圈的焦点事件,说数据本地化是印度创业者为了避免竞争搞事情,说方言平台可能对facebook印度社交巨头的地位发起实质性的挑战。
除了我之外,当时还有印度的主编和另一位同事在场。
这些对记者来说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态,我们想整理成采访发布,对方公关部婉拒了,称事先并未知悉内容将作为采访,此时不便对外发声。
主编当即大为光火。当时我和他坐着突突车,在去往另一次采访的路上,因为这件事越吵声音越大,到了目的地才被迫消停,谁也没能说服谁。
“我们是一家媒体,他当时也知道有记者在场,既然觉得不便公开发声,那为什么当时要说这些话呢?”
“你说是这么说,但你应该也很清楚他当时能那么坦诚,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从中国来的创业者,而不是记者吧?”
“他说的那些话都是事实,我们都有录音,我们也不需要他同意。”
“你说的没错。但我们作为媒体,也是需要维护采访对象的关系的呀。为了发这一次稿子,如果因此失去了一个采访对象,有必要吗?”
“这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我有个好故事,我为什么不能发?”
“为了建立更长期的关系呀。”
“在印度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永远只会选择对大的媒体发声,同样一件事,我告诉《经济时报》可以到达更多的读者,我为什么告诉你?”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印度的媒体格局与美国类似,大媒体都由财团掌控,是自负盈亏的生意,媒体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候一点风吹草动就要“搞个大新闻”。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印度的公司也更主动地去掌控舆论的主动权,大多都很愿意对外发声。
而中国公司却截然不同。很多时候,愿意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国公司在印度的员工,给中国负责海外业务部门发的采访请求经常没有回应。
甚至有几次,在我们的稿子做完之后,中国公司那边又找上门来要求不发甚至撤稿。理由五花八门,印度员工未得到授权,印度员工不了解核心信息说的并不准确,信息对外披露将影响竞争。
一次对方公关找上门,甚至问我,是否给接受我采访的印度员工付了钱。还暗示我,他们可能会因为接受我的采访而工作不保。
“那就再写一篇稿子报道他们随便开人呀。”这样的事情三番两次地发生,印度同事开始调侃这是“typical chinese”。
我想曲线救国。撤稿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信源力所能及地做到了平衡,中国公司自己不发声是你们的事,现在既然觉得信息不准确,那不如争取一下你们更高层的人出来发声的机会。至少建立一个联系,而不是保持对立。
同事将信将疑。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第一次有一个媒体,是有来自两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在日常的相处里,在笑声和争吵中,逐渐突破强加在对方身上的刻板印象。
你会有心理落差吗?
我带着满身风尘和被晒伤的脸,还有一箩筐的好故事,见到了老朋友。“你看起来比之前开心多了耶!”仿佛小女孩揣在兜里的糖果被发现,却乐于跟大家分享。他们没有担心我吃得习不习惯,住得好不好,而是关心我快不快乐。
之前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一家公司的公关问我,“你从财新出来,会有心理落差吗?”
和团队一起开会的时候,同事胡剑龙也问了我类似的问题。我当时没怎么犹豫,对我而言这份经历早就不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地方生活,我也换了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
说遗憾是有的。毕业的时候,我的打算是在一个装备齐整的新闻编辑室干三年,打磨自己最基本的记者功底,也更直接地理解中国。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离开,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有成长为一个完全合格的记者。
开会的时候,我用英文说了一大段,非母语表达反而让我更自如地说出了最真实的想法。在当时的我看来,留在北京做记者,在一个又一个机构之间跳来跳去,吐槽雾霾地铁和房价却束手无策,不是我十年后想成为的自己。
而且,他描述的愿景和正在尝试的努力,确实“忽悠”到了我。
作为一个人口与中国旗鼓相当、又国土相邻的大国,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印度的了解确实少得可怜。在阿里、腾讯、头条、滴滴都把印度作为国际化的重要一站,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前赴后继飞往南亚次大陆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却很少听到来自印度的声音。
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中国也成为了包括印度在内新兴国家的标杆。中国在发生什么,中国的市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印度的年轻创业者和投资人们对这些信息求之若渴,却总觉得不足够。
前几天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印度的投资人找到我,跟我聊了二十分钟的中国在线音频市场,他们想在印度投类似的项目。
聊完觉得开心,好像之前一直在想象的“bigger picture”突然落到了实处,希望成为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班加罗尔的时候,我强迫自己每周约两个投资人或者创业者见面,也收获了诸多惊喜,这位投资人就是其中之一。采访之前,我略微紧张,他见到我就开始问我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自然得聊了起来。
印度也彻底地治愈了我的轻微社交恐惧,一个人忙里偷闲地走了很多个地方,见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神奇的是,班加罗尔却始终如影随形。
春节假期在大吉岭,碰到一个在班加罗尔工作的人,聊了一下,是一位it工程师;之后到了斯里兰卡,半夜在青旅的阳台看月亮,旁边坐的男生说他也从班加罗尔来,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在外面碰到从班加罗尔来的人,一半可能是it工程师,另一半可能就是创业的。
班加罗尔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在印度的时候,总有人会问我,“你是韩国人吗?”“你是日本人吗?”在他们眼里,一个中国的年轻女孩子一个人在印度,仍然是一件稀奇事。
但就是在这个很多人都为安全担忧的国家,我却尝试了很多之前想做都不敢做的事。在科钦海边的公路上,第一次骑摩托车的我把车开到了80公里,被我甩在身后的叔叔还对我按喇叭示意。
在pondicheery的海边,不会游泳的我慢慢朝着浪花往里走,让海浪温柔地扑进我的怀里,从此克服了对海的恐惧。
跨年夜,我在班加罗尔郊外的村子里,围着篝火坐,听一个欧洲小国的男生唱《加州旅馆》,看过午夜的烟火,在树上的帐篷里入眠。
这是我在北京从未感觉过的温柔。
在北京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关于残障人士的报道,他们大多活在暗处,抱团取暖。一天晚上,在班加罗尔的一个小公园里,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幕。
一个看上去是七八岁的小男孩腿脚不便,战战巍巍地小步向前挪动,他的妈妈站在两步开外的地方,轻声对他说着什么。我请身边的朋友为我翻译,她说的是,“不用怕,慢慢来,你不会摔倒的。摔倒了也没关系,你可以再站起来的。”
在班加罗尔,我也像这个男孩一样,努力克服对广阔世界欠缺的想象力。在异乡,我终于找到治愈的机会,重新赋予生活意义和快乐。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