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摘要:作为以巴冲突的纠结点之一,犹太定居点的建设的动力来自于犹太教、希伯来语和政治三者互动。希伯来语和与定居点所在土地直接相连的犹太教是难以分割的,希伯来语本身也承载了对土地的珍视之感;而政治一方面受到了犹太教和希伯来语的影响,包括实体化组织的和思想上的,同时,政治行动也使得他们更加可信。如此形成的强大诉求并没有在以色列国土内得到满足,而转向了宗教上属于他们但国际社会却不承认的地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此消彼长)
一、引言
2015年1月30日以色列土地管理局招标在约旦河西岸修建450套犹太人定居点新住房。此举再次引来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浪潮,冲突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在本已紧张的以巴关系上火上浇油。折磨了巴勒斯坦这个圣经中描述成“蜂蜜和牛奶”的地方近70年的以巴冲突中,犹太定居点问题长期以来是冲突双方难以达成持久和平的症结所在。
以色列国起源于零星分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而现今定居点则主要在被占领土地上。这些犹太定居点的构成不仅包括官方承认、规划的犹太人聚居区,也包括未被承认的自发建设的犹太人聚居区“前哨所”。在巴勒斯坦看来,犹太定居点的蔓延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不断进行的妄图对巴勒斯坦祖国的蚕食,其意图在于消灭巴勒斯坦。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建设定居点的动力深入犹太骨髓中的犹太认同。定居点问题的重要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到了单个因素造成的动力,并且在一些概念上的使用并不准确。
本文认为定居点的动力源自宗教上的领土愿望并没有在以色列国土内得到满足的,迫使以色列政府顶住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建设定居点,而另外一些更为狂热的则自主建设定居点。希伯来语和以圣经为经典的犹太教是难以分割的,希伯来语本身也承载了对土地的珍视之感,而政治一方面受到了犹太教和希伯来语的影响,包括实体化组织的和思想上的,同时,政治行动也使得他们更加可信。如此,力求对定居点建设的宗教、语言以及两者与政治的互动而产生的动力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时,并不否认其他诸如经济、军事安全等因素作为定居点的建设以及扩张的动力的重要性。
二、定居点建设的犹太教动力
首先,现今以色列的国土并没有填满犹太人认为上帝许诺他们的土地。谈论犹太教对定居点建设的影响,离不开两个概念:“应允之地”和“以色列之地”。这两个概念在一些研究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前者在《圣经》中在不同章节有不同的解释,但大致上前者指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而后者则是随以色列部落的位置而定,包括现在的黎巴嫩,西岸和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和一小部分的叙利亚。这两个概念不仅是复国主义者建国的精神指导,而且是在现今犹太定居点建设的口号。“以色列之地”和“应允之地”都作为合法性的证明而被使用,而在有定居诉求者的宣告中,“以色列之地”更为常用。不管采用哪个观念,现在的以色列国包括未被承认但实际控制的领土在内,也没填满“圣经领土”,而他们要做的就是要用定居点“填满它”。
犹太教作为定居点建设行动合理的辩护,认为这片土地就属于他们。尽管“以色列之地”的地理界限是模糊的,但是所有者却是明晰的,在他们看来观念的模糊性并不阻碍“回到”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步伐。这片土地是耶和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后来更明确许给以色列人。以所有者自居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当然是正当的,就算国家或政府没有准许又奈定居者何?以色列国的起源就是散布在巴勒斯坦的300多个定居点。西岸的定居者们对神圣土地的向往高于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原则的尊重,因而会有时无视政府法令和国际社会的谴责而涌向“以色列之地”中那些尚未纳入以色列国领土的部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他们定居到“以色列之地”之外,比如在埃拉特,这事实上也并不违反犹太律典:“上帝会给你们许给父辈的全部土地,上帝会扩大你们的土地。”
再者,定居者们具有强硬的宗教弥撒亚主义的世界观鼓舞着他们进行定居点建设。他们认为犹太人应该控制整个“以色列之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的定居点工程是犹太民族复兴的一部分,是救世主早日降临的不可或缺条件,而他们所遭受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先知预言显现的必要奋斗,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更有甚者声称:“只有当被流放的犹太人重回故土,人类的灵魂才能得到救赎。”这种将在“以色列之地”定居与善相连的观点在 “因为作恶的必备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袭土地。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府对两个在犹太教堂里施暴的阿拉伯人的惩罚之一便是拆除他们的居所,让他们流离失所,这也是宗教的伎俩。犹太教的信仰体系中“行为成为相信证据”,不是靠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争取,犹太人需要靠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相信上帝,而在西岸等地建设定居点,便是对上帝应允的信仰的证明。在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不仅强调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等地的历史权利,而且认为以色列祖先的土地神圣不可出让”,他们为神圣的土地而斗争,而国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增加了他们对国家的不信任,甚至对在他们看来是以色列国象征的军队和警察充满敌意。建国后以色列并没有获得完整的“以色列之地”,今天的以色列国也没有。但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的信仰不止步于国家,而是在上帝的救赎和应许的土地。以色列中社会意见很不同意,在复国主义、传统主义犹太人和犹太教徒中也时常争论不休。但是他们作为犹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他们生活的习俗、语言都是源于犹太教的。
三、希伯来语与定居点建设动力:
希伯来语的使用也为定居点建设提供了动力。在承认定居点的政府声明特别值得注意,“整个‘以色列之地’历史土地是犹太人不可分割的遗产,犹大和撒玛利亚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交给外国统治。”除了对“以色列之地”的强调之外,特意使用了“犹大”和“撒玛利亚”两个词,他们所指的就是西岸。之所以使用“犹大”和“撒玛利亚”而不是“西岸”有宗教因素,也有语言因素——这两个都是希伯来语词。或许一些犹太教派的具体教旨对世俗犹太人而言有较小的感召力,但现如今使用希伯来语的他们没法从用于表达和思考的希伯来语中逃脱。一个民族的思索都体现在语言上,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希伯来语中,存在对土地的珍视感。古希伯来语是《圣经·旧约》(塔纳赫)的语言(其中就体现了人和土地的紧密联系)这是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的精神根本。希伯来语是犹太人与塔纳赫之间的纽带,希伯来语把犹太历史、犹太教和犹太人牢牢绑在一起。当今以色列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是古希伯来语的复生,除了在词汇上的增减外,没有大变动。本身存在于古希伯来语中对土地的珍视也随之复生。
有意思的是亚当也就是人一词和土地一词是同根的,从构词法角度解释,土地则应为“人母”之意。犹太人的认定是基于母系一支,确认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母亲是不是犹太人,而母亲观念的地位也就更有力地说明了土地,也就是“人母”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了。语言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力来自于所指的观念,“人母”观念的重要性在现今犹太人日常使用中不断强化,很容易转化为思想上的强大暗示——更何况人和土地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就是密不可分的——进而产生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语言暗示下转化为寻求更多土地行动的冲动,这种冲动成为一些犹太人以建立定居点而占取土地的动力。
另外,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犹太人身份认同紧密相连,语言会塑造认同,而不同的认同会导致不同的行动以及不同的理解。“地名以不同形式标识,显然不仅是语言表层的差异, 它可以唤起不同族群的情感与记忆。”以色列政府也意识到了语言名称的作用,而使用希伯来语古名称比如将西岸称为“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这便是向犹太认同求得西岸的合法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看来,巴勒斯坦地名不过是阿拉伯人把希伯来地名用阿拉伯语拼法和读法表示出来;再者,“西岸”是约旦国王的叫法,是充满政治化的词汇,不能表达救赎意味;另外,古罗马人驱逐犹太人后将以色列改为巴勒斯坦,而称“犹大和撒玛利亚”是犹太人回归对土地重新正名,与复国主义遥相呼应;还有“犹大”和“撒玛利亚”两个希伯来词语像一根线一样将犹太圣经历史传统与现代以色列国缝合。犹太人尽人皆知撒玛利亚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又是现代以色列的心脏;也知道古犹大国王约西亚复兴犹太教的故事。这些故事吸引着以色列犹太人遵循上帝的意志重新回到西岸。当然,这也是这片土地圣经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属于犹太人的强调,增加定居之举的正义感,继而减轻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公意的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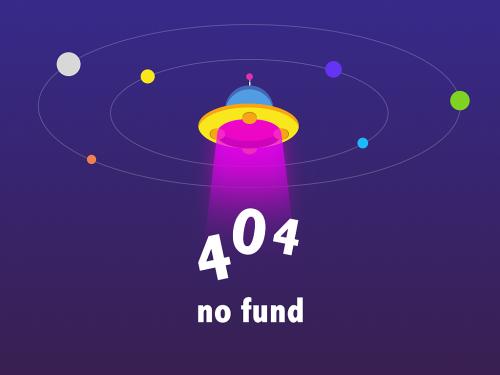
(犹太定居点)
四、政治和宗教、语言的互动:
在2011年时在西岸就有150个经批准的定居点和100的未经批准的定居点。定居点的不断扩建是政治和宗教、语言互动的结果。以色列是一个犹太议会制民主国家。在强调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强调犹太的认同,虽然给予了阿拉伯人相应的选举权,但是犹太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2014年11月在内塔尼亚胡内阁通过“犹太国家”法案则更加强调了希伯来语的地位,将它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作为犹太的认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的教义和希伯来语言的暗示成为以色列当今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宗教和语言影响着每一个以色列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宏观的世界观图景,这个图景驱赶着他们走向未被纳入以色列领土的那部分“以色列之地”。
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复国主义之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教与民族主义的历史结合。它们策略不同,但是无论哪种复国主义都承认源自犹太人在“以色列之地”的神圣权利。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控制了以色列议会,在2013年选举产生的利库德集团就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今天以色列的政治思想是极度多样的,“一百个以色列人就有一百个政党。”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党。但是以色列实行的单一比例代表制的席位门槛比较低,只需2%就可以进入议会,这使得在议会中小党林立,大党不大,大党常常需要争取小党的支持。宗教政党的产生本身就是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的体现,它们在以色列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因而宗教政党常常成为争取对象。宗教政党加入政府,反过来又增加了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在2013年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为了执政就和坚持定居点建设的犹太人之家组成政治联盟。犹太人之家坚持要建立一个犹太法典治下的政体,坚持对“以色列之地”全境的神圣控制,许多议员在领导定居点建设。党首纳夫塔里·本内特(naftali bennett)任新政府的经济部长和宗教事务部长,而犹太人之家党员乌利·阿里尔(uri ariel)任住房建设部部长,这位虔诚的部长就居住在西岸定居点。宗教事务部和民政部一直是定居点的主要推手,而宗教正当党员在政府中的任职使他们更容易践行弥撒亚主义,鼓励在西岸定居,为定居点建设大开方便之门,乌利·阿里尔曾兴奋地表示:“我认为五年内将会由55万到60万犹太人生活在犹大和撒玛利亚。”
在议会民主政治中,一个政党不但要回应选民的诉求还要照顾好与院外集团的特殊关系。在院外集团中,信仰者集团首屈一指。是20世纪后期在以色列兴起的有强烈原教旨主义犹太右翼院外集团。它以宗教复国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以通过在被占领土狂热开展定居运动从而“推动神的拯救”为其主要使命。它与利库德集团的紧密联系使他们在定居点建设上愈发猖狂,一则使用各种手段反对政府采取的拆除、迁出定居点政策,再则自己私自建立定居点。早在七十年代信仰者集团无视政府规划,在戈兰腹地、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筹建定居点,因为在“以色列之地”上,利库德政府在考量两自己的立场和信仰者集团的“天然盟友”关系后,予若干定居点以承认。而这又是个危险的先例,刺激了其他的极端集团采取同样的策略。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橙军”,坚决反对沙龙政府2005年从加沙拆除21个定居点,同时在西岸自行建设定居点。沙龙的军人的意志力也没办法顶住巨大的压力,只好妥协在西岸批准建设定居点作为补偿。政府尽管会对未被承认的定居点采取拆除或者驱逐的办法,但是大多数私建的定居点还是得到了政府默许,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加上政府在定居点建设上的积极态度,造成了一种积极复归“犹大”和“撒玛利亚”,宗教使命一步一步的走向实现的表面现象。

(巴勒斯坦民众高举国旗抗议 反对以色列占用土地)
复兴希伯来语本来就是复兴犹太国家的一部分。通过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整个集体文化中的一分子。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犹太人的认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英国托管时期就已经成为托管当局的官方语言,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学校中广泛使用。希伯来语塑造了犹太民族,没有希伯来语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国,自独立起,希伯来语就是以色列政府大力推广的,无论是在政府机构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学校里的强制使用让希伯来语在以色列国完全扎根。语言所承载的思想也随之犹太人心目中扎根,其中当然包括对土地的珍视。虽然在以色列官方语言中有阿拉伯语,但是位处卑微。11月23日,在内塔尼亚胡的强力运作下,以内阁通过了一份由他提出的“犹太国家”法案。法案规定,以色列是“犹太国家”,希伯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将不再是官方语言,只享有“特殊地位”。另据内塔尼亚胡解释,“犹太国家”属性意味着以色列是“专属于犹太民族的家园”,但只有犹太人拥有民族权利,比如国旗、国歌和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及其他民族象征。这是与内塔尼亚胡在西岸扩建定居点的政策相一致的。
更名运动通过将地名改为希伯来名称,政治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在地名上融合,企图发挥希伯来语连接宗教、历史以及生活的纽带作用。三个心概念:上帝、选民和土地,这三者相互紧密联系,乃是犹太精神永恒的品质。只有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犹太人才是遵从上帝的戒律,而“以色列之地”与“托拉”两者密不可分。在更名运动时,政府更是成了急先锋,先是在内盖夫,后来扩展到六日战争后的被占领土地。
以色列国国父本·古立安就曾主抓过用希伯来语拼写重新命名的工作,在第一次视察内盖夫的时候就指示道:“当以色列国旗在内盖夫沙漠升起时,更改地名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去掉外国地名, 改为希伯来名称,才能贴近内盖夫保卫者和定居者的心。” 使用表达“以色列之地” 与古代文献之间的“连续性”与“一贯性”,又可以见证古代犹大和以色列王国与现代以色列之间的历史联系。在内盖夫那里的更名运动旋即扩大了,本·古立安“我希望你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从外国语言的统治中救赎出来。”现在“以色列之地”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名称,地名的更改不仅要贴近内盖夫定居者的心,还要贴近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定居者的心。目前在该区域上的路标、指示牌、对应的地图等采用的都是希伯来语名称。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定居者一方面受到地区名称所承载的历史-宗教的感召,加上熟悉的语言减少了对初到地域的陌生感,定居在此至少没有语言困难。当定居者们看到“犹大”或“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脑海中反映不仅仅是两个希伯来单词,而是整个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一切属于犹太人的记忆与期待。许多定居点便在一种崇敬心态下被建立起来,许多定居者也慕名而来。和早期定居点的命名一样,更名运动伴随着定居点的扩张。到了1992年,已经勘定了希伯来语地名7000个。更名运动和定居点都是“去阿拉伯化”大潮的一部分,一个是在文化层面的,另一个则是赤裸裸的殖民。政府强行推行希伯来化工程,无视当地居民的日常使用的地名,受到一定民间习惯的阻力。不过官方还是找到突破口——军队,以其服从的先是在国防里强制推行新名称。在国防军中服役的许多不久后就会回到社会中生活,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人是信仰者集团的成员。受更名化运动影响,士兵复员回到社会,又带动身边的人习惯新的地名。就这样,从部队里放出的洪水猛兽,又支持更名名运动,积极分子还受到语言的感召,踏步走向“犹大”和“撒玛利亚”并在那定居下来了。原来地名积累下来的民间记忆渐趋消损。
这种政府动员和自发形成的在民众中宗教和语言的混合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国父本·古立安接受分治方案时也要面对复国主义这内部重重困难,而在土地狂热的压力下,迫不得已方案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声称接受分治方案只是暂时的安排,他本人的目标是整个“以色列之地”。从此,一道“伤疤”留在以色列犹太人心中,他们的国家一开始领土就不是完整的。在教义和语言的指引或暗示下,他们便通过在西岸等地占据“属于他们的”土地,建设大大小小的定居点,有时甚至无视政府禁令。政府毕竟要和国际社会打交道,而且要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经济考量、国防安全和再次当选等等问题,不能一味只满足定居者的愿望。而定居者对土地的热衷和现实政治的局面对当政者是个挑战,因而拥有批准定居点权力的门槛不断提高直至唯独以色列总理全掌。
五、结论
犹太教和希伯来语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构成了犹太人认同的绝大部分,这个认同既有指引力量又有强迫力量,犹太教的弥撒亚和自我救赎的观念,加上希伯来语和希伯来化所承载的对土地的珍视,使许多犹太人对“以色列之地”趋之若鹜。而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不能够将整个“以色列之地”纳入囊中,而定居点,特别是自发建立的定居点则是这对一缺憾的“补偿”。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政治行为体本身就受到宗教和希伯来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他们对希伯来化的推动和对犹太认同的强调反过来使得犹太教和希伯来语所承载的观念更加可信。同样,政府和定居者们也达成心照不宣的协议,对未批准的定居点给予部分承认和事实上的政策支持,定居者们则会捍卫土地以及将以色列的政治延伸到“犹大”和“撒玛利亚”。
许多年来,和平进程、宗教在国家的角色和政治丑闻是政治联盟产生和分裂的原因。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建定居点是亏钱的,不过在舒缓人口压力有有限作用。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中心经济学院院长茨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曾说:“我知道怎么能够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建造定居点更多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政治。”诚然如此,兴建定居点是要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的。现在看来,围绕定居点的矛盾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定居点问题是成了一种手段,外交的进攻手段。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好后,以色列立即宣布新增加建立定居点。这又加深了以巴之间的矛盾,使得哈马斯更加受欢迎。对哈马斯的憎恶又加强了国内的认同压力,也增强了建设定居点作为安全前哨的紧迫感,迫使政府在定居点上的让步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另外,有失败的加沙撤退的前车之鉴,以色列在定居点上的让步也变得越来越谨慎。定居点不断的扩张则又刺激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对犹太定居点的敏感和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他们的大灾难(al-nakba)就始于零星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定居点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在哪?
(吴迪,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新视角发布时未保留注释和参考文献。)
摘要:作为以巴冲突的纠结点之一,犹太定居点的建设的动力来自于犹太教、希伯来语和政治三者互动。希伯来语和与定居点所在土地直接相连的犹太教是难以分割的,希伯来语本身也承载了对土地的珍视之感;而政治一方面受到了犹太教和希伯来语的影响,包括实体化组织的和思想上的,同时,政治行动也使得他们更加可信。如此形成的强大诉求并没有在以色列国土内得到满足,而转向了宗教上属于他们但国际社会却不承认的地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此消彼长)
一、引言
2015年1月30日以色列土地管理局招标在约旦河西岸修建450套犹太人定居点新住房。此举再次引来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浪潮,冲突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在本已紧张的以巴关系上火上浇油。折磨了巴勒斯坦这个圣经中描述成“蜂蜜和牛奶”的地方近70年的以巴冲突中,犹太定居点问题长期以来是冲突双方难以达成持久和平的症结所在。
以色列国起源于零星分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而现今定居点则主要在被占领土地上。这些犹太定居点的构成不仅包括官方承认、规划的犹太人聚居区,也包括未被承认的自发建设的犹太人聚居区“前哨所”。在巴勒斯坦看来,犹太定居点的蔓延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不断进行的妄图对巴勒斯坦祖国的蚕食,其意图在于消灭巴勒斯坦。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建设定居点的动力深入犹太骨髓中的犹太认同。定居点问题的重要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是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到了单个因素造成的动力,并且在一些概念上的使用并不准确。
本文认为定居点的动力源自宗教上的领土愿望并没有在以色列国土内得到满足的,迫使以色列政府顶住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建设定居点,而另外一些更为狂热的则自主建设定居点。希伯来语和以圣经为经典的犹太教是难以分割的,希伯来语本身也承载了对土地的珍视之感,而政治一方面受到了犹太教和希伯来语的影响,包括实体化组织的和思想上的,同时,政治行动也使得他们更加可信。如此,力求对定居点建设的宗教、语言以及两者与政治的互动而产生的动力进行较深入的分析时,并不否认其他诸如经济、军事安全等因素作为定居点的建设以及扩张的动力的重要性。
二、定居点建设的犹太教动力
首先,现今以色列的国土并没有填满犹太人认为上帝许诺他们的土地。谈论犹太教对定居点建设的影响,离不开两个概念:“应允之地”和“以色列之地”。这两个概念在一些研究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前者在《圣经》中在不同章节有不同的解释,但大致上前者指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而后者则是随以色列部落的位置而定,包括现在的黎巴嫩,西岸和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和一小部分的叙利亚。这两个概念不仅是复国主义者建国的精神指导,而且是在现今犹太定居点建设的口号。“以色列之地”和“应允之地”都作为合法性的证明而被使用,而在有定居诉求者的宣告中,“以色列之地”更为常用。不管采用哪个观念,现在的以色列国包括未被承认但实际控制的领土在内,也没填满“圣经领土”,而他们要做的就是要用定居点“填满它”。
犹太教作为定居点建设行动合理的辩护,认为这片土地就属于他们。尽管“以色列之地”的地理界限是模糊的,但是所有者却是明晰的,在他们看来观念的模糊性并不阻碍“回到”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步伐。这片土地是耶和华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后来更明确许给以色列人。以所有者自居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当然是正当的,就算国家或政府没有准许又奈定居者何?以色列国的起源就是散布在巴勒斯坦的300多个定居点。西岸的定居者们对神圣土地的向往高于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原则的尊重,因而会有时无视政府法令和国际社会的谴责而涌向“以色列之地”中那些尚未纳入以色列国领土的部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他们定居到“以色列之地”之外,比如在埃拉特,这事实上也并不违反犹太律典:“上帝会给你们许给父辈的全部土地,上帝会扩大你们的土地。”
再者,定居者们具有强硬的宗教弥撒亚主义的世界观鼓舞着他们进行定居点建设。他们认为犹太人应该控制整个“以色列之地”,在每一寸土地上的定居点工程是犹太民族复兴的一部分,是救世主早日降临的不可或缺条件,而他们所遭受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先知预言显现的必要奋斗,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更有甚者声称:“只有当被流放的犹太人重回故土,人类的灵魂才能得到救赎。”这种将在“以色列之地”定居与善相连的观点在 “因为作恶的必备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袭土地。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府对两个在犹太教堂里施暴的阿拉伯人的惩罚之一便是拆除他们的居所,让他们流离失所,这也是宗教的伎俩。犹太教的信仰体系中“行为成为相信证据”,不是靠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争取,犹太人需要靠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相信上帝,而在西岸等地建设定居点,便是对上帝应允的信仰的证明。在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们不仅强调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等地的历史权利,而且认为以色列祖先的土地神圣不可出让”,他们为神圣的土地而斗争,而国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增加了他们对国家的不信任,甚至对在他们看来是以色列国象征的军队和警察充满敌意。建国后以色列并没有获得完整的“以色列之地”,今天的以色列国也没有。但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的信仰不止步于国家,而是在上帝的救赎和应许的土地。以色列中社会意见很不同意,在复国主义、传统主义犹太人和犹太教徒中也时常争论不休。但是他们作为犹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他们生活的习俗、语言都是源于犹太教的。
三、希伯来语与定居点建设动力:
希伯来语的使用也为定居点建设提供了动力。在承认定居点的政府声明特别值得注意,“整个‘以色列之地’历史土地是犹太人不可分割的遗产,犹大和撒玛利亚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交给外国统治。”除了对“以色列之地”的强调之外,特意使用了“犹大”和“撒玛利亚”两个词,他们所指的就是西岸。之所以使用“犹大”和“撒玛利亚”而不是“西岸”有宗教因素,也有语言因素——这两个都是希伯来语词。或许一些犹太教派的具体教旨对世俗犹太人而言有较小的感召力,但现如今使用希伯来语的他们没法从用于表达和思考的希伯来语中逃脱。一个民族的思索都体现在语言上,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希伯来语中,存在对土地的珍视感。古希伯来语是《圣经·旧约》(塔纳赫)的语言(其中就体现了人和土地的紧密联系)这是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的精神根本。希伯来语是犹太人与塔纳赫之间的纽带,希伯来语把犹太历史、犹太教和犹太人牢牢绑在一起。当今以色列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是古希伯来语的复生,除了在词汇上的增减外,没有大变动。本身存在于古希伯来语中对土地的珍视也随之复生。
有意思的是亚当也就是人一词和土地一词是同根的,从构词法角度解释,土地则应为“人母”之意。犹太人的认定是基于母系一支,确认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母亲是不是犹太人,而母亲观念的地位也就更有力地说明了土地,也就是“人母”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了。语言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力来自于所指的观念,“人母”观念的重要性在现今犹太人日常使用中不断强化,很容易转化为思想上的强大暗示——更何况人和土地在希伯来语圣经中就是密不可分的——进而产生对土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语言暗示下转化为寻求更多土地行动的冲动,这种冲动成为一些犹太人以建立定居点而占取土地的动力。
另外,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犹太人身份认同紧密相连,语言会塑造认同,而不同的认同会导致不同的行动以及不同的理解。“地名以不同形式标识,显然不仅是语言表层的差异, 它可以唤起不同族群的情感与记忆。”以色列政府也意识到了语言名称的作用,而使用希伯来语古名称比如将西岸称为“犹大和撒玛利亚地区”。这便是向犹太认同求得西岸的合法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看来,巴勒斯坦地名不过是阿拉伯人把希伯来地名用阿拉伯语拼法和读法表示出来;再者,“西岸”是约旦国王的叫法,是充满政治化的词汇,不能表达救赎意味;另外,古罗马人驱逐犹太人后将以色列改为巴勒斯坦,而称“犹大和撒玛利亚”是犹太人回归对土地重新正名,与复国主义遥相呼应;还有“犹大”和“撒玛利亚”两个希伯来词语像一根线一样将犹太圣经历史传统与现代以色列国缝合。犹太人尽人皆知撒玛利亚为古以色列王国首都,又是现代以色列的心脏;也知道古犹大国王约西亚复兴犹太教的故事。这些故事吸引着以色列犹太人遵循上帝的意志重新回到西岸。当然,这也是这片土地圣经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属于犹太人的强调,增加定居之举的正义感,继而减轻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公意的愧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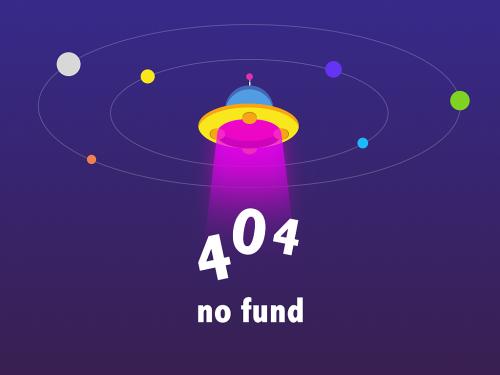
(犹太定居点)
四、政治和宗教、语言的互动:
在2011年时在西岸就有150个经批准的定居点和100的未经批准的定居点。定居点的不断扩建是政治和宗教、语言互动的结果。以色列是一个犹太议会制民主国家。在强调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强调犹太的认同,虽然给予了阿拉伯人相应的选举权,但是犹太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在2014年11月在内塔尼亚胡内阁通过“犹太国家”法案则更加强调了希伯来语的地位,将它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作为犹太的认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的教义和希伯来语言的暗示成为以色列当今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宗教和语言影响着每一个以色列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宏观的世界观图景,这个图景驱赶着他们走向未被纳入以色列领土的那部分“以色列之地”。
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复国主义之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教与民族主义的历史结合。它们策略不同,但是无论哪种复国主义都承认源自犹太人在“以色列之地”的神圣权利。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控制了以色列议会,在2013年选举产生的利库德集团就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今天以色列的政治思想是极度多样的,“一百个以色列人就有一百个政党。”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党。但是以色列实行的单一比例代表制的席位门槛比较低,只需2%就可以进入议会,这使得在议会中小党林立,大党不大,大党常常需要争取小党的支持。宗教政党的产生本身就是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力的体现,它们在以色列政治影响力不容小觑,因而宗教政党常常成为争取对象。宗教政党加入政府,反过来又增加了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力。在2013年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为了执政就和坚持定居点建设的犹太人之家组成政治联盟。犹太人之家坚持要建立一个犹太法典治下的政体,坚持对“以色列之地”全境的神圣控制,许多议员在领导定居点建设。党首纳夫塔里·本内特(naftali bennett)任新政府的经济部长和宗教事务部长,而犹太人之家党员乌利·阿里尔(uri ariel)任住房建设部部长,这位虔诚的部长就居住在西岸定居点。宗教事务部和民政部一直是定居点的主要推手,而宗教正当党员在政府中的任职使他们更容易践行弥撒亚主义,鼓励在西岸定居,为定居点建设大开方便之门,乌利·阿里尔曾兴奋地表示:“我认为五年内将会由55万到60万犹太人生活在犹大和撒玛利亚。”
在议会民主政治中,一个政党不但要回应选民的诉求还要照顾好与院外集团的特殊关系。在院外集团中,信仰者集团首屈一指。是20世纪后期在以色列兴起的有强烈原教旨主义犹太右翼院外集团。它以宗教复国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以通过在被占领土狂热开展定居运动从而“推动神的拯救”为其主要使命。它与利库德集团的紧密联系使他们在定居点建设上愈发猖狂,一则使用各种手段反对政府采取的拆除、迁出定居点政策,再则自己私自建立定居点。早在七十年代信仰者集团无视政府规划,在戈兰腹地、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筹建定居点,因为在“以色列之地”上,利库德政府在考量两自己的立场和信仰者集团的“天然盟友”关系后,予若干定居点以承认。而这又是个危险的先例,刺激了其他的极端集团采取同样的策略。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橙军”,坚决反对沙龙政府2005年从加沙拆除21个定居点,同时在西岸自行建设定居点。沙龙的军人的意志力也没办法顶住巨大的压力,只好妥协在西岸批准建设定居点作为补偿。政府尽管会对未被承认的定居点采取拆除或者驱逐的办法,但是大多数私建的定居点还是得到了政府默许,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加上政府在定居点建设上的积极态度,造成了一种积极复归“犹大”和“撒玛利亚”,宗教使命一步一步的走向实现的表面现象。

(巴勒斯坦民众高举国旗抗议 反对以色列占用土地)
复兴希伯来语本来就是复兴犹太国家的一部分。通过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整个集体文化中的一分子。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犹太人的认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英国托管时期就已经成为托管当局的官方语言,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学校中广泛使用。希伯来语塑造了犹太民族,没有希伯来语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国,自独立起,希伯来语就是以色列政府大力推广的,无论是在政府机构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学校里的强制使用让希伯来语在以色列国完全扎根。语言所承载的思想也随之犹太人心目中扎根,其中当然包括对土地的珍视。虽然在以色列官方语言中有阿拉伯语,但是位处卑微。11月23日,在内塔尼亚胡的强力运作下,以内阁通过了一份由他提出的“犹太国家”法案。法案规定,以色列是“犹太国家”,希伯来语为唯一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将不再是官方语言,只享有“特殊地位”。另据内塔尼亚胡解释,“犹太国家”属性意味着以色列是“专属于犹太民族的家园”,但只有犹太人拥有民族权利,比如国旗、国歌和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及其他民族象征。这是与内塔尼亚胡在西岸扩建定居点的政策相一致的。
更名运动通过将地名改为希伯来名称,政治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在地名上融合,企图发挥希伯来语连接宗教、历史以及生活的纽带作用。三个心概念:上帝、选民和土地,这三者相互紧密联系,乃是犹太精神永恒的品质。只有生活在上帝应许之地,犹太人才是遵从上帝的戒律,而“以色列之地”与“托拉”两者密不可分。在更名运动时,政府更是成了急先锋,先是在内盖夫,后来扩展到六日战争后的被占领土地。
以色列国国父本·古立安就曾主抓过用希伯来语拼写重新命名的工作,在第一次视察内盖夫的时候就指示道:“当以色列国旗在内盖夫沙漠升起时,更改地名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去掉外国地名, 改为希伯来名称,才能贴近内盖夫保卫者和定居者的心。” 使用表达“以色列之地” 与古代文献之间的“连续性”与“一贯性”,又可以见证古代犹大和以色列王国与现代以色列之间的历史联系。在内盖夫那里的更名运动旋即扩大了,本·古立安“我希望你们继续他们的工作,把以色列全境从外国语言的统治中救赎出来。”现在“以色列之地”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名称,地名的更改不仅要贴近内盖夫定居者的心,还要贴近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定居者的心。目前在该区域上的路标、指示牌、对应的地图等采用的都是希伯来语名称。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定居者一方面受到地区名称所承载的历史-宗教的感召,加上熟悉的语言减少了对初到地域的陌生感,定居在此至少没有语言困难。当定居者们看到“犹大”或“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脑海中反映不仅仅是两个希伯来单词,而是整个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一切属于犹太人的记忆与期待。许多定居点便在一种崇敬心态下被建立起来,许多定居者也慕名而来。和早期定居点的命名一样,更名运动伴随着定居点的扩张。到了1992年,已经勘定了希伯来语地名7000个。更名运动和定居点都是“去阿拉伯化”大潮的一部分,一个是在文化层面的,另一个则是赤裸裸的殖民。政府强行推行希伯来化工程,无视当地居民的日常使用的地名,受到一定民间习惯的阻力。不过官方还是找到突破口——军队,以其服从的先是在国防里强制推行新名称。在国防军中服役的许多不久后就会回到社会中生活,更重要的是有许多人是信仰者集团的成员。受更名化运动影响,士兵复员回到社会,又带动身边的人习惯新的地名。就这样,从部队里放出的洪水猛兽,又支持更名名运动,积极分子还受到语言的感召,踏步走向“犹大”和“撒玛利亚”并在那定居下来了。原来地名积累下来的民间记忆渐趋消损。
这种政府动员和自发形成的在民众中宗教和语言的混合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国父本·古立安接受分治方案时也要面对复国主义这内部重重困难,而在土地狂热的压力下,迫不得已方案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声称接受分治方案只是暂时的安排,他本人的目标是整个“以色列之地”。从此,一道“伤疤”留在以色列犹太人心中,他们的国家一开始领土就不是完整的。在教义和语言的指引或暗示下,他们便通过在西岸等地占据“属于他们的”土地,建设大大小小的定居点,有时甚至无视政府禁令。政府毕竟要和国际社会打交道,而且要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经济考量、国防安全和再次当选等等问题,不能一味只满足定居者的愿望。而定居者对土地的热衷和现实政治的局面对当政者是个挑战,因而拥有批准定居点权力的门槛不断提高直至唯独以色列总理全掌。
五、结论
犹太教和希伯来语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构成了犹太人认同的绝大部分,这个认同既有指引力量又有强迫力量,犹太教的弥撒亚和自我救赎的观念,加上希伯来语和希伯来化所承载的对土地的珍视,使许多犹太人对“以色列之地”趋之若鹜。而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不能够将整个“以色列之地”纳入囊中,而定居点,特别是自发建立的定居点则是这对一缺憾的“补偿”。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政治行为体本身就受到宗教和希伯来语言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他们对希伯来化的推动和对犹太认同的强调反过来使得犹太教和希伯来语所承载的观念更加可信。同样,政府和定居者们也达成心照不宣的协议,对未批准的定居点给予部分承认和事实上的政策支持,定居者们则会捍卫土地以及将以色列的政治延伸到“犹大”和“撒玛利亚”。
许多年来,和平进程、宗教在国家的角色和政治丑闻是政治联盟产生和分裂的原因。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建定居点是亏钱的,不过在舒缓人口压力有有限作用。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中心经济学院院长茨维·埃克斯坦(zvi eckstein)曾说:“我知道怎么能够在政治正确的情况下回答问题。建造定居点更多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政治。”诚然如此,兴建定居点是要付出极大的经济代价的。现在看来,围绕定居点的矛盾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定居点问题是成了一种手段,外交的进攻手段。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好后,以色列立即宣布新增加建立定居点。这又加深了以巴之间的矛盾,使得哈马斯更加受欢迎。对哈马斯的憎恶又加强了国内的认同压力,也增强了建设定居点作为安全前哨的紧迫感,迫使政府在定居点上的让步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另外,有失败的加沙撤退的前车之鉴,以色列在定居点上的让步也变得越来越谨慎。定居点不断的扩张则又刺激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对犹太定居点的敏感和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他们的大灾难(al-nakba)就始于零星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么,定居点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在哪?
(吴迪,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新视角发布时未保留注释和参考文献。)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打赏哦